【中国故事】
谢大伟的态度让谢五龙感到很受用,心里有了一束亮光,他要把这束亮光照到农民工身上去,让他们感到,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门房,也有关心他人的情感。所以一整天他都给工友们沏水、递水,以至于把一整罐“信阳毛尖”都喝光了。
壹
刚才晚霞还通红,低头的工夫就灰了,西天被遮得灰蒙蒙一片。接着就听到头顶的石棉瓦上有叮咚叮咚的声音。
这个声音很稀落,有一搭无一搭的。谢五龙探出头去,一颗硕大的檐滴落在他的脸上,凉了一下。他心中一喜,暑热或许从此就消了,好日子或许就来了。他索性把胳膊伸出去,任檐滴一颗一颗打在上面,一片皮肤被润湿着,有惬意在当下的感觉,他不禁欢快地叫了一声:好。
家屋的当庭长着一棵大香椿树,春天的嫩芽是喂嘴的,给寡淡的日子添味道;夏天的老叶是爽心的,承接的雨露径直滴到头发上、脸上、胳膊上,让人感到时序的滋润,活着真好。
到了这个小城,小区扩建,他给工地当门房。门房临街,傍着一棵国槐,墙是毛砖干砌,屋顶是石棉瓦遮覆,是临时的建构,所以,住在里边,他总感到有一个特别的提醒:他不属于这里,不过是个临时栖身的人。夏天风吹日晒,热;冬天寒风钻隙,冷——他都得忍着。几个工钱虽然很少,但也是好的。大儿子日子过得好好的,但不甘心仨饱俩倒的凡常生活,非得建了一家蜂窝煤厂,后来推行煤改电,厂子就关闭了。但建厂的钱都是借来的,得还。债是越还越少的,不还总是背着,因此,尽管他的工钱少得可怜,但也金贵,能帮儿子还钱,是翻身的希望。
虽然住在临时房里,人感到卑微,但也能接到雨滴;虽然雨滴是打在屋瓦上的,染了灰尘之后滚落成檐滴,不纯净了,但毕竟是湿润的东西。人一被湿润,内心就舒展,还联想到家乡,就不自怜了。
而且,这份工作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轮到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老兄弟在区建委给领导开车,哪儿能在城里的工地找到一个门房的职位?嘁,你想卑微还卑微不来呢,所以我不卑微。
檐滴不停地滚落,他心情很好,开始拾掇晚炊。
门房外他自己支了一个塑料凉棚。凉棚下,他用砖头垒了一个土灶,用水泥抹了灶身,柴火直接就地取材,便可以放心地烧。用土灶做饭,火候能自己掌握,木柴慢慢地烧、油慢慢地热、菜慢慢地熟,他能从容应对。而且,他这个人,干什么都不能快,一快,心里就仓皇,左腿就抽缩,跛了。
这源自生活的意外。
贰
他少年的时候,很调皮。暑期他跟大人一起到山上的堰田里耪地,中午吃完干粮就歇晌。人家歇在地头平整处,躺在干草或细土上,而他却歇在一棵大杏树上。混蒙中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入梦来,向他挤媚眼,嘲笑他不认真学功课。他很生气,睁开了眼睛,向下一望,地上居然真的就蹲着一只白色的狐狸,冷冷地向上看着他。他一怒之下,狠狠地挥出拳头打向狐狸。但是,他忘了,他在树上,狐狸在树下。拳头出,人跌落,狐狸跑,他摔断了腿。经过疗治,断腿长好了,但肌肉萎缩,还短了一截。如果天气好、心情好、睡得好,走起路来两条腿没什么区别,很稳当、很正常;如果天气阴、心里乱、人犯困,短的那节就凸显,好像路面不平,走路的姿势就一上一下的,跛。
在跛与不跛之间,一切都要靠心情调节。那么,他特别提醒自己,看问题,一定要看积极、积极看,也就是说,遇事要想得开、往开里想,做到豁达、乐观、向上、阳光,不消沉。
他给自己拍了一个黄瓜。黄瓜是小贩卖剩下的货色。老、丑、蔫,很不新鲜,但两块钱就能买一兜子,省钱。他先是用醋泡,醋能返嫩、返脆,还能去陈腐味。他给自己爆炒了一个猪大肠。这猪大肠也是小贩卖不出去的一截剩货。那截猪大肠看上去又脏又肥,他一笑:“脏也不是真脏,那是搁到最后的颜色。肥倒是真肥,但是,吃猪大肠吃的就是它那个肥劲儿,嘿嘿。”关键是那截猪大肠很便宜,跟白送的一样。他馏了两个馒头——他本来能吃四个馒头,但是他节制自己:“一个看大门的,吃那么多干什么,白糟蹋粮食。”
他从床下拉出来一个纸箱子。那是一箱子廉价白瓶二锅头。这是住在附近小区有身份的大侄子谢大伟送给他的。数了数还有十五瓶,他嘟囔道:“今天是阴历七月十四,如果一天喝半斤的话,到中秋节还是够的。那么,今天就多喝两杯,嘿嘿。”
他的门房很小,放下一张木板床之后,就剩下屁大的一点地方了,但是,他还是在靠门楣的位置挤进了一个细长的旧木桌。他觉得,没有桌子,我的酒杯往哪儿放?能不能在桌子上喝酒,代表着过的是不是“正经生活”,也代表着一个男人的尊严,所以穷也要讲究。
黄瓜的脆爽,大肠的肥香,二锅头的麻辣,白面馒头的咬劲儿,把他陶醉在小桌子上了——他喝得有点多,懒得起身,乜斜了一眼门外:“咱多讲究,还有沙发,嘿嘿。”
他在门房外紧邻门扉的地方,还放上了一只捡来的单人沙发,每天酒后都会在上边仰一仰、靠一靠,赏一赏月、看一看星,踅摸踅摸街上的行人,有时候还颠着二郎腿哼一哼京西老家的酸曲。哼,我不单单是一个给人家看工地的工具,也是个大活人,也得适时地安逸一下子。
不过,那只沙发也太破了,靠扶手的地方有一个洞,白天他坐,晚上老鼠就钻了进去。“今天就不安逸了,酒把我拿住了。”
叁
谢五龙每天早晨都是六点钟起床。
这时候太阳已经把工地照得很灿烂了。灿烂的东西容不得懒,他得打扫一下门房前后,让人看到他的勤快。勤快的人总被人信任,这个道理他懂。
今天早晨他起得稍早些,因为门外袅进一股气味,又热又呛似有似无的那种。他推开门,吓了一跳。工头竟坐在那只破沙发上,大口地吸烟。工头脚下的地面上,散落着很多烟头。工头抽的是大中华,所以他本能地想,工头心里有事,而且无处诉说。因为那么金贵的名烟,却抽得如此无品,像糟蹋轻贱的东西一样。他小心地赔上笑脸:“您早来了。”工头迷惑地看了他一眼:“你问谁?”真是奇怪了,我能问谁?他只好嘿嘿一笑,避过口风。工头从烟盒里拿出最后的一支烟,用手上的烟头一对,又大口大口地抽了起来。“老谢你说,我该怎么办?”
“您是说,他们答应的工程款还没拨给您?”
“拨?好像连拨付的意向都没有呢,这样一来,我的资金链就快断了。”
谢五龙难受了一下子。当门房的工钱太少了,他几次下决心,一旦遇到工头,无论如何也要请求他给涨几个钱。但工头说资金链就快断了,那就是说他手里也缺钱了,他都自顾不暇了,还能给你涨工钱?真是晦气。
工头承建的这几座楼房,主体已经完成,就差封顶了,本来希望就在前头,却给他带来满腹忧愁——他前期垫资太多,而按约定划拨的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这就带来悬念:如果如期封顶,主建方赖账怎么办?如果拖延工期,主建方追责怎么办?所以,在封顶与不封顶之间,他很犯踌躇。“老谢,你说这几栋楼咱给它封顶不封顶?”谢五龙看了看那个被笼罩在烟雾中的人,突然感到,他虽然是工头、是有钱人,而自己是……但他也有难处,也过得很不容易,那么,他跟自己是一样的,便也应该送上一份体贴,“这还不好办,最好别给它封顶,俗话说得好嘛,有把儿的烧饼必须攥在自己手里,一旦你攥着把柄,甭说人,就连狗都得听你的”。这个为人着想的理由的背后,其实是他个人的思绪——一旦封顶,就意味着竣工,就意味着我的门房要被拆掉,那么我也就随之被解雇了,再少的工资也没地方挣去了。
工头的眼睛被点亮了,从破沙发上站起身来,拍拍谢五龙的肩膀:“嘿嘿,老谢,你够意思。”
“我一个看大门的,够不够意思有什么意思?不过吃谁向谁,说话做事我都得站在您的立场上。”
这个朴实的门房很让工头感动,他大声地说道:“老谢,你心里想什么我也是知道的,你放心,我回去就跟会计说,给你再涨三百块钱的工资,从每月的一千二百块给到一千五百块。你看,咱够不够意思?”
谢五龙心里说,这有啥区别?都是芝麻绿豆钱,还弄得那么大气豪迈,好像有多大方似的。但是,他还是弄出大喜过望的样子:“够意思,真是够意思,老够意思了。”
肆
可工头走了之后,他还是欣喜不已,不停地念叨:“一千五,嘿嘿,一千五。”念叨一久,竟真的以为自己已拿到了这份工钱,便用老年手机拨通了老家的电话:“老伴儿,告诉你吧,我开到一千五百块了,嘿嘿。”
“真拿到手了?”
“真拿到手了。”
“拿到手了好,你要舍得给自己弄点儿好吃的。”
“你就舍得?”
“怎么不舍得?从来没希图他给涨工资,那是多余的钱。”
“那么,你来吧。”
“不去,屁大的个地方装两个大活人,很不正经。”
“真不体贴,那么不跟你说了,费电话费。”
其实,他刚来当门房的时候,老伴也是跟来的,因为两个人搭伙吃饭,省。那是冬天,工地停了,只留门房,看管搬不走的工具和施工材料。两个人挤在狭小的门房里,一张窄床也觉得宽大,因为能够厮守,好像依然翻滚在自家的土炕之上,有离土不离乡的感觉。而且,还能以特殊的方式,过一种小城生活——上早市,砍价买菜,听小贩的吆喝声;也可以向街面张望,看人群熙攘,看车流穿梭,看路灯眨眼。他们觉得新鲜、有趣,好像生活重新开始了一样。
但是,第二年的夏天一过,老伴又悄悄地走了。因为她觉得,这个门房,不是她的容身之地。
冬天,门房四面透风,即便是烧着电暖器,也是冰天冷地。两个人挤在小床上,即便是紧紧相拥、肉挨着肉,浑身上下也像到处都是缝隙,冷得刺骨,贫穷的真实感无处不在。要是搁在老家,滚烫的老土炕,热了皮肉,也热了心扉,更热了梦境,即便是家徒四壁,也不感到贫寒。夏天,蚊虫乱飞,咬得他们恨不得钻天入地。要是搁在老家,即便是房门大开,或者躺在露天地里,也没有一个蚊虫飞近,感到凉爽是不被打扰的。更不能忍受的是,两个人躺到小床上去,身子一靠近,就热烘烘地流汗,肉一挨上肉,就像两团泥搅和在一起,黏缀得不清不楚。
“我得走了。”有一天,她突然说。
“为什么?”
“又冷又热又咬,还没皮没脸地跟你黏糊在一起,好像我离不开你似的。”
“嘿嘿,是我离不开你,还不成?”
“那也不成,你没看见每天开门走出来,工地上那些人看咱们的眼神,好像咱山里人很不讲究。”
“然而咱们是夫妻。”
“在人家的眼里,门房就是一个人住的,非得住两个人,而且还是一男一女。即便是夫妻,也像是搞破鞋的一样。”
白天施工的人,好像都放慢了节奏,肯定是工头下了叮嘱,不让他们急于封顶。但是,他们却把活做细了——认真地打磨外立面,让墙体四面光滑,不放过一条缝隙。因为施工的人都是农民工,他们身上有本分的东西——既然拿着人家的工钱,就不能出工不出力;既然房子将来要住人,就要保证工程质量,让住户住着放心。谢五龙知道他们的心思,所以心里特别敬佩,而且他们拿的工钱并没比自己多多少,却还心甘情愿地卖实在力气,所以敬佩之上又多了一份敬重。
他拿出侄子谢大伟送给他的好茶叶,给他们沏水,殷勤地邀他们来喝。所谓好茶叶,是一种叫“信阳毛尖”的河南茶,谢大伟说是同事旅游时带回来的礼物,而他一年四季只喝北京花茶,因为喝不惯,就拿来“孝敬您老人家”了。他对谢大伟说:“那是你舍得。”在他看来,因为这茶贵重,侄子怕他不好意思喝,就弄出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理由。这孩子重情义,知道他在这里当门房,每到周末,就提着一大堆东西前来看望。谢大伟曾经说,其实他比他老叔关系多,老叔毕竟只是个司机嘛。但是,老叔却费力八荒地给五龙叔找工作。“你们做长辈的真好,不愿给晚辈找麻烦。所以我必须经常来看看您,要对得起亲情。”
瞧这孩子说的,好像他做错了事儿似的,竟然满心的惭愧。谢大伟的态度让谢五龙很受用,心里有了一束亮光,他要把这束亮光照到农民工身上去,让他们感到,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门房,也有关心他人的情感。所以一整天他都给工友们沏水、递水,以至于把一整罐“信阳毛尖”都喝光了。一个工友说:“老谢,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跟捡到钱包似的。”他说:“谁的钱包肯让咱们捡?不捡钱包就不能快乐?我是见不得你们渴。”
伍
他一天“快乐”下来很累,到了晚上,也懒得收拾饭菜,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桶装方便面。这也是谢大伟送的,因为舍不得吃,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闻着这没有油香味的面饼,他拿不定主意了,“到底坏没坏?吃是不吃?”
“过期了,过期了,千万别吃了。”谢大伟钻了进来。
他吓了一跳,猛地仰起头来。
谢大伟很魁梧、很高大,把他眼前的光亮遮黑了一大片。“你怎么来了,今天又不是周末?”
谢大伟说:“俗话说,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
“都当领导了,还这么泄松,还满口的山里土话。”
“当着您老再不说家乡话,就没地方说去了。”
谢大伟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带来了不少货色,让谢五龙惊叹地说:“不年不节的,你这是干啥?”
“今天是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祖的日子。”谢大龙一边往外掏东西,一边说:“如果搁在老家,就要到祖坟上去进贡、烧纸,即便是在这里的街道,人们也会在路边画个信封、写上世祖的名字烧些冥钱。但是,我既回不了老家,也不能当街烧纸,毕竟是机关干部嘛,不能污染环境、更不能搞封建迷信。我一想,虽然不能祭奠先人,但身边就有家族的前辈,敬奉敬奉,跟回家祭祖没什么两样。”
谢大伟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在窄桌上。熟食、点心应有尽有。最有意思的是,居然还有一瓶子酸黄瓜,一袋子玉米面窝头。
十几样东西把一张小小的桌子撑满了,谢五龙说:“你这都是供品啊。”
谢大伟说:“对,供活人比祭祖强,因为活人他都能吃上。”
真空包装的食品,一打开就搁不住了,依节俭的天性,他们只打开了一袋酱肘子、一袋原味花生米。由于桌子已有承载,所以爷儿俩席地而坐,迫不及待地喝。
一瓶酒很快就喝完了,谢五龙又拿出一瓶。谢大伟拦住他,“咱们点到为止,因为您是看门的,不能喝醉了。”
“我不瞒你说,你婶子不在身边,我就跟个出家人似的,整天介修身养性,身子骨比年轻的时候还硬朗,放心喝。”他在地上走了两圈,步履稳健,看不出跛来。
“对了叔,我忘记带酒了,您的酒还够不够喝?”
“我昨天数还有十五瓶呢,即便是两天一瓶,也能喝到八月节。琢磨着你忙,算计着你即使平时不来,八月十五肯定来,酒就接上了,没想到你七月十五就来了,嘿嘿。”
“那我明天再给你送一箱来,甭省着。”
酒喝到有些飘飘然,谢五龙说:“大伟,叔对你有点儿小意见,我住得离你们家那么近,你却不请叔去你家认认门,是不是有点儿那个?”
“您是看门房的,不能离开门房去串门儿,咱是脸薄的人,不能破了规矩让人说,这既是替您着想也是替我着想。”
“不去认门儿,给个门牌号也成啊,别让叔守着就地的家人还两眼一抹黑。”
“您的性子我知道,如果给了您门牌号,您脑袋一热,就管不住自己了,肯定会找了去。”
“你是觉得你叔是浑身泥土的山里人,上不了台面,怕惹侄媳妇嫌弃,脸上不好看。”
“您这就想多了,我是觉得,我家里有孩子,您又是长辈,到家里肯定要给孩子买吃食,而现在儿童食品又很贵,我不忍心您破费。”
“你是心疼我挣得少?”
“难道您觉得挣得多?”
话说到这儿,谢五龙摇摇头,“既然你知道我挣得少……”然后不停地嘿嘿笑。谢大伟觉得他表情怪异,肯定有难为情的话要说,便鼓励道:“您有话就说。”
“既然你催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谢五龙低着头,说道:“你看,我家你兄弟借了那么多债,而我又挣得这么少,我是说,我是说,你能不能借给他点儿?”
谢大伟听了,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依旧笑着端起酒杯:“叔,我先敬您一杯。”
谢五龙感到难为情,只是轻轻地抿了一下,而谢大伟则一饮而尽,依旧笑着说:“我兄弟创业背债,虽然是坏事儿,却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他会从中吸取教训、增长智慧、磨炼意志,今后会更成熟、更会经营。所以,他欠的钱,由他自己还为好,这是让他有尊严、懂担当。说实话,您老人家含辛茹苦地帮他还钱,我就觉得您为儿女做马牛的心思太重了。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出来打工,想想就让人心疼。用挣来的钱养活我婶儿和您自己,不给儿子添麻烦,本身就是在帮我兄弟了。他欠的外债好还,他欠父母的内债,还得起吗?所以,我还得提醒您,您每月开了工钱,不要让他直接就拿走,你要拿在自己的手里,那是您和婶子的养老钱。”
谢大伟给自己满上酒,高高地举起:“叔,来,我替我兄弟敬您。”
谢五龙不知这酒什么寓意,忍不住站了起来,想想走两步,舒缓一下紧张的心绪,但一迈步,就觉得左腿又短了,不争气地跛。
谢大伟一笑:“你还是坐着喝吧,这事儿以后再说,先把酒喝透。”
最后,酒是喝透了,但却没说这钱到底借与不借,弄得谢五龙反而难以再张口了。“甭老是惦记着我,你忙。”
“那哪儿成,您住在这里,就跟我爹住在这里一样。”谢大伟的眼圈有点红,急急地走进夜色。
陆
谢大伟走后,他把自己扔在那个破沙发上,满脑子的迷惘。他觉得谢大伟说得对,我为什么非得给儿子当牛做马?唉,谢大伟对他嘘寒问暖,关心体贴得一如亲生,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正因为这一“浓”,让他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唉,亲情这个东西虽然是个温软和贴近的东西,但里边却也有冷与远的东西,而且还说不明白。以前就有感觉,今天怎么就忽略了?看来,自己真的老了,不懂情理了,甚至越来越自私了。
谢五龙越想越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得寸进尺不厚道,他不停地自责,“这人活的,嘿嘿……”
这时,石棉瓦上又响起了叮咚叮咚的声音,这个声音还是很稀落,有一搭无一搭的。一颗硕大的檐滴落在他的脸上,接着又一颗硕大的檐滴滴到他的脸上……润湿让他清醒了,也心安了——唉,这亲情或许就如这檐滴,一颗一颗滴下来,感受到润湿,惬意在当下就成了,可别让它下成大雨,那么,就没法在这沙发上坐了。
(作者:凸凹,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文联理事,著有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大猫》《京西文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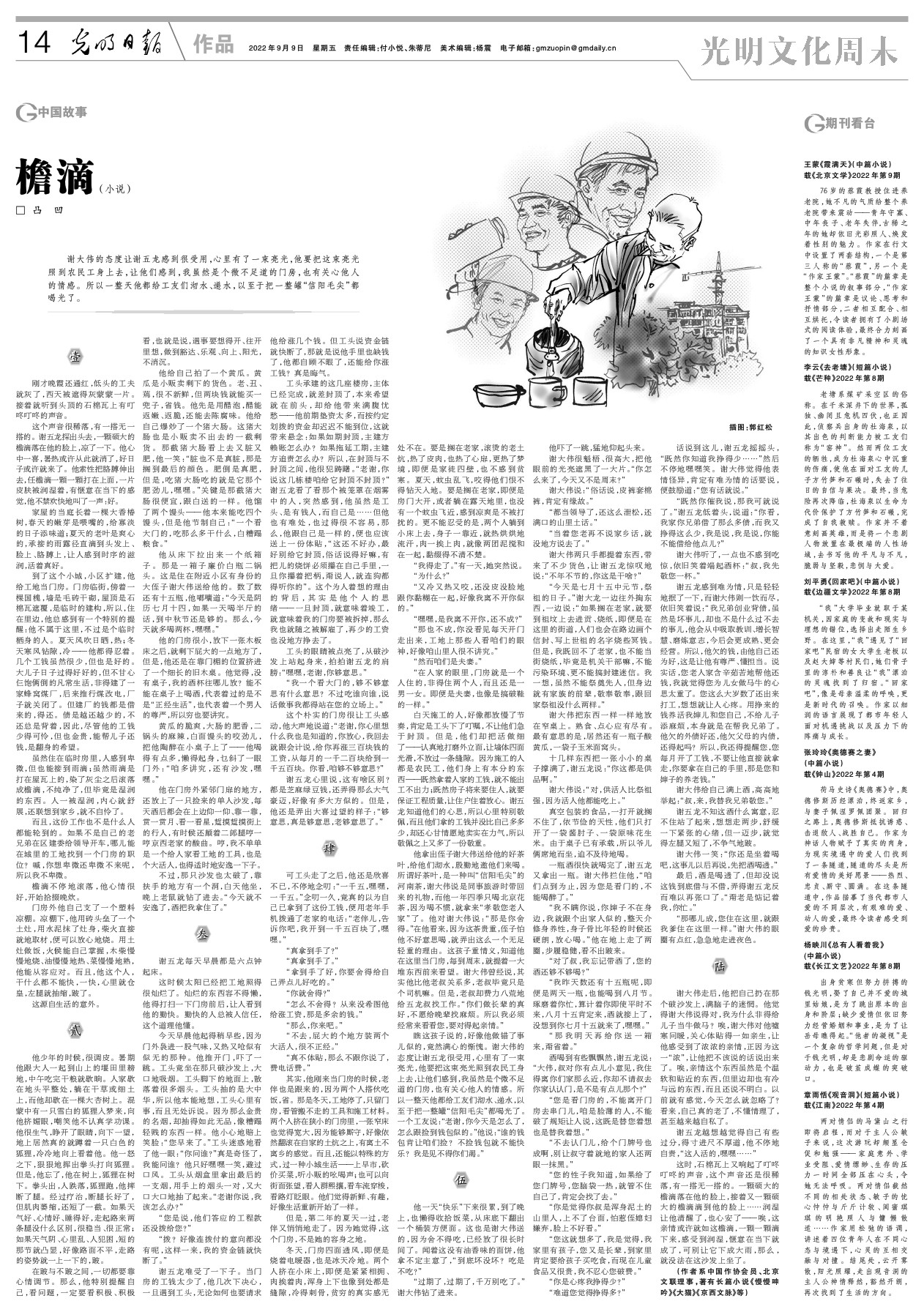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