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记,“现代小说”这一强势文体正式迈开了她的中国征程。一百多年来,与中国迈向现代性的步履同频,中国现代小说同样肇始于对世界的全面学习。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真诚学习中,中国文学获益良多,同时又日益感觉到其与我们的集体经验和生命感受在某种程度上的违和。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相较于我们这个如此古老与悠久的文明,“现代小说”终究需要完成“中国化”,以期更为准确地回应中国人自己的现实,契合中国人自己内在的审美特质。
这个判断,想来如今已有不少相近的观点,但观点的形成与佐证,尤为需要具体实践的印证与激发。回到文学创作的现场,我们需要有具体的作品来达成认知的共鸣。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恰好回应了我对“小说艺术‘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思考。
这部小说,凡50万字,我通读了两遍。是什么驱使了我的阅读?当然,这是一个“工作”,对于重要作品,我需要去阅读;并且,再次阅读,也是带着“问题”的,我意图在作品中读出文学创作现场阙如的某些因素。但最为根本的是,我被作品本身所吸引,是那种我们称之为“快感”的阅读感受。这更多是受着感性的支配,其中“感性”亦可置换为“文学性”。
当我将这次阅读体验里的“感性”与“文学性”挂起钩时,我知道,我已经面临着某种文学观念的辩难。那个似乎已根植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根植在我们的审美准则中、铁律一般的“文学性”,长期以来左右着我们的基本判断。以此,我们可以罔顾一部作品的广泛流传,甚至罔顾自己在阅读时的“感性”反应。我们长期所倚重的,实则都是某种“他者”的标准。我绝非要否定“他者”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想要说的是:如今,困扰着我的,也许是“我”在哪里。
这次,我在《长安》中看到了“我”。这个“我”,当然首先关乎我的个人经验。作品中所描摹的那座军工大厂,直接与我的生命经验吻合,它在现实世界中,就坐落在我童年的生活环境中。由此,我才能读出阿莹是以相当准确的笔墨、相当标准的“现实主义”笔法,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物理的世界。其次,这个“我”也关乎“我们”共同的经验。这个“我们”,对应着的是共和国的人民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长安》是一部共和国完成自身工业化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风起云涌,放在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来看,都有着非凡的书写价值。再次,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最为至要的,这个“我”,神奇地对应了一个中国读者内在的审美密码。
阅读《长安》,我读出了《水浒传》这般的“中国式”笔法。如果说,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塑造,遵循了“现代小说”的一些规律,它更多是以一种“绣像式”的中国笔法在描摹着诸多的人物。忽大年、忽小月、黑妞儿、黄老虎、连福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几无西方作品的范式,他们更像是传统文学中依赖绘画手段“页子”造像一般的人物:不做过度的人为评价,少有冗长的心理分析,每个人都是行动着的,并且由行动本身表达着自己,以此构成了唯有“故事性”才有的吸引力,并且,在行动的故事中,天然而然地具备了人的个性美。
及此,我想到了创刊于1903年的《绣像小说》。李伯元主编的这本中国近代小说期刊,宗旨明确:发挥小说的“化民”功能,便于群众阅读理解,努力使小说通俗化,在所载小说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绣像,配合小说故事内容。其所刊小说内容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现象,意在使人民群众脱离愚昧走向清醒的境地,了解并憎恶现实,利于改革现状,自求生存。
“便于群众阅读理解”“使小说通俗化”,这些指标是不是与我们所秉持的某种小说观念相左?当一百多年前的李伯元立志如此“化民”之时,是否也要经受那个“文学性”的捶打?而对于《长安》的阅读,令我不能不重新反思某些既有的立场。当我们因了“文学性”之名,多多少少拒绝“群众阅读理解”与“小说通俗化”的时候,是否已经暗自将自己放在了“化民”之“民”的外面?这个“民”,难道不是“我”,不是“中国人”吗?
历史经验不是简单的重复。于今,中国人所面对的世界,也早非光绪二十九年,但“中国性”这样的命题,从来都不应该脱离我们的视野。“便于群众阅读理解”“使小说通俗化”这样的问题,《长安》都给出了富有启迪的答案。阅读这部作品,你绝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如果阅读的快感即是“通俗化”的表征,那么,“通俗化”就不应当被粗暴地否定。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以这样一种有别于“现代小说”念兹在兹的那种“文学性”,实现某种中国化了的文学性。
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被赋予“载道”的重任,但实践起来,时时感到力不从心,那么,是不是我们所秉持的某种“文法”,与我们的所欲之“道”,有着某种天然难以匹配的方向?解决这一文学困局,也许能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中获得启迪。中国式的、绣像的、便于理解的《长安》,给出了一个方案:原来,历史变局的叙写,宏大的时代主题,复杂的人性想象,是可以这般符合中国人内在文化观与审美习惯地来表达。而且,在充分表达“人”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时代的主体意志,在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中,也能高扬壮烈的牺牲精神与理想主义的道德诉求。
(作者:弋舟,系小说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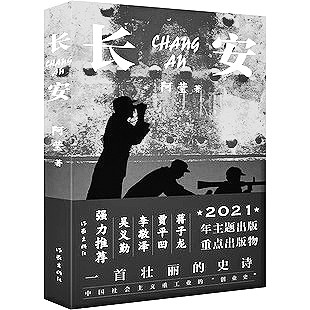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