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与人没结过死仇,即使严重伤害过我的人,经历数年以后体恤了他的年长,就可有些许谅解。再加上从个人方面找原因,当年年轻气盛,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这样一来,原来的创伤便归于平淡。
但是,对于一种食物,一种平平常常、本性柔和的食物,我记它的“仇”,记了好几十年,晚年才将仇怨解开。
白薯。
不明就里的会问:你跟不通人事的白薯较什么劲啊?
这当然要先给你讲明身份,扒了皮让你看。就出身来讲,人家有“书香世家”“官宦世家”“豪门世家”,都特别体面。我的出身是什么呢?白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往上数,就以种白薯吃白薯为传家之宝,我也以白薯起身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由小到大,我的血管流淌着白薯催生的血液;我的性格恪守着白薯做派里的耿直和温婉。
它养育了我,也蹂躏了我。爱它恨它若不至极点,是写不出这么一个题目来的。
在往日农村,我也算是个有志气青年。对于宿命,采取抗争态度。自己订立的检验标准以白薯为界限,作彻底摆脱旧困,争取到新生的区别。简易清楚的表达是“跳出白薯锅,不再吃白薯”。这对当时心存志向的农家子弟来讲,是最易产生的动力。纲领虽然低,但它是从现实出发,跨越宿命,能够显示心灵成果。至于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祖上没有人传授,我也想不到那么奇特。最低纲领于我,比读书饱食者向往人生的高级目标更具有激发作用。
浩茫心头,纠结不休的白薯,于我有恩,有爱,有苦,有乐,有愤懑,也有凄惶。哪一个方面,都是真实的。待我把它们梳理出来,你或许明了我的怨气从何而起了。
爱与乐
爱与乐都和母亲做出的白薯饭食有关。
这么一说,童年的快乐情景就在心头跳跃。
现今的儿童可能没听说过“糖稀”吧?在我心里那可是最具有诱惑力的食物。
它是蒸白薯的副产品。蒸过的白薯挨个取出来以后,锅底会汪着一底儿黏液,它是鲜白薯里的糖分和水分一同蒸馏出来的。它的颜色比蜂蜜颜色深,糨糊状带亮光儿,而黏稠度却甚于蜂蜜。扎下一筷子拔出来,糖丝拉得很长。这对于平时吃不到糖的农村孩子,可谓天然的美食。
守着铁锅,我一筷头一筷头蘸着它嘬。母亲笑眯眯地瞅着我。她收藏着我的快乐。
糖稀,大人是不吃的,只留给孩子。吃糖稀回数多了,我也长经验,这东西趁出锅时热着吃好,一放凉,它就凝固住,一旦凝成了坨儿,拿筷子就再也挑不动了。
从吃上寻到快乐,还有烤白薯片儿和烤白薯。
烤白薯片儿是把鲜白薯切成片,放炙炉子上边烤。土窑烧制的炙炉子,与深砂锅形相似,用途上大有区别。砂锅是容器,而炙炉子只外壳起作用。它器形如一面鼓,顶部略微凸起,分布稀疏得当的圆坑,而坑儿又不穿透,比别处只薄了一点儿。如果没有那些坑眼,把它倒扣过来,它就与砂锅一般无二了。
需要烤的白薯片儿,在烧热的炙炉鼓面上摆开。火候别太大,火候一大就从坑眼把薯片燎了,造成煳不抡吞,吃着咔哧咔哧,不熟。慢火烤,时不时给薯片翻个儿。在这过程,特有的薯香气味就软软地发散在屋里边了。
烤熟了的白薯片儿,十分柔软,它上下两面都有被炙炉坑眼烙过的痕迹。那痕迹特像小孩接种麻疹疫苗以后皮肤上花朵似的瘢痕。
烤白薯片儿,只烤一炉是不行的,不解饿,也不解馋,非得请求母亲烤上两炉。
也叫炉白薯的烤白薯,更离不得母亲协助。使用煤火很重要。要先摊一铲儿湿煤,把湿湿的煤泥蒙住火苗,不使火焰外泄。全蒙上了,围绕炉盘摆放薯块。薯块别太大,挑选顺溜的。摆放也要细心,让薯块你挨着我,我搭着你,相互插紧。底层码稳妥了,上边再码一层,料定不会散架了,严严实实扣一个铁锅或者一个大砂锅,不让跑气儿。
整块白薯炉熟,靠铁炉盘的热度和扣紧铁锅以后四围的热气烘烤。其间上下两层调换一次位置,费一些工夫。但烤熟了的薯块比任何吃法都香浓。紧绷绷的薯皮松开了,有的还向外流油,轻轻一剥,薯皮就剥下来了。—股香气直扑脑门儿。你会看见薯肉上边有红色经络,真跟肉儿—样。你得捧着吃,还得慢着吃,它烫,咬进一口热气嘘嘴。非要急着吃,咬入口的薯肉就得在嘴里倒换,从口腔左边移到右边。吃了两块烤白薯以后,你会觉得手指发黏,几个手指头粘连得快挣不开了。
同是在炉盘上处置白薯,还有一种方式不叫“烤”,叫“熥”。它是蒸熟过的白薯延续加工。往往在入睡之前,把煤火封了,让火劲顺着烟道烧暖土炕,灶台上搁着中午吃剩的蒸白薯,什么东西也不扣,平摆浮搁,只是不让它离火眼太近。只接受徐徐的烘烤。睡了一宿以后,那白薯也熥出了样子。耗去许多水分的熥白薯,它皮肉紧缩,带竖褶。没离被窝儿,伸手来一个,皮蔫儿皮蔫儿的,特别有咬劲儿,我们管它叫“牛筋白薯”。
上小学的时候,书包里装的牛筋白薯,是我的最爱。
当然,吃鲜白薯还有更好吃的方法,那是“拔丝白薯”。把白薯片切成菱形小块儿,放入熬化了的糖锅,起锅放盘子里,拿筷子搛它会带出金黄金黄、长长的糖丝来。但这吃法奢侈,我家穷,一年也不得吃上两回。
小小年纪,我就懂得了有关白薯的知识——储存了一冬的白薯最好吃!
刚刨出的白薯,水汽大,发“艮”。无论怎么吃,都达不到冬储白薯的效果。为何呢?它缺少所含淀粉糖化的过程。白薯入窖,空间变暖,有利于糖分转化,它从汗毛孔(芽腺)沁出一些水汽,潮乎乎的。我爷爷把它叫作“发汗”。水汽减少,甜度定然增加了。
我这般得意扬扬,甚有成就感地介绍鲜白薯的吃法,现在的儿童没这机会了。原因就在于煤火取消了,传统炊具没有了,变换为清洁能源和电气炊具。即便炙炉子还有,用液化气的火苗去烤薯片会串味儿。更何况液化气的炉盘根本熥不了牛筋白薯。烤箱也能烤白薯,但烤出的味道你能吃出用煤火烤出的那人间烟火味吗?像我过去那样,在母亲慈爱的目光里,感受到身为孩子的快乐和幸福。
不单吃鲜白薯让我念念不忘,白薯干儿面也让我非常留恋。
白薯干儿面当然是白薯干儿碾成的面粉。它是在大秋时候把存储过剩的白薯和受创伤不能储存的白薯切成片,在空地或房顶上晒干,干透了收集入囤。这其实是储粮的一种方式。
白薯干儿出粉率是很高的。碾一遍,筛一遍,最后剩下不多的渣滓。
碾成的面是什么颜色呢?告诉你吧,淡红色!用手指在面笸箩里蘸一蘸生面粉,舌尖舔一舔,它甜!若扑下身在碾盘满口地舔,干干的面粉甜得还有些呛嗓子呢。它以后做成的无论什么饭食,都脱离不了这个颜色和甜味。
我母亲有一双巧手,我感恩我的母亲给我做过多种多样白薯干儿面饭食。
擦格儿。轧擦格儿的器具为木框和带窟窿眼的薄铁板组合。低矮的木框呈井字形,架在锅沿上,镶在木框上带细小圆窟窿眼的铁箅子对着锅的正中。和好了面,锅里的水开了,揪一疙瘩面团放进擦床,然后用跷跷板一样短粗短粗的木杵在上边来回碾轧,通过窟窿眼挤出来面条。那面条又短又细,长约三厘米,它蜷蜷着,捋不直,就像蜷曲的小蚯蚓。
捏格儿。器具是铁片卷成的圆筒,高度一拃左右,分内外两件。套在里边的铁筒平底,外边的底部有许多窟窿眼。关键是在“捏”。一块软硬适度的面团放入空筒,两手各三个指头掐住外筒的耳子,上下正反给力,用平底的筒儿不停顿地往下压,圆面条就缕缕地捏出来了。如果和面不巧硬了,几个手指会掐得酸痛。它在锅里滚两回,用筷子挑一挑翻个个儿,就能捞了。一捏格儿能够捞一碗,每锅都要轧两捏格儿。
摇嘎嘎儿,那名字就嘎。那是把面团擀成饼叠起来,切成小方块,厚度约莫小指头肚的一半。把小方块儿撮入簸箕,撒上不使它粘连的泊面(玉米面),摇。摇的结果,方块的直角变成钝角,不见棱了,就簸进锅里。簸箕里只剩余泊面。它煮的时间比较长,吃起来有咬劲儿,比较顶饿。
猫耳朵。白薯干儿面适合做猫耳朵。白薯干儿面黏,把面和硬一些,擀薄了切开,捋直了卷成筒状,使用刀尖部分一丁点一丁点往外抹,用力不大,但腕子劲要巧。碾出来的效果,个个薄面皮抠抠着,半张开,我看它不像猫的耳朵,像伊拉克蜜枣儿。
其外,还使白薯干儿面蒸窝头、做烙饼、切板条、摇球、蒸大馅团子、包饺子、稀面带萝卜丝的拉拉鱼儿汤等等。一家一户多是这么些吃法,而农家的红白喜事办勾当,那就像招待大队兵马,盘大灶,架大铁锅,烧硬柴,吃白薯干儿面轧饸饹了。
我母亲除了会做白薯干儿面的各种饭食,她还会在传统模式上创新,让你更得下饭。她真是一个能持家的好手。
我吃过白薯干儿面,只是对白薯干儿面烙饼缺少兴趣。这种烙饼因为不使用油,所以不起层儿,粗粝得难以下咽。略微一放凉,它又变得干硬干硬了。还是蒸煮方式的好吃。蒸煮的都有入口爽滑的特点。尤其煮着吃,略微过一遍凉水,去一去黏度,捞上碗浇上黄花木耳或者茄丝卤,就着小葱或者青蒜,一边吃一边鼻子尖冒汗,那才叫一个美呢!
怨与仇
我本家一位家境比我们好的拐爷爷,领着我去岳母家提亲,就我家经济状况向我岳母陈述:没有大福享,也没有大罪受。
当我面说的这话,我听着不舒服。
他说的很中肯,但不知晓我的志向。
他的认识,停留在我们的“白薯世家”上。
不说东街,整个坨里村,谁家有我家的白薯多呀?名冠全村。井窖里有白薯,敞窖里有白薯,空房子里有大囤的白薯干儿。这都是我爷爷、我父亲和我们小辈用勤苦换来的。
白薯本来不作主粮,和小麦、玉米、谷子根本比不上。在城镇它属于菜蔬一类的东西。国营粮站收购白薯,四斤白薯才抵一斤粮票,找给两毛钱。兑换成的粮票只许买玉米面,买不成白面。因为家家具备籽粒特征的粮食少,它就更成为“保命粮”了。
乡下人口中,“大挡戗”是对它的尊称。
谁愿意总吃“大挡戗”呀,吃一天,就证明你过穷日子一天。
白薯是亩产能够达三千斤以上的高产作物,为了多产白薯,我爷爷和我父亲太辛苦了!一亩四分地的山坡自留地,因为种白薯最高产,根本容不得倒茬。招地时,招的深、暄实;施肥时,施的大,把最好的粪肥用到白薯埂上;除草时,除的勤,不容一棵高草争肥。栽白薯是一场大战,爷爷负责培埂、招坑儿、栽秧儿、埋埯儿,父亲负责挑水、浇水。哥哥和我也去支援。我俩都挑不动水,就合着抬一桶水,抬水上坡。别人家只浇一遍水就得,我们家为了薯秧保活,浇两遍水,并且哪遍水都浇足。头遍水全渗了,才给浇第二遍水。我记得一桶水浇一次,浇足量了,只能浇二十几棵。一亩四分地的白薯,几千棵秧苗,需要担多少次的水啊!
光是小嫩肩膀抬水,把我都抬怕了。
盼着秧苗成活,盼着缓秧,盼着薯藤爬蔓儿,盼得心急。可每年的“五一”前后总会刮一场大风。大风把小苗都刮成了光杆儿,刮趴下。它蔫蔫的,我像大人一样揪心。
霜降节气,该收获白薯了。又是全家出阵。我刨不动,负责归拢堆儿。这时会听到父亲多次惊喜的叫喊:“过来看,瞧一瞧这个‘大挡戗’!”
一块二斤多重的白薯,拨拉到他脚面,他的笑口咧到了耳根台。
收白薯时,全家是欢腾着的,而往后的日子,天天吃白薯,顿顿吃白薯,却是我最憷的事情。
生产队分白薯,自家产白薯,白薯存量大,储存得好,我家白薯能从头一年的大秋,吃到来年五月。算算吧,七个多月时间吃的都是白薯。
冬春两季,早晚常规性的白薯粥,中午蒸白薯,硬食稍有变换,吃一顿小米饭,捞出饭的米汤里又熬了一锅白薯块儿。我见着白薯,心口就发堵。
哪有什么好菜啊,入秋以后熬白菜、熬萝卜条,少油没酱的,连焌个葱花都没有,光是一把盐的清汤儿。冬仨月,我家九口人的菜,就靠咸菜条。顶多顶多,浇上一勺儿干辣椒油。那口大咸菜缸,现在还留着,它昔日的容量,一次能腌三四百斤青萝卜和蔓菁。
白薯吃多了,烧心,口里常控出酸水儿。
而且它不禁饿,我们叫“不拿时候”。没多大时辰,肚子就空空如也。
但是,有它,就不至于饿死。
我是那么厌恶白薯,而与我同龄的非农户同学却看着白薯香。有一个姓崔、长得很俊的男同学,一次主动提出用一个馒头换我一块白薯。我当然愿意。当着我面他把白薯吃了,而我则揣起这个馒头带回了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过饥饿。连续三年大旱,全国闹灾荒,全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北京城里居民下农村捡白薯须子、白薯秧子,挖白菜疙瘩。大多数农民靠借粮,提着条空口袋东借西借。
我们家的情形好一些,虽然白薯粥掺和倭瓜、蔓菁丁儿了,原先筛剩下的白薯干儿渣有新的用项,掺进稀稀的玉米糁粥了,却没断顿儿。
母亲也看出我吃白薯、喝白薯干儿渣稀粥的委屈,她在全家人面前,眼神表现出小心翼翼,似乎做不出好饭食是她的罪过。
我老早就知道为家庭生活出力了。
中学毕了业,家里缺煤,去很远的矸石山捡煤。去的人多,捡不着煤块儿,少年只是用小铁筛子翻腾煤矸石下边的黑面儿。然后装入帆布口袋,背下山。—去一天,带的干粮是蒸白薯。高山上,大风呼呼地刮,冷风从裤腿底下向上边灌,冷透了身子。手早拘挛了,鼻子和脸生疼。当作午饭的白薯,冻得邦邦硬。抡起来完全可以当手榴弹。那也要吃。两颗兔子牙一般的大门牙,上口一啃,只会勒出两道白印儿。根本咬不下整口儿的来。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身在高山做苦工,冷风吹着,想想比城市同龄人多得多的寒苦,悲愤啊!
从那时起,我就仇视出身,仇恨白薯。为了逃离农村,特想去当兵,因为那是有志向的农村青年在当时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可能由于改换命运的心情迫切,连续三年参加征兵体检,都是因为血压高,被刷下来。
命运让我走不出农村,吃白薯的苦就得受着。那一段漫长的经历,我谓之“苦大仇深”。
有白薯吃没有饿死,却对白薯充满了仇恨,这一类型很像魏延脑后长的反骨,早晚证明他的叛离;也像说升米养恩、斗米养仇,那种人没出息。但于我,的确是那样叛逆。
我还得声明,虽然我与白薯为仇作对,但未与窝头结仇,从来不拒绝窝头。家常饭里玉米面净面窝头是上等食物。在过去年月普通农家也不是轻易就吃到的。
又很多年,我手上也有城镇居民的购粮本儿了。凭个人不懈努力,最低纲领实现了,曾吃种田饭、转寻卖文钱的本人,更有名义消除白薯,更加强化不吃白薯的信条。入超市上集市,一见白薯,心理上冷漠得厉害。
可是啊,命运真的会捉弄人,老了老了反而想吃白薯了,重新回到本命食轨道上来。家里没地儿种,去超市或集市上买。老远见了烤白薯的小贩,从老远鼻子就一劲儿地吸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谁发明的?真对!
捧起来一块烤白薯,如见故人,情形宛然“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一般。
你根本想不到,今年的春节我是怎么过的,吃啥都不是滋味,就想吃白薯。春节几天,白薯是我的主食。
去大街买白薯,遇见一个面孔似红皮白薯、卖白薯的外乡妇女,她看我像个吃主儿,跟我喋喋不休,从品种到口味推荐她的白薯。
我见她没完没了地兜售,心说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回敬了一句:“我是种过白薯的!”她不言声了。
(作者:董 华,系北京市房山区坨里村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草木知己》《大地知道你的童年》《十里不同乡》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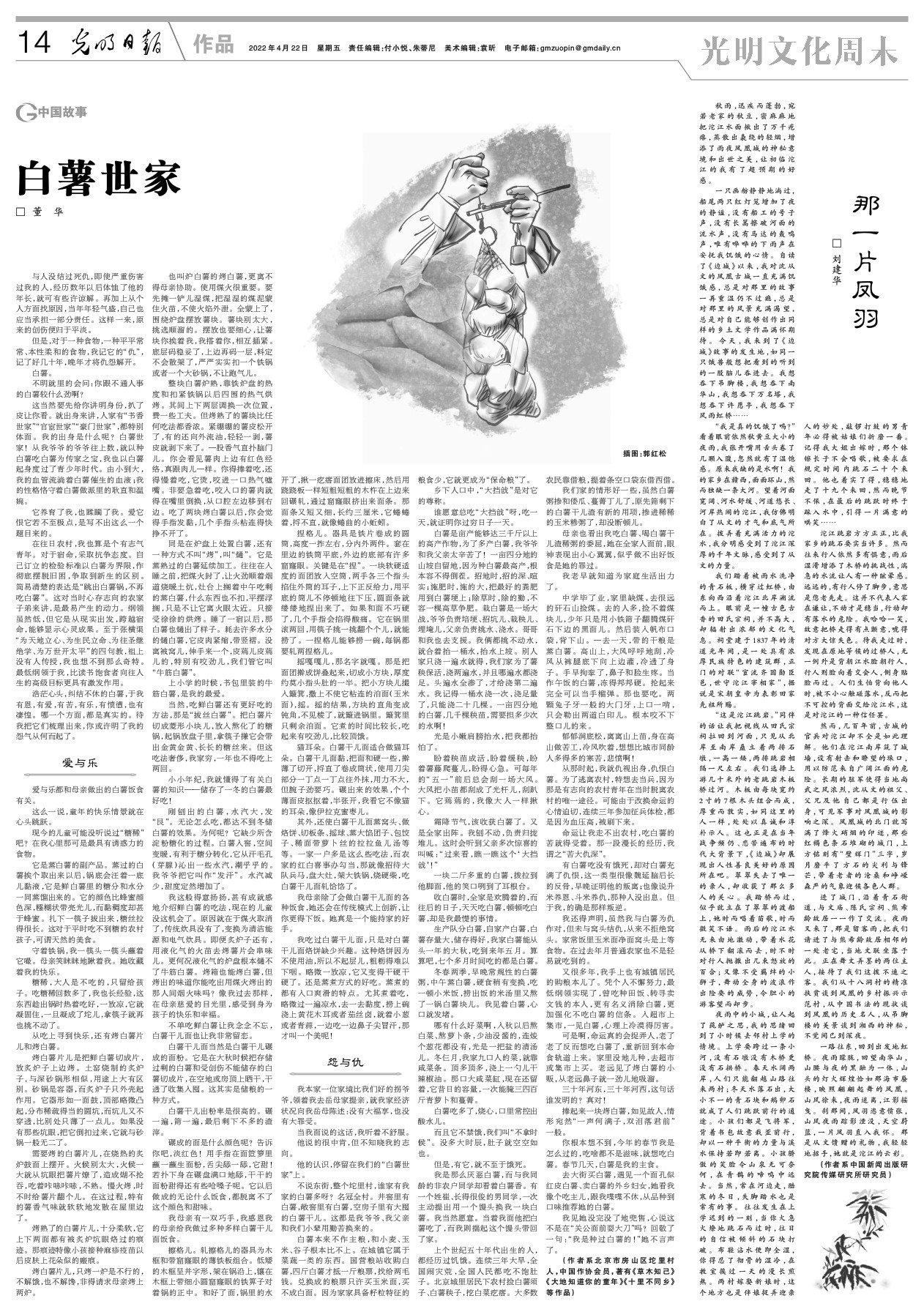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