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以来,人们对口吃并不了解,因而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对口吃的污名化更是给口吃者带来很大的生活和精神负担。
近年来,随着复杂的脑成像技术出现,科学家开始认识到口吃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与普通人相比,口吃者大脑中一些特定的、连接多个脑区的神经纤维并不完整,一些神经递质的活性存在异常。
基于这些研究,科学家开始使用针对神经系统的药物来治疗口吃,但这些疗法还需经过更多的检验。
1、麻烦的口吃
李·里夫斯(Lee Reeves)一直想成为一名兽医。他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区读高中时,曾在一个周六早上去一家离家较近的动物医院申请工作。当时,医院正处于繁忙阶段,接待人员告诉他兽医太忙了,没时间接待他,但是里夫斯决定等一等兽医。3个半小时后,兽医看完了所有就诊的狗和猫后,接待了他,并询问里夫斯能做什么。
从3岁起,里夫斯就有口吃,回答问题较为困难。“我明白自己想要这份工作,但是当他问我的名字时,”他说,“我无法说出自己的名字来拯救自己。”最后,兽医伸手拿了一张纸递给里夫斯,让他在上面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但兽医告诉他目前还没有适合他的工作。“我记得那天早上走出诊室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里夫斯说,“我不仅永远不会成为兽医,甚至连清洁笼子的工作都找不到。”
50多年过去了。现在72岁的里夫斯已经成为了一名有影响力的、为口吃者发声的倡议者,但昔日的沮丧和尴尬依旧历历在目。这些都是口吃所带来的复杂体验的一部分。口吃是指轻松、流畅的口语表达被迫中断,由于口吃通常伴随着生理上的挣扎和情绪变化,这常会导致医生将其错误地诊断为舌头或喉部缺陷、认知问题、情感创伤或紧张,而其中最不幸的是,将口吃归因于糟糕的家庭教养。弗洛伊德派的精神病学家认为,口吃代表着“口头虐待冲突”,而行为主义者则认为,给孩子贴上口吃的标签会加重他们的口吃症状。医生曾告诉里夫斯的父母,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口吃上,只需耐心等等,口吃就会自然消失。
不过,这些关于口吃的谜团和误解已经被揭开。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在近5~10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口吃本质上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具体而言,它像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在全球7000多万名口吃者中,大多数患者的口吃症状会出现在学习说话的阶段。通过观察口吃者的大脑,科学家发现和正常人相比,他们的大脑中存在细微的结构和功能差异,会影响语言流畅性。口吃者在神经连接、语言和运动系统的整合方式,以及多巴胺等关键神经递质的活性上,均与正常人存在差异。
口吃的出现同样离不开遗传学因素: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4个基因,它们极大地增加了患口吃的可能性。就像当灯泡闪烁时,有时并不是灯丝坏了,而是房间里的线路出错了。这些错误整合起来,就是神经科学家所说的大脑“系统层面”的问题。
神经生物学的发现催生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目前,一种针对多巴胺过度活跃的药物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他治疗口吃的药物也正在研发中。近期一些研究显示,脑部刺激或许可以有效改善口吃。考虑到神经可塑性对幼儿的重要性,目前专家们建议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治疗口吃,而不是观望。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语言病理学家J.斯科特·亚鲁斯(J. Scott Yaruss)说:“这些关于大脑的研究证实,我们需要尽早对口吃进行干预。”
我们对口吃的了解还不全面。口吃影响了大约1%的成年人和5%的儿童,在这些儿童中有高达80%的人能恢复到可以进行流畅交流的程度。科学家、父母和治疗专家和口吃者本人都想要了解,那些长期口吃和能从中恢复的人的差异在哪里。虽然治疗能给予一定的帮助,但似乎不能解释这种情况。一些针对口吃儿童的长期研究或许能解释这一点,目前这类研究才刚开始获得结果。尽管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些和口吃相关的基因,但尚不能确认它们的功能。
随着对口吃的了解逐渐深入,研究人员和治疗专家希望能深入理解口吃出现的生物学原因,从而改变社会对口吃的偏见。许多口吃者没有工作,还患有社交焦虑障碍和情绪障碍。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分校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杰拉尔德·A.马圭尔(Gerald A. Maguire)本人就患有口吃,他致力于了解口吃,并开发药物来对其进行治疗。但不幸的是,他的弟弟因患有口吃而自杀身亡。马圭尔说:“如果我们理解口吃的生物学机制,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治疗口吃。患者因这种病而遭受的污名很有可能会减少。”
2、从鹅卵石到大脑扫描
数千年前,人们就注意到了口吃,这种现象存在于各种语言和文化中。从古至今,有不少尝试克服口吃的故事。例如,古希腊的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会把小石子放进嘴里来练习演讲;英国国王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接受的非传统语言疗法因为2010年的电影《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而流传下来;演员塞缪尔·L.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会通过说脏话来提高自己说话的流利度。
口吃不同于人们讲话时偶尔或习惯性出现的单词错误。在说话时,口吃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停顿,如重复说某个单词或者在说出的句子中加入多个“啊”或“嗯”。这意味着在进行语言表达时,口吃者和其他人之间的一个潜在的神经学差异影响了更为基础的语言生成过程。亚鲁斯说:“每个人说话都不流利,但只有一部分人会口吃。”
口吃者会经历以下3种情况:延长一个音节的发音(例如在说“man”时,读成“mmm-man”);重复发出某个音节或发音(我-我-我-我-我自己);阻塞,即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如果一个孩子在8岁以后仍然有口吃的情况,那么口吃很可能会伴随他终生。
里夫斯将口吃描述为一种意料之外的失控。“你知道你想说什么,以及如何说出单词、短语、句子结构以及语调的变化,但突然之间你就卡住了,”他解释道,“你不能前进、不能后退,所有的肌肉活动好像都卡住了。”1928年,科学界首次意识到口吃可能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当时,塞缪尔·奥顿(Samuel Orton)医生和语言病理学家李·特拉维斯(Lee Travis)提出,口吃是两个脑半球相互竞争的结果。但马圭尔表示:“口吃者的两个脑半球都很正常。”20世纪90年代,随着先进的脑成像技术的出现,科学家开始能够揭示口吃者与其他人的神经学差异。1995年,马圭尔和同事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扫描了4名口吃者的大脑,发表了第一份关于口吃的PET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口吃者语言区域中的神经活动会持续下降。而其他小型的早期研究发现,口吃患者纹状体(striatum)中的多巴胺水平会升高,这是大脑奖赏回路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基于这些工作,研究人员测试了能阻断多巴胺受体的抗精神病药物对口吃者的治疗效果,发现这些药物能改善一些口吃者表达的流畅性,但它们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如导致帕金森病。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怀疑者认为口吃和大脑毫无关系。马圭尔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提出口吃是一种大脑疾病时,“我有点像是被嘘下了台”。
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通过高科技扫描仪和复杂的分析技术,证明早期那些研究人员的发现是正确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语言主要由左脑负责。相比于不口吃的成年人,在患有口吃的成年人的左脑中,支持语言产生的区域的活动水平较低,而右脑的活动水平反而较高。例如,牛津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凯特·沃特金斯(Kate Watkins)发现,口吃者在说话时,大脑左半球靠近语言区的腹侧前运动皮层(ventral premotor cortex)并不会被激活。沃特金斯等人发现,口吃者和正常人在这个神经区域上存在结构差异,该区域位于连接听觉和运动控制区域的白质纤维束的正上方。白质由神经元的轴突组成,是由神经元胞体发出的、能传递神经冲动的细长突起。沃特金斯说:“它为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提供了条件。”
神经元之间的交流需要神经冲动到达的时间十分准确。为了实现这一点,轴突会被髓鞘包裹,这是一种加速神经冲动传递的脂质。髓鞘完好的轴突束会通常沿同一方向传递神经冲动,就像芹菜茎中的纤维。但是,科学家通过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扫描口吃者的大脑,发现他们大脑中的轴突很可能是交错的。
除此之外,神经递质应该像水沿着平行的纤维流经芹菜一样,穿过白质束。在大脑扫描图谱中,这种神经信号的传递能通过一个参数——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来量化。当FA值越高,白质组织越紧密。在口吃者中,这个白质束的FA值一直较低。沃特金斯怀疑,大脑中原本能获得由白质束提供的神经信号的区域,有时并不会接收到信息,因此不会被激活。在口吃者中,其他一些白质束,例如连接大脑半球的胼胝体,也存在类似的缺陷。
从大脑功能上讲,口吃者的一个神经通路——大脑皮层-基底神经节-丘脑环路(cortico-basal ganglia-thalamocortical loop)——似乎存在缺陷,这也是大脑整合听觉、语言和运动神经信号的基础结构。顾名思义,该通路能将大脑深处的结构,包括丘脑和基底神经节纹状体,与大脑表层的皮层中的各个区域连接起来。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张秀恩(SooEun Chang)说:“说话是人类进行的最复杂的运动行为之一。它依赖于神经回路和肌肉之间毫秒级的协调。除此之外,这个神经回路能使多种运动模式顺利、及时地启动。”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回路被破坏的确切原因,但即使是一些细微的差错也可能导致说话变得不流畅。“一切都在指向基底神经节,它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所在,”马圭尔说,“如果在这条神经通路上有任一过程被干扰,就会导致口吃症状。”
诸如此类的大脑差异可能是口吃产生的根源,或者说,可能是大脑为了试图适应口吃,而产生的补偿性变化。为了分辨上述因果关系,张秀恩跟踪调查了250多名口吃的儿童:从3岁开始,持续跟踪至少4年。其中有些孩子能从口吃中恢复,但有些不会。
2017年,张秀恩和同事报告称,与不口吃的儿童相比,口吃的儿童连接听觉和运动区域的左脑白质的完整性存在缺陷。但在康复的儿童中,随着时间推移,白质会逐渐恢复完整性。张秀恩说:“在康复的儿童中,这一区域的白质会逐渐变得完整且趋于正常;而在长期口吃的儿童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会变得更糟。”
她发现,无论是口吃的成人还是儿童,他们的左脑都会存在缺陷。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在成年的口吃者中普遍存在。她还发现了他们的右脑过度活跃,这是一种后期才会出现的适应性变化。张秀恩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一开始是否存在一种可检测的差异,能用来区分日后可恢复正常的儿童和长期口吃的儿童。她说:“尽早获得这个客观的检测标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将指示哪些儿童长期出现口吃的风险更高。
3、基因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患口吃的风险会通过家族DNA遗传。一些对双胞胎和收养的儿童的研究表明,42%~85%的口吃风险与基因有关。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双胞胎之一患有口吃,对于同卵双胞胎,另一人也患口吃的比例是63%;而在异卵同性双胞胎中,这一比例只有19%。其他的患病风险还包括环境因素(这种非基因因素的影响体现在,在部分同卵双胞胎中,只有其中一人患有口吃)。尽管有些环境因素可以与遗传倾向相结合,但目前,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环境因素究竟是什么。
得益于美国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的遗传学家丹尼斯·德雷纳(Dennis Drayna)大约在20年前开始的研究,一些和口吃相关的基因已经被确认。德雷纳去过巴基斯坦,在那里近亲结婚较为常见,这种做法会在整个家族内增强某些基因的影响(特别是有害基因)。德雷纳说:“我很容易找到拥有很多口吃者的大家庭。”
2010年,德雷纳和同事们报告了3个口吃基因。其中之一是基因GNPTAB的一个突变体,这种基因曾在一种与口吃完全无关的严重的遗传疾病中被发现;另外两个分别是基因GNPTG和NAGPA的突变体。随后,德雷纳收到一个来自喀麦隆的男性在网上询问的问题。他想知道,他所在的大家庭的口吃发病率为什么会如此之高:在71个家庭成员中,有33人患有口吃。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德雷纳找到了第4个口吃基因AP4E1。(目前关于第5个口吃基因的报告还未发表。)德雷纳说,这些基因只导致了总口吃人数中20%~25%的人患病。口吃较高的家族流行率也表明还有更多的基因有待发现,为了寻找这些基因,由澳大利亚科学家领导、22个研究小组参与的联盟正在对口吃人群进行一项新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
目前发现的所有基因都与细胞内的物质运输或者分子运输有关。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德雷纳和同事发现,存在基因GNPTAB(其表达的蛋白参与合成一些新的酶,这些酶会被转移到溶酶体中)突变的小鼠在发声过程中会有异常长的暂停,类似于口吃。他们发现这些小鼠的星形胶质细胞存在缺陷,这类细胞广泛存在于连接两个脑半球的白质束中。一些和溶酶体功能相关的、有助于清除废物的基因的突变,有可能将口吃出现的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基础联系起来。
4、终止污名化
口吃的出现存在遗传学因素,并不意味着它无法得到治疗。最新的研究已经为治疗口吃提供了可能。一些药理学方法正在逐渐完善。马圭尔和同事们认为,利用能降低特定神经回路中多巴胺活性的药物(例如抗精神病药物)来治疗口吃,是迄今为止最有潜力的一种方法。马圭尔已经成功测试了利培酮、奥氮平和鲁拉西酮,这些药物都能减轻口吃的严重程度。不过目前,它们都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不幸的是,这些药物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如导致体重增加和运动障碍。尽管如此,包括马圭尔在内的很多人还是会使用这类未经审批的药物。
马圭尔目前正在领导一项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对一种名为依考匹泮(Ecopipam)的药物进行测试。一些研究曾测试了该药物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的效果。不同于以往的药物,依考匹泮的靶点是一组不同的多巴胺受体。一项小规模试点研究显示,该药物能改善口吃者的语言流畅性和生活质量,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但是,即使是被FDA批准用于治疗口吃的药物,也无法对每位口吃者都有效。马圭尔说:“我们的下一步是进行个性化治疗,弄清楚每个口吃者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口吃并非只有一种症状。”
用温和的电流刺激大脑也是一项很有潜力的疗法。在牛津大学,沃特金斯将无创经颅刺激和已知的改善语言流畅度的方法相结合,比如让一群人一起朗读,或者让人们跟着节拍器的节奏说话。这些技巧已经被证明可以暂时提高口吃者的语言流畅度,其原因可能是外部的暗示促使口吃者开始说话。沃特金斯团队发现,在接受联合治疗的患者中,讲话时出现重复、延长音节或其他口吃特征的比例从12%下降到了8%。但是,在没有接受大脑刺激的对照组中,这个比例没有变化。虽然这项研究的规模很小、持续时间也只有5天,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这些治疗或许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口吃治疗中加入脑刺激可以提升治疗的效果。沃特金斯说:“我们通过电刺激巩固这条通路,使其更有效地运行。”现在,许多口吃者只能接受传统的语言障碍矫正。这些技巧通常包括练习演讲、学习如何有效与口吃者进行交流。语言障碍矫正可能非常有效,但是效果不一定持久。大多数口吃者会在某个时候回到以前的状态。
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口吃的真相,再加上文化意识的改变,近年来,治疗口吃的目标已经从试图根除口吃转变为让口吃变得更容易接受和控制。亚鲁斯说:“很大一部分工作与适应有关。”他把这比作学习滑冰。当你第一次穿上冰刀鞋踏上冰面时,你会踉踉跄跄,感觉自己随时要滑倒。但当你学会忍受这种随时会滑倒的感觉时,也就能更熟练地应对。他表示:“你可以说,当口吃症状出现时,我知道该做什么,这样你就能更熟练地应对口吃。”
这种治疗重心的转变受到了大家的欢迎。54岁的凯瑟琳·莫罗尼(Catherine Moroney)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大气物理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她说,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我基本无法让别人理解我”。语言障碍矫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她的语言流利程度,但这只是暂时的。完成治疗时,她正在学习一门困难的物理学位课程。压力和焦虑不会导致口吃,但会让她的口吃症状变得更糟。
相比于过去,莫罗尼现在的口吃症状减轻了很多。她正在研究云层及其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幸运的是,她的领导只关心她的工作质量。现在,她也在服用抗精神病药奥氮平。“这只是为了让我的日常生活变得简单一点。”但是,真正改变莫罗尼生活的是,她加入了她所说的“我的口吃家庭”。“这可能有违直觉,但世界上最嘈杂的地方是一场只有口吃者参与的会议,”她笑着说,“没人会闭嘴。成为多数人是如此自由。”
里夫斯是美国口吃协会的前主席,也是口吃者自助运动的早期倡导者。语言障碍矫正确实改善了他的语言流畅性,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治疗师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帮助里夫斯改善了口吃带来的精神压力,这一点对里夫斯的治疗至关重要。里夫斯说:“我学会了一种自己能接受的口吃方式。”
他的口吃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名兽医。在里夫斯少年时去那家动物医院的3周后,那家医院的兽医彼得·马尔纳蒂(Peter Malnati)打电话给他,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里夫斯高中和大学期间都在这家诊所工作,后来他做了50年的兽医,为小动物诊治,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得克萨斯州的普莱诺。对现在的他来说,沮丧和尴尬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还有口吃症状。我昨天和今天都会口吃。”里夫斯说,“我希望我明天还会口吃,因为这意味着我还活着。”
(作者:莉迪娅·邓沃斯(Lydia Denworth),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科普作家,同时是《科学美国人》特约编辑;翻译:余文静)
本版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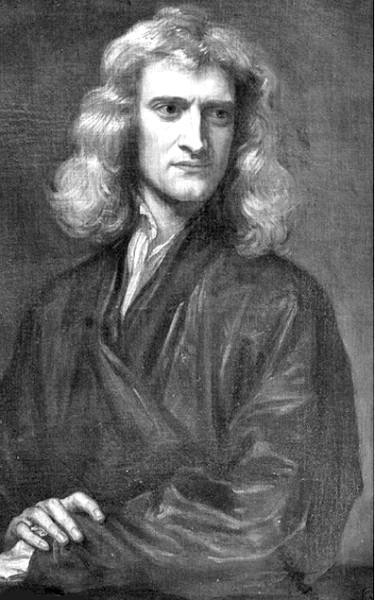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