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顾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斗争的英雄历史。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被改编成影视剧、歌剧等艺术形式,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对青年成长的关注,对青春力量的颂扬,历来是作家艺术家乐于倾注心血的一个重要主题,青春题材作品也是文艺创作序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反映的是退伍青年回乡创业的故事;小说《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下青春的困惑,更写下青春的激情……梳理关于青春题材的红色文艺经典作品,《青春之歌》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青春之歌》以简洁而自然的方式,展现青年知识分子挣脱家庭束缚,迈向广阔社会,从“小我”走向“大我”,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让我们看到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所迸发的强大力量。这部作品先是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尽管艺术形式不同,但其内在始终洋溢着真挚而饱满的激情。
在诸多红色文艺经典当中,《青春之歌》有其独特性。这部作品致力于书写知识分子如何改造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主角林道静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甚至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使她警醒,憎恶不公的本性和追求真理的愿望使她奋发,在经历过懵懂、茫然和挫折之后,她终于能够认定正确的方向,将个人的生命融入民族解放的伟业之中。这个不无缺点、跌跌撞撞的林道静让读者感到亲切,让人们看到一个普通人是如何成长为英雄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青春之歌》拥有着恒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1.书名从“千锤百炼”到“烧不尽的野火”再到“青春之歌”
从北平开往北戴河的火车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在她身边有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杨沫小说《青春之歌》开篇处的林道静。
茅盾在这段文字旁曾经写过眉批:描写太不简练,可以删去。但杨沫并未听从这一建议。这固然是因为她要刻意渲染此时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气质,以使其后来的成长更具意义,却也未尝没有一点个人情感的因素。1931年,17岁的杨沫和她笔下的林道静一样,因抗婚而离家出走,投奔在北戴河教书的哥哥。我们已无从得知当时的杨沫是否也随身带着那样一个行李卷,多年之后创作这部小说时,她在日记中写道:“关节使我痛得成天躺在床上看书,累了就欣赏音乐。我对于音乐的爱好不亚于文学——初中时,我弹月琴、吹口琴,还学过笙、笛。”很显然,那一袭白衣的女子,不仅是年轻时代的林道静,也是年轻时代的杨沫本人。
多年后,杨沫已成长为一名革命女干部,却仍遭受着难耐的痛苦。只是这痛苦并非林道静那样找不到方向的迷茫,而是找到了方向,也迎来了胜利,却不能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的负疚。1939年,杨沫第一次身患重病,那时她正跟随贺龙率领的部队连续行军,黑热病令她终日高烧。但她仍不愿离开工作和战友,坚持不肯按组织安排去北平治病。病根未除,留下长久隐患。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杨沫在日记写下的主要内容就是生病。当时杨沫已调到《晋察冀日报》,报社老领导邓拓让她不要逞英雄,安心养病。她听了却很不高兴,认为领导不理解她渴望工作的心情,也不注意发挥女同志的作用。她的倔强和要强,正和她笔下的林道静十足相像。
新中国成立以后,疾病还在纠缠着杨沫,这让她格外痛苦,痛苦自己不能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多做事情。怀着这样痛苦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真的躺在病床上无所事事。相反,病中闲居造成的敏感,使她频繁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反思自己的成长道路。记忆中的那些人,尤其令她念念不忘,终于决心要写出一部传记式的小说来。
病中阅读的文学名著,显然也鼓舞了她:“今天闲中翻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自述,又刺激我想起久已想写的那本书来。我想还是大胆地写吧!等准备充足再写,是没有日子的。只要起了头,全部精神被吸引进去,那么病呀,一切不顺心的事呀,便都自然解决或者忘了。大胆、大胆地写起来吧!”
但对于杨沫来说,这并不容易。病痛让她每天最多只能工作四五个小时,更多时候是完全无法动笔,她几乎是抱着一种以命相拼的心情来创作这部作品的:“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好不了,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或许对于杨沫而言,尽管自己因身体原因暂时不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能将她记忆里那些优秀的革命者写出来,也是一种工作吧:“我有时想起我那个年轻时代的朋友,他现在正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有时想起他对我的感情——革命的深挚友谊。我忽然想,我应当在未来的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写出他高贵的革命品质;写出他出生入死的事迹;也写出他对我经受了考验的感情……有时我想,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搏斗,他会牺牲吗?我现在的愿望是把他写入我的书中,使他永远活着——活在我的心上,也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但不知我能够写出来吗?”
她写出来了,写得非常成功。这位正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朋友名叫路扬,是《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原型。小说中,林道静被卢嘉川身上真诚、热情、果敢、敏捷的革命者气质深深吸引。然而直到卢嘉川被捕、遇难,两人的感情并未宣之于口,而表现为一种崇高的同志之爱。卢嘉川是林道静从一名迷惘的知识女性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重要领路人,他的身上凝聚了这部小说最多的华彩,甚至超过最后成为林道静丈夫的江华。事实上,卢嘉川不仅对小说中的林道静,还对小说外的无数读者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光彩照人的作品出自艰苦的劳动。从1951年9月25日列出提纲,到1955年4月完稿,杨沫写了3年7个月,三四十万字,最初取名“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大概是,像林道静这样的知识青年,要经过千锤百炼,才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像她这样的青年,在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前仆后继。这两个名字,何尝不是杨沫自己那种顽强的创作热情的写照呢?
1955年年初,小说尚未完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红旗谱》等重要作品的伯乐吴小武,也就是作家萧也牧,就听说杨沫在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立刻联系要来了上半部书稿。中国青年出版社对小说很感兴趣,因为知识分子题材的革命小说在当时相当稀少。也正是这个原因,出版社格外慎重,提出还需要请一位名家外审。杨沫找到剧作家阳翰笙,但阳翰笙实在事务繁忙,拖了几个月,仍无暇看稿。倒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张羽先给出了初审意见。这份意见充分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认为能够赢得青年读者的喜爱,但同时更多谈到了修改意见。分身乏术的阳翰笙抱着歉意,推荐一位专家审读书稿。1956年1月,这位专家给出审读意见,共33条,其中30条都是谈小说的不足。张羽带着意见将书稿送还杨沫修改,此时这部小说已在吴小武的建议下,定名为“青春之歌”。
多年之后,张羽回忆出版社的态度是:“并不是我们不要了,我们是要的,只是需要修改。我们把主动权交给了作者,请她考虑。于是,我们就在家等着杨沫改稿。”那么杨沫呢?从日记看,她的态度是谦逊的:“开始我有些失掉了信心,但后来又平静了。……我决心改好它。”病痛仍在折磨着杨沫,这让她近一个月都无法动笔修改。卧床静思,反让她逐渐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信心,又将书稿送给老战友秦兆阳审读。5月17日,杨沫在日记里写道:“秦兆阳已看过了我的小说。他说好,无甚大毛病。他打算替我拿给出版社。大概已经拿去了。”秦兆阳将小说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此时毛泽东同志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家出版社当即表示只要修改一两处就可出版,还预支了1000元稿费。但因1956年年底开始全国纸张缺乏,《青春之歌》迟迟未能付印,直到1958年1月才与读者见面。
《青春之歌》先在《北京日报》上连载精彩章节,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但不常见的是,北京人艺很快就找到北京日报社,希望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小说单行本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很快加印5万册。3月开始,杨沫陆续收到读者来信,《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诸多媒体也纷纷发表介绍和评论文章,基本都持赞扬态度。当时,周扬在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还有一部,就是《青春之歌》。紧接着,北京大学等六所学校相继致信杨沫,邀她到校演讲。小说出版六个月后,销量达到39万册。8月,评剧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表示要把《青春之歌》改为评剧。10月,杨沫成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一员,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与此同时,小说的英语、朝鲜语和俄语翻译都被提上日程。杨沫在病痛中艰苦创作的近四年时间终究没有白费,《青春之歌》令她真正成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
2.“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北戴河的风呼啸着,大海翻卷着怒涛,一个单薄的身影迎着风朝向海,从凶险的礁石上,纵身一跃,没入海中。这是电影《青春之歌》开场处的林道静。
在这组画面中,仍然身着白衣的林道静没有了那个插满乐器的行李卷,早早表露出革命者的刚强。要将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小说拍成电影,自然需要删减情节和人物,何以选择这样富于动感的开场,或许与电影拍摄时的时代背景与具体情况有关。
和小说出版一样,《青春之歌》的电影拍摄可谓一波三折,且情况更为复杂。早在小说出版之前的1955年6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也是杨沫的妹夫蒋君超便与杨沫约定,由他来改编电影剧本。但有人提出这部作品应该由北影厂来改编与拍摄。杨沫是北影厂编剧,《青春之歌》又是写北平的事,这个建议有其合理性。最终,电影《青春之歌》由北影厂拍摄,并由杨沫亲自编剧。
经过如此周折,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在围绕国庆主题创作的7部彩色故事影片中,北影厂占3部,名列首位的就是《青春之歌》。当时北京市领导指定廖沫沙、邓拓和杨述负责影片摄制,北影厂派出崔嵬和陈怀皑联合导演。1959年1月,杨沫完成了文学剧本第一稿;两位导演立刻介入,共同对剧本进行加工完善;而后廖沫沙等三人又提供了一些建议;最后,由夏衍对剧本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和再加工。与此同时,演员的物色和挑选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最终崔嵬力排众议,选择在武汉的青年演员谢芳出演林道静。
但即便重视到如此程度,仍有意外干扰。就在电影紧急筹备的1959年2月,有报刊发表了一篇基层工人的文章,指出《青春之歌》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等问题。这篇文章引发长久讨论,又出现一些其他批评意见。但肯定声音还是占明显优势。何其芳、马铁丁、巴人等名家,都纷纷撰文表示对杨沫的支持,其中茅盾的意见大概最有分量,可算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在《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茅盾主要谈了三点:首先,《青春之歌》真实反映了历史事实;其次,林道静有缺点,但是赤心为党,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的,有典型性;最后,《青春之歌》有缺点,但缺点不在于没有很好地写工农群众,作者着意写的是学生运动,不应苛求作者完成她自定任务之外的任务。
出于慎重,北影厂在1959年2月底会同《北京晚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尽管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肯定小说原作,摄制团队仍虚心接受了会上提出及此前讨论中的种种意见。除正常删减情节、合并人物之外,较之小说,电影的一个重要改编就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经受锻炼的内容,使其思想成长过程更加合理。正因为这样精益求精的谨慎态度,电影在公映前集体审看时便得到一致赞扬。陈毅审片后,也相当兴奋地表示,什么是国际标准?这就是国际标准。周恩来总理亲自调看此片,并邀请主创人员同到西花厅观影。多年后杨沫还记得,观影时周总理扭过头来亲切地对她说:“小超很喜欢你写的小说《青春之歌》……”整个看片过程中,周总理兴致很高,不断询问拍摄外景地以及演职员情况;中场休息时,他特意向主演谢芳表示祝贺;影片看完后,还对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在听说有人认为影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时,周总理表示反对:“我们都是这样走上革命的路的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大概代表了很多人。电影音乐的作曲者翟希贤在回忆创作经历时也谈及当时激动的心情:“今天,四十岁左右的人,在抗战前夜开始接触革命并投身在群众运动洪流中的人,谁能不为这段历史激动呢?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林道静只是比我们大几岁的同时代人;《青春之歌》中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都是非常熟悉和容易理解的。”青年观众同样深受鼓舞,当时还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张炯,就在座谈会上表示,当林道静“经历了斗争的磨炼和监狱的考验,在党的红旗前庄严地举起手来的时候,也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光明和激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青春之歌》一上映,就赢得广泛欢迎,美名甚至传到国外。
据说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电影后,纷纷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1961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还撰文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说:“《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就在这一年,谢芳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代表团乘坐的汽车无论开到哪里,都能遇到电影粉丝举着签名本,喊着“林道静”的名字,请求谢芳签名。
而对于小说《青春之歌》而言,电影不仅扩大了它的知名度,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电影中增加林道静在农村锻炼的情节,是杨沫个人意见还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如今已不可考。后来,杨沫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杨沫说:“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
3.时代在前进,但《青春之歌》不会被遗忘
在一幕幕老北京名胜的画面里,一个画外音平静地叙述着自己想要过平常生活而不得的悲剧。而后镜头陡转,一伙人吵吵嚷嚷地冲进一户大宅要债,一名少女怯怯地从房里探出头来打量。这是1999年版电视剧《青春之歌》的开头,林道静换下她标志性的一身白衣,穿上女学生的淡蓝上衣,平添几分家常气。这部由众多明星联手打造的电视剧与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电影相比,更强调从人性角度理解人物,表现符合他们性格逻辑和思想逻辑的人生选择。
电视剧本的执笔者之一、作家陈建功在谈及创作初衷时表示,作为当今的一位作家,即使冒险,也应当在改编中赋予自己的理解,30多年前,《青春之歌》是一部激励了一代人的小说,到了近来,应该承认人们在首肯其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情怀的同时,已经看到了原著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作为改编者,我们的基调是既要继承张扬其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情怀,又要把对过去那场革命的更深刻更新鲜的了解传递给观众,让观众从中看出社会思想前进的足迹,看出艺术创造者思想情感前进的足迹”。时代再一次激活了这部名著。
新世纪到来了,青春作歌,依旧传唱。2009年5月1日,歌剧版《青春之歌》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首演。2017年,浙江歌舞剧院又推出了民族歌剧版《青春之歌》。这两部歌剧都将戏剧事件集中在“林道静因为反抗包办婚姻投水自杀——遇到余永泽结为夫妻——遇到卢嘉川走上革命道路”这条主线上,以突出表现青春的选择,表达对青春的礼赞,让几十年之后的青年,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之下,依旧能够理解林道静当年的挣扎、斗争与进步。
所谓经典,正是这样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作品。因为其自身的价值,它将在不同时代都被挖掘出新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将成为它的一部分,同它一起,继续在时间中旅行:不断旅行,不断积累,不断焕发出光芒。我们有理由相信:时代继续前行,《青春之歌》不会被遗忘,青春将始终昂扬,歌声会日益嘹亮。
(作者:丛治辰,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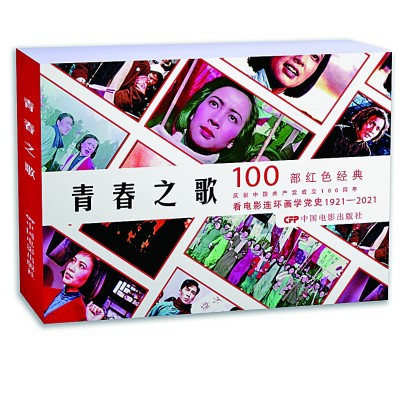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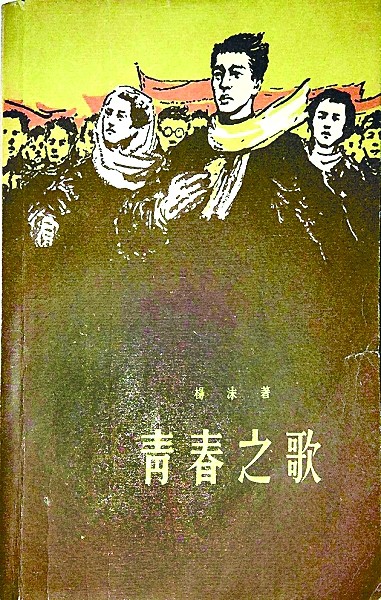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