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铲释天书】
王世民先生的《夏鼐传稿》,是考古学界期盼已久的一部学术史著作。这本传记,按照夏鼐先生的生平经历,用平实的语言,描述了这位杰出考古学家传奇的一生。作者的记述,或追迹《夏鼐日记》,或访求故友良师,或实录亲身经历,所言、所记、所忆,如晤故人、如数家珍……读来让人感到既真实又亲切。当年裴駰在评价太史公《史记》时曾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夏鼐传稿》,文直事核,正是这种佳作。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描绘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的一个“镜像”:看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也照见了我们考古人自己。比如,夏鼐为什么选择学习埃及学,科学的田野考古何以登陆中国,历代帝陵为何不提倡主动发掘,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何绝不涉足文物收藏……如此问题,林林总总,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答案。1985年6月19日,夏鼐先生去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胡乔木发表纪念文章,称夏鼐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细读《夏鼐传稿》,足证此言不谬!
夏鼐先生确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巅峰。“作为考古学家的夏鼐,是如何长成的”?《夏鼐传稿》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一、天资聪颖、一生勤勉
夏鼐先生自幼熟读诗书,过目不忘,显示出卓尔不群的天赋。从春草池畔到黄浦江边,从清华园到泰晤士河畔,夏鼐留下了一系列的求学“神迹”:就读光华附中,学业成绩曾高居年级第一;大学时作“魏晋南北朝史”课程论文,陈寅恪先生的批语是“所论甚是,是证读史细心,敬佩,敬佩!”;参加公费留学考试,梅贻琦校长称其成绩为“历年之冠”;素以严苛著称的伦敦大学埃及学系,对夏鼐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赞誉有加,称其研究成果“至少有六十年的命运”,意指直到20世纪之末,该文仍将具有重要价值(该文被誉为二十世纪埃及学的杰作,现已出中文版和阿拉伯文版)。难能可贵的是,天赋超群的夏鼐,毕生保持了勤勉刻苦、严谨自律的治学习惯和学者风范,无论负笈求学,还是考古荒野,乃至旅途颠沛、卧病治疗之时,他都手不释卷,不曾懈怠,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师出名门、比肩硕学
师出名门而又比肩硕学,这是“考古学家夏鼐”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夏鼐的中小学老师,即不乏后来成为大学知名教授者,如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华东师大副校长廖世承博士、上海书法界名流马公愚先生等;就读清华园,受业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史学大家;留学英伦,得惠勒教授田野考古之真传,还曾求教于埃及学权威皮特里教授;供职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颇受傅斯年、李济、梁思永之提携与赏识……与此同时,夏鼐相与交游的同辈学友,亦不乏后来成为鸿儒硕学者,如吴晗、季羡林、钱锺书、向达等。可以说,不同凡响的求学成长之路,使天纵其才的夏鼐注定会成为一位博采众长、贯通中西的学术大师!
难能可贵的是,夏鼐并不盲从于学校的安排与导师的规制。中学期间,他就曾订正吕思勉先生对“茹毛饮血”之误解;在燕京大学就读一年之后,他决计离开风景优美的燕京大学而投身心仪已久的清华大学,由社会学转攻历史学;留学伦敦大学,为了能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谢绝叶慈教授的挽留而转赴埃及学系;对于郭沫若、吴晗发掘明永乐帝长陵的提议,他也在完成定陵发掘任务之后,秉笔上书国务院禁绝此类发掘项目……由此可见,夏鼐其实是一位性格执着坚定的学者。
三、博览群书、贯通中西
夏鼐自认为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在燕京大学期间,夏鼐除了广泛阅读中文典籍,还给自己定下每天读英文书100页的任务。《夏鼐传稿》中列举了他的读书目录,使人不得不惊叹其读书之勤、涉猎之广、用功之深!夏鼐读书,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曰“读经典”,凡所能够见到的中外历史与考古学名著,他几乎是遍览无遗,包括不少外文原著。1940年他启程回国,随身携带的西文书即有380余册。其二曰“读当代”,关注国际学术最新动态,始终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在他那个时代,他大概是唯一与国际学术动态保持同步的中国大陆考古学者。
四、追求科学,求真务实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夏鼐的突出之处还在于他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他力主将自然科学手段引入到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碳十四测年法就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进入中国考古界的。再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和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的铝片,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但夏鼐力排众议,坚持科学原则并组织进行分析测试,确认前者为陨铁而非人工冶铁,后者则系晚近扰入之物,澄清了冶金史上的两大悬案。夏鼐本人还致力于考古学与科技史的研究。他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一文里,将这些考古发现归纳为七个方面,包括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对这些内容夏鼐本人均有涉猎,成就非凡。
五、“兼通世界学术”
1998年,王世民先生在夏鼐自存本《考古学论文集》扉页背面发现了一段文字,系夏鼐用毛笔抄录王国维先生的一段话,应该就是夏鼐用以自勉的学术座右铭:“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可见,夏鼐一直是以“兼通世界学术”为人生目标的,这是何等的气魄!正因为夏鼐在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他成为当时国内接受境外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人称“七国院士”。如日本著名学者樋口隆康所言:“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夏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田野考古奠基人。1945年,夏鼐在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于齐家文化,“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1950年,他带队实施新中国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车身已朽的情况下,用灌注石膏的方法成功剔出大型木车的遗存,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许。他是新中国成立时唯一接受过西方田野考古专业训练的学者,现下我们在田野考古中常常用到的一些技术方法和专业术语,从土质土色的辨认到熟土生土的区分,从墓葬找边到剔人骨架,从建筑柱洞的发现到车马坑的清理,从工地日记的编写到标本材料的整理……凡此种种,莫不由夏鼐率先垂范,并在高校教育和考古培训中得到推广。
考古学家的传记,其实就是考古人自己的历史。受人尊敬的夏鼐先生,还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学者。他的日记中,常常有这样的记录:与考古所青年同事去做田野发掘,大家一起睡土炕通铺,抵足而眠,大家笑称“像是排葬坑”;考古工地伙食很差,新来的厨师问老厨师,先生们有什么口好?后者明言,“你喂过猪没有?只要给他们吃饱就算了”;夏鼐与向达先生考古西垂,向达先生一时内急,不得不在废墟旁解决问题,由此而深深自责,称是“遗臭万年”;“文革”期间,一位考古人被下放劳动,夏鼐安慰他,“考古人去挖土,其实还是在干本行”……我们仿佛看到一位穿着淡蓝色布衫的长者,带着一身的书卷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让岁月无法冲淡的背影……掩卷之时,我想起一位考古界前辈的话,“夏鼐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作者:姜波,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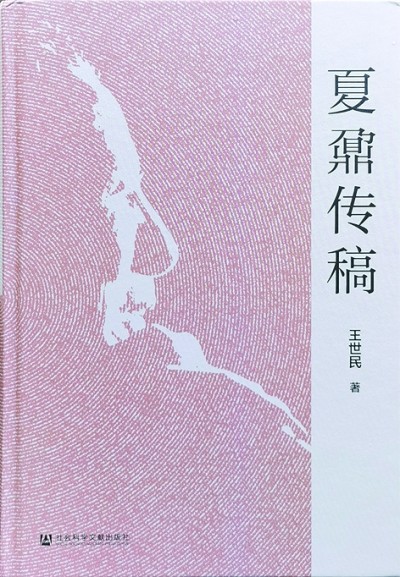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