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思想以道为中心,主要分为道论和德论两个部分。庄子的道论包括“逍遥”境界和“齐物”之法。“逍遥”境界是一种理想中的精神世界;“齐物”是进入逍遥境界的方法和途径。与道论紧密联系的是庄子的德论,德是道在现实层面的落实和体现。《庄子·德充符》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的德论以安命思想为中心,以“用心若镜”和“与物为春”为其两翼。庄子的其他思想观念,诸如庄子的天人观、生死观、政治观、处世观、养生观等,都是在庄子道论和德论在不同方面的投射。
在今天的讲座中,围绕庄子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我想谈谈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庄子的人生体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
庄子的人生体验:“白驹过隙”与“天地之美”
庄子眼里的人生是短促的、梦幻的、痛苦的。写人生短促的,如《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其三把这一句诗化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写人生如梦的,最有名的是《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又曰:“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我们以为不是在做梦,其实还是在梦中。写人生痛苦的,例如《齐物论》曰:“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连用了“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谓大哀乎”三个感叹句,对人生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千古而下,令人慨然。
虽然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短促,人生如梦,但并不能把庄子看成一个悲观厌世者。庄子有自己的理想人格,他的理想人格表现为神人至人真人。《逍遥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描绘了神人的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齐物论》描绘了至人的形象:“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大宗师》描绘了真人的形象:“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的说法,被后世的道教信徒视为神仙显身;不过从哲学的角度看,他们更可能是庄子思想中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体现者。
如果说,上述神人至人真人对于常人来说只是一种精神偶像,可望而不可即。为了让常人能够体会到“道”的境界,庄子又告诉我们他的另外一些体道之法。《齐物论》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吾丧我”是一种常人经过修炼就可能进入的精神境界。《人间世》曰:“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大宗师》曰:“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心斋”和“坐忘”乃是两种进入“吾丧我”境界的方法。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即虚而待物,顺物自然。在心斋和坐忘之前有一个“我”,这个“我”抵制外曲,自我意识强烈。通过心斋坐忘之法破解了我对自身主体性的执着,从而进入到吾丧我的境界,这是一个由有心到无心的过程。心斋当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自由,现代自由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宗旨,而心斋重在对生命主体意识的消解。它可以使人暂时离开矛盾的漩涡,进入到敞亮澄明的无我之境。
清胡文英《庄子独见》曰:“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表面看起来,庄子冷眼旁观着人间世,在心底则对人间世充满了大爱。日本学者福永光司通过自己的体验说:“《庄子》是一本慰藉心灵的书。……《庄子》是教会我在悲惨中微笑的书。……《庄子》是一本赋予我不屈不挠之心的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9年)
在《庄子》中,我们会读到他对天地万物的深情。《知北游》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又曰:“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在意识到人生短促、生命无常之后,庄子并没有走向宗教,庄子思想始终扎根人间世,庄子热爱自然,也热爱生命。
人与自然之关系:“天与人不相胜也”的对与错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命题,古人云“学不究天人,不足以为学”,岂虚言哉。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最重视天人关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然”一词相当于《老子》《庄子》中的天和地。按照老子的思想,人要效法天地,自然而然地生活。《齐物论》曰:“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庄子哲学的理论基石。庄子借真人发论,说明天人合一的重要性。庄子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也”的著名论断。《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自然是万物的父母,也是人类的父母。在庄子眼里,天与人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和谐共处的整体。
到了战国时代,庄子学派观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恶化。《祛箧》曰:“夫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软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在历史上,庄子学派反对使用机械,《天地》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佚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按照庄子学派的观点,人类一旦“好知”就会走向科学技术,有了科学技术就会扰乱自然的运行,就会破坏自然的秩序。一个人有了“机事”就会形成“机心”,有了“机心”的人会打破自己精神世界的平衡。
庄子学派对“好知”的恐惧,其中当然有错误的认识,不过其中也有值得后世借鉴的部分内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建设现代文明的今天,庄子的天人思想依然值得现代人加以借鉴。
人与社会之关系:“无用之用”的相对性
《荀子·解蔽》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从儒家的视角看,荀子的批评恰如其分,入木三分。相对于老庄思想,儒家思想始终以积极进取的面貌示人。《论语·泰伯》载曾子之语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一生克己复礼,以天下归仁为己任,成为后世士人效法的楷模。《孟子·滕文公下》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横渠语录》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回顾中国古代历史,历朝历代有理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们,无不以上述儒家思想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与儒家不同,道家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处世方式。《人间世》既表述了庄子所主张的处人与自处的人生态度,也揭示出庄子处世的哲学观点。庄子要求人们摒弃名利之心,保持心境的空明,被王夫之称赞为:“此篇为涉乱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术,君子深有取焉。”(王夫之《庄子解》)在庄子眼中,事君之难,是涉世的第一难题。在漫长的专制时代,一个士人想要建功立业就不能不走上仕途,就不能不面对统治者。庄子主张在身心之间以心为本,在多与一之间以一为本,在有心无心之间以无心为本。君臣相处之难,也表现为人道之患与阴阳之患。庄子主张忘身,所谓的“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也就是顺其自然。人臣与储君相处之时会面临国与身的两难境地:“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庄子提出了顺物无己的思想。在顺之的前提下引导对方,“达之,入于无疵”。庄子认为,人处世间,必须以顺应物情为要。庄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无用”之用正是“虚以待物”的体现。“无用”之用决定了庄子“无为”的人生态度,但也充满了辩证法,有用和无用是客观的,但也是相对的,而且在特定环境里还会出现转化。
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形态,但两者并非水火不容,更多的时候是以儒道互补的形式共存于世。《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儒道思想如同阴阳的对立统一体,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体系。《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处的独善其身与道家思想并不逆违。在处世哲学上,古人往往向儒家思想学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也常常把道家思想作为必要的补充。面对逆境和挫折之时,道家的逍遥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古人消解焦虑、战胜自我,从而走出人生的困境。这种补充关系,也可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
人与自己之关系:“用心若镜”和“与物为春”
庄子逍遥境界中的无己、无功、无名,齐物之法中的心斋、坐忘,都涉及人己之关系。庄子德论中的安命思想,以“用心若镜”“与物为春”为安命之法,更应该成为处理人己关系的准则。
“用心若镜”出现在《应帝王》中,《应帝王》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德充符》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又曰:“‘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镜子是被动的,它无法选择走向自己的物体。世界上的一切物体都可能显现在镜子中,大到风云变幻,山川河流,小到人物花草,鸟兽鱼虫。面对来者镜子只是客观的反映,面对去者镜子不会挽留。静止的水面也具有和镜子同样的功能。“用心若镜”也就是心如止水。“与物为春”出现在《德充符》中,《德充符》曰:“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庄子认为,生命的出生与死亡、四季的运行轮转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作为个体的人,无法改变它;个人的贫穷与富贵、社会声誉的上扬与下降,取决于很多因素,有时候并不是通过个体的努力就能够改变的。庄子把这些不能改变的东西统称为“命”。面对这样的“命”,庄子的主张是并不消极去承受,而要“使之和豫”“与物为春”,用春天般温暖的情怀去接纳和对待我们不能改变的“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子思想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用心若镜”是说我们的内心如何去应对外在世界的冲击,“与物为春”是说我们的内心如何去面对冰封的外在世界。“用心若镜”是由外入内,“与物为春”是由内向外。这一内一外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庄子的处世哲学。
对于庄子的道论思想,目前我们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了,读者也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于庄子的德论思想,学界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庄子“用心若镜”“与物为春”的德论思想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小结
简单而论,我认为,庄子对人生冷眼旁观但并不厌世,他对生命的体会思考前无古人,力透纸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庄子对人类发出了善意的提醒;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庄子思想与儒家思想形成了互补关系,可以让人们在处理人我关系时张弛有度;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上,庄子的德论思想甚为深刻。当然,在发掘庄子思想中历史闪光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警惕其中的那些消极成分,例如庄子过分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集体精神等,这是在当代认识庄子思想过程中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在今天可能还有一些人把历史上的老庄思想,看作消极思想的代名词,也有些人认为老庄思想只是属于两千多年前的精致古董,和现代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两种看法都值得商榷。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把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这一时段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古老的东方出现了《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典籍,它们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经典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它们都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后世的我们继续研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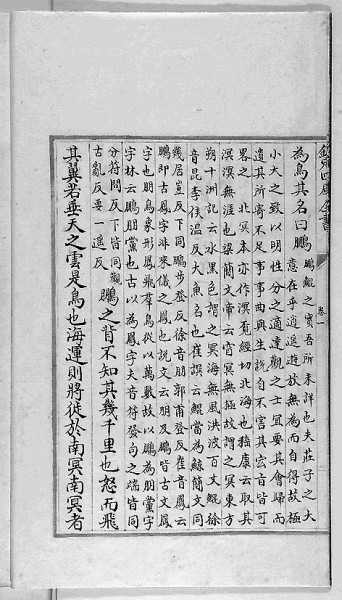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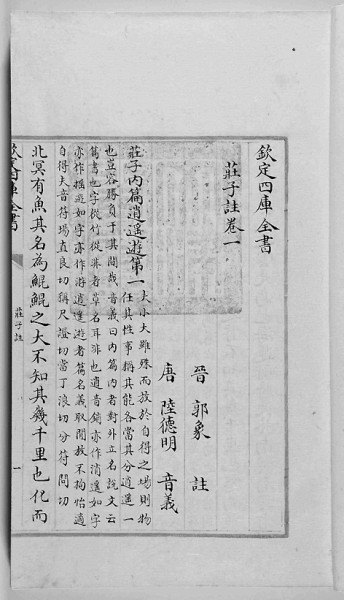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