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阿拉伯、粟特文献中称呼大唐都城长安为“胡姆丹”(Khumdan),这可能是这座享誉欧亚的帝国之都独特地位的一种表现。而且,长安实际上也是世界帝国大唐王朝的缩影和象征。现代研究者借助多元的历史典籍、考古资料、出土文献而融会贯通,试图复原长安的历史全貌,不断推动方兴未艾的“长安学”研究。然而,近年来另外一种聚焦于长安意象的“文学考古”异军突起,长安学由此或将挺进更为广阔和纵深的地带。
郭雪妮新著《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关注长安都市景观在日本古代“汉”“和”文献中的演变,跳脱了长安本身而突进到域外文本对于现实长安的书写,别开生面,应该说是长安文学考古的嚆矢。全书的核心议题,即对在唐朝灭亡以前和以后日本建设国家的不同阶段,日本文学文本中亦真亦幻的“真实长安”和“意象长安”进行了绝妙的对比,并将之落实到“东亚都城时代”长安都城真实空间在日本的复刻、变异和折射这一历史背景中深入理解。
具体而言,这部作品的前三章虽然瞄准了三种“汉”文献,但是其折射的历史内容却存在流变:《怀风藻》中长安的缺席,映射出建立律令制国家的日本难以将作为八世纪唐朝“国家权力和皇帝威严的王权之都”的长安作为歌颂对象;“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基本无涉于唐长安城,而仅以汉长安隐秘现身数次,暗含着日本文人面对强势的唐帝国时“脆弱民族国家的话语表达”;《本朝无题诗》则大量出现指涉长安的诗作,但这些无一实指,而是以“长安”来写现实中的平安京,并利用两座都城名称的重合,植入中国典故,将日本都城平安京描述为囊括唐帝国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巨大存在。
后四章多元化地引入几种“和”文献虚构文学作品,竭力寻觅长安意象的变迁以及客观历史投射其上的另一种真实。圆仁的旅行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包含着从开成五年(840)到会昌五年(845)他在长安生活的四年十个月的记录,尽管日记文本在后半段的唐武宗灭佛期间表现出与僧人整部日记大相径庭的情绪化描写及“不可靠”叙事,但对历史亲历者(圆仁)而言仍是力求秉笔直书并自信为真的文本,然而后来的《今昔物语集》等说话类虚构作品却逐渐放大、扭曲法难期间“圆仁”遭受迫害的情节,制造以“绞缬城”为重心的恐怖长安景象。院政时期“词书”与“绘画”交叉结合的《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兼具图像和文学史料,描述了遣唐使吉备真备在长安应对唐人难题考验的冒险传说,长安的海岸风光、唐人的滑稽描摹等不实内容映射了日本平安末期对长安的基本知识和想象。平安末至镰仓初的《弘法大师行状绘》以空海生平为题材,其入唐部分的描画将唐长安城中的青龙寺作为惠果传授密教于空海的象征而被日本真言宗神圣化,而与真实的青龙寺相去甚远。镰仓初年遣唐使物语的集大成之作《松浦宫物语》,既混合了仙界等非人间的浪漫唐土乌托邦,又以汉长安的用语细致描写唐都长安的宫殿、关隘、城市、郊外,其间的想象基础多来自白居易的诗文和《文选》,而非正统的地志文献。显然,花非花,雾非雾,“和”文献中的长安绝非唐长安的写真,而是文学想象、历史意识和现实感怀的杂糅造作。
其中的知识密度、探索深度、视野广度显而易见。关键是,唐都长安作为城市客观实在本身,已然不再是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已转变为日本人从奈良、平安时代至镰仓初期在诗歌和说话、绘卷、物语等文本中对于长安的“忽视”或者“想象”——其间,真实的长安城在十世纪初随着帝国覆灭而遭致毁坏和废弃。由此,这一研究仿若是在日本人的真实长安之旅以及长安梦境呓语之间,寻觅长安的影踪,这令人联想到诺兰的经典影片《盗梦空间》中“梦中梦”的多层穿越。
历史学者围绕着隋唐长安展开的多学科的研究,或可笼统称之为“长安学”(虽然未必所有学者都认同此概念)。如果以其涵盖的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以及艺术等多方面内容为“中心”领域,恐怕作为域外思想史、文学史的长安书写无论如何都只能算“边缘”领域。然而,诚如妹尾达彦所说,学术本身没有“中心”或“边缘”之分,很多学术突破恰好发生在学科交界的边缘,因为那里“本就不是边缘,而是被忽略的地方”(序二)。日本文人长安意象的文学考古实际上裹挟着以上以历史为主的诸多学科的成果,反过来对认知历史提供广阔的纵深空间。
作为历史学者,我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在这些层层考释的更深处,在围绕着长安意象的“文学考古”整个过程中作者不断强调的预设前提,即东亚所共同享有的华夷思想在都城建设和国家观念上的投射。如何理解这一见解?
十世纪唐帝国崩溃以及东亚社会全局性的连锁性质变作为一个分水岭,使得全书呈现出一种上半部是拥有长安旅行经历的遣唐使和求法僧笔端语涉长安或者绝口不提长安,下半部是无缘再前往中国的日本文人通过文学想象对于长安多种形式的异化和虚拟。在这种虚实相生、真假莫辨的强烈反差中,揭开层层包裹和修饰而袒露其本体,整个“文学考古”的过程辗转腾挪曲折繁复,却不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魅力,真实历史被悬置,“权力”在追寻中浮出水面——这个权力关乎日本律令制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其对唐朝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态度。
长安被书写或被遗忘是历史表象,它其实反映的是日本的文人在华夷思想和律令体制的多重影响下,“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模仿中国,却又在精神世界试图对抗的矛盾心理”(序二)。唐朝的华夷秩序之下,日本等周边政体都被纳入朝贡—册封体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世界格局,其典型是白江之后唐、新罗、日本抟成的国际结构,学者称之为“东亚世界”。在中国强盛时期,日本文人刻意不去书写长安即唐朝象征,也就意味着深层意识中不想流露出本国的屈尊地位,在唐帝国瓦解之后,日本文人或以辉煌长安的意象喻指平安京,或虚构唐都长安的恐怖梦魇,或建构日本宗教与唐朝源头的纽带等,则是日本民族意识高扬的时代之声。其中,平安京融唐朝京、都为一体的理念,实际上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文化共享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共享得以实现是基于存异而非求同(拙作《唐朝与东亚》)。长安作为文本的线索,首先反照出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平安时代(794—1185)及镰仓时代(1185—1333)初期的中国观,进而折射出来自中国的“中华思想”的强力辐射。
对于日本汉文学最早的作家群遣唐使而言,长安城以及平安京固然是作为物理可感知的第一空间,而同时遣唐使群体诗文制造的“长安意象”,又是隐喻的第二空间。第二空间本质上讲与第一空间越来越疏离乃至抵牾,甚至使得长安由陆地城市变成海岸城市,这就是我所说的“梦境呓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二空间的虚无荒诞,却是呓语者其来有自的亲身经历和切肤真实——譬如,圆仁将会昌年间的道听途说煞有介事写入行记,我们丝毫不怀疑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坚信这些记载,而后世在将他神圣化的过程中,以文学虚构进一步把他在法难中罹受屈辱、迫害、苦难之地长安夸大扭曲成如地狱一般的时候,正是日本“佛法东渐”思想和与优位意识炽盛的时期。再如,绘卷中的吉备真备战胜唐人的层层阻碍,凭借的不是真实的才华智慧,而是欺骗、盗听、偷棋等不光彩手段,这些狡黠的智慧在作者看来是平安末期贵族文人对唐弱者意识的结果,潜藏着“一种顽强的抵抗感”。
总之,日本国家的律令制国家建设、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换、东亚局势和本国内政的变动、日本民族意识的抬头,这些历史的真实无不经由作者在数量浩繁、种类多样的文本中批拣出来的“长安书写”(刻意不写也是一种书写,正如遗忘也是一种记忆)而映射显现。统领全书的序章或因此而题为《在日本发现长安》,似与书名《从长安到日本》桴鼓相应。然而,通览全书内蕴丰赡的知识与思想史呈现,我倒是更愿意凸显研究者在这种探索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而谓之《在日本寻觅长安》。至于其追寻的文本在生成之初是否即为长安而作,探寻所得结果是否为互文共生的文本丛的透彻解读,抑或在寻找过程是否全面关照日本文人的中国地理知识接受史,似乎已不是症结所在。在中国与域外往复交流的宏大背景中,苦苦的摸索和反复的寻觅,过程本身足以动人,加之其间历史景观不停变换,沿途满是可堪吟味之处,读者自可逐一赏析。诸君何不立即与作者一道,一日看尽长安花?
(作者:冯立君,系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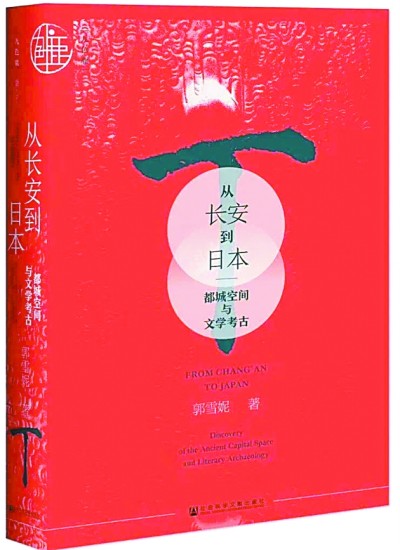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