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启功先生(1912—2005)出生前七个多月的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所以我们称启功先生是“中华书局的‘同龄人’”。又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因缘际会,启功先生常说:“中华书局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师从启功先生,在阅读他这本大书的过程中感慨颇多。
启功家世的启示
启功的九世祖为爱新觉罗·胤祯,即清雍正皇帝,八世祖和亲王弘昼系乾隆(弘历)胞弟,但是到他的曾祖父溥良(礼部尚书,广东、江苏学政)和祖父毓隆(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则已不靠世袭取得爵位,而是凭真才实学获取功名;他父亲恒同更因华年病逝而家境困窘。所以启功先生常强调:我出生于民国元年,既非清朝遗老,亦非遗少。少年时,他因家境困难无法读完中学。在留给我的一份自撰简历手稿上特意写明“曾读小学,中学未毕业”。启功先生的“外家”系蒙古族阿鲁特氏后裔,如外高祖赛尚阿曾任首席军机大臣,外曾祖崇纲为驻藏帮办大臣(其弟崇绮是清朝唯一一位蒙古族状元),母亲克连珍也是蒙古族。所以,启先生常讲自己生长于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他虽是北方满族人、清朝皇室后裔,却绝无丝毫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对祖国大好河山、西域边疆,对历史文化名城,对得中外文化交流风气之先的中华书局先后所在地上海、北京有着同样亲切的感情。他认为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是由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积淀而成。这就启示我们要从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及融会贯通的视角来认识启功先生,来理解先生和中华书局的因缘。启功先生自1934年起历任辅仁大学附中、辅仁大学美术和国文教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执教70年。作为海内外知名的诗书画大师、文物鉴定大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中华书局杰出的作者和师友,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个家”的缘由
作为中华书局的同龄人,启功先生常说这样一句话:“中华书局是我的第二个家”。启先生青年时代阅读了大量古籍及相关的整理本与学术研究著作,当然对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情有独钟;1962年,他曾应邀为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题写了书名;但是,据我了解,他真正与书局的直接交往,应该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启先生的书法造诣已为学界公认,书局遂邀约先生撰写《中国书法》一书,并预付了200元稿酬(这在当时相当于先生两个月的薪资);可惜因为其时不可预料的原因而未能撰写出版,成为一大憾事。据他1966年8月28日的日记记载:“下午到邮局寄还中华书局前预付《中国书法》一稿稿费二百元。”当时,启功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古代字体论稿》已在文物出版社印行;第二部书稿《诗文声律论稿》正在撰写之中,先生希望书局能出版此书,已经请他的恩师陈垣老校长题写了书名。
1971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驻校军宣队员通知正在校园里劳动的启功先生:“你到系里去一下,要借调你到24师去。”先生闻言大吃一惊,十分疑惑:“为何要我去部队呀?”8月30日,先生到系里开借调介绍信,才得知中央下达文件,要在各高校及研究机构抽调一些文史专家集中到中华书局去做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古籍整理工作。原来是“二十四史”,不是“24师”。先生的心方由忐忑不安转为又惊又喜,为自己能换一个环境去做自己喜欢之事而高兴。先生当天就急忙赶到位于王府井大街36号的书局办公楼报到了。当时,为了减少专家来回奔波之劳,就安排一些人住在办公楼的临时宿舍里,这样也可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启功先生很快就住进了大楼,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当时,启功先生的夫人因病住院,他经常得抽时间去探视。除了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和业务会议外,他尽力抓紧时间点校《清史稿》。在此,选录几条他当年9月其中七天的日记:
9.6:上午《清史稿》组开会,分工,我先点志(舆服、礼、选举)三种。
9.13:上午上班,清史组商讨标点事,下午点书3200字。傍晚到医院,《选举志一》点毕,自今日点书始入正轨。
9.18:今日点志五毕三半,共计已点四卷半,自9号起至今共9个单元共点37440字,计每半日点4160字。
9.25:今日共点十五页,共11700字。
9.27:上下午点书,今日点9300字。
9.29:上下午点书。今日点约一万字,到协和。
9.30:上午点书约五千字,下午扫除,到北京医院看咳嗽,到协和。
我粗略计算,在这半个月里,启功先生已经点校了八万余字,工作效率很高。据当时一道参加点校工作的书局几位编辑回忆,启先生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既认真负责,又风趣幽默、乐观大度,仿佛给大家带来了和煦的春风。启功先生也常说:从1971年夏到1977年秋,在中华书局参加《清史稿》点校工作的六年,是他比较稳定、舒心、顺利的时期,书局真正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先生享受到能为国家古籍整理事业贡献力量的快乐,也感受到了学者、同事之间互相关心和爱护的温暖。有一次,书局找出了一幅1973年参加点校的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四楼平台上的合影,让我拿给启功先生看,先生不仅准确地辨认出每一个人,而且马上用毛笔将姓名注写在每个人影像旁,还写明了拍摄的时间,使这幅照片成为书局也是中国古籍整理史上的珍贵资料。
1977年秋,启功先生的手写本《诗文声律论稿》几经波折,终于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此书后经先生修订,至今在书局已有几个版本问世,总印数超过了20万册。也是从那时开始,启功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题写书名趋于“高峰”。只要书局编辑或作者提出请启功先生题签,他不仅会欣然允诺,而且会主动替美编考虑封面设计,询问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横排抑或竖排。有时还各写几幅以备选用,甚至自己跑邮局寄给编辑。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他为中华书局的题签总数近200幅。2018年初,中华书局出版了《启功先生题签集》,刊发了启功先生为书局的题签影印真迹170余件。书后附录了书局现在的掌门人徐俊执行董事题为《中华版图书他题签最多》的文章,叙述了启先生为书局出版物题签的一些生动故事和他的切身感受;书后还附录了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大弟子来新夏教授的文章《启功老师题书签》。启功先生的题签以及来、徐二位的文章,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捧读温习的佳作和佳话。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故事:八九十年代,因为启功先生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越来越高,有一回,书局领导觉得不付先生题签费说不过去,就让我去问先生给多少合适。不料先生听我一问,很不高兴地反问我:“书局是我的第二个家,难道给家里人写字也要钱吗?”为书局出版物题签分文不取,是启先生坚定一贯的态度。2000年,书局出版了启功先生主持并指导北师大几位教师共同校注的《红楼梦》,受到读者好评;先生也是坚持将稿酬支付给那几位老师,自己不取分文。
启功先生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做编辑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我在新疆任教十年后考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启功先生是我们九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也是我和其他两位撰写唐宋诗文论文的指导教师。其实,先生并不赞成将唐代文学作品截然分为初、盛、中、晚段的主观而生硬的做法,告诫我们要全面、贯通地研究古代文学。因为我有在新疆生活、工作的经历,读研期间关注唐人边塞诗歌作品,1979、1980年暑期还专门到南、北疆进行实地考察,写了几篇考辨西域地名的短文。1980年秋天返校后,习作呈请启功先生审阅,先生认为有发表的价值,便提笔给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推荐了古汉语专家俞敏教授的《金文略说》和我的两篇西域地名考辨文章,特别强调“柴文尤望赐以指正”。先生对我说:“傅先生和张忱石、许逸民在书局办了个学术集刊《学林漫录》,刚出版了初集,在学界颇有人气,我答应为他们提供一些随笔、题跋类短文,觉得你的文章也可以在该刊发表。”第二年初,拙文《“瀚海”辨》便刊登在《学林漫录》第二集中;不仅这一集的书名便由启先生题写,而且第一篇文章就是他撰写的纪念恩师陈垣先生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春末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前,启先生又给傅先生写了一封信云:“师大柴剑虹同志毕业论文,关于岑参者,敬求我公为校外审查,赐予评定,并参与答辩,其文公已大致看过,过目当不多费时间也。”当时还有其他几位同学论文答辩的校外委员,也是启功先生写信邀请的,所以傅先生来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想法。其实,当时启功先生已经有推荐我进中华书局工作的想法,只是因为我是从新疆的教师岗位上带薪来读研的,还不清楚我毕业后的动向,所以没有跟我明说。研究生毕业了,师大规定我们几位从外地考来的研究生不能留校工作,我也觉得应该回新疆继续任教,但先生不赞成;后来,我有了留京指标,先生即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工作,体现了对我的关爱和对“第二个家”的衷情。
1981年秋,我进中华书局古代文学编辑室工作。是冬某日,先生打电话来讲他要带一些研究生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要我也参加。我知道,启功先生在他30多岁时就担任过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对院藏文物可谓烂熟于心。他认为做文史研究一定要有实地考察文物的经历与心得,做编辑亦如此,而我读研时并无此机会,因此特地给我一个补课的机会。那次跟着先生看故宫文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同学拍摄了我在考察间隙时向先生求教的一张照片,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在书局文学编辑室担任责编的第一本古籍整理著作是《罗隐集》,先生知道后,马上题写了书签。后来,我担任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的责编,启功先生不仅也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又详细诉说了50年代中期和王先生等编撰《敦煌变文集》的往事,鼓励我通过编书了解敦煌与敦煌写本,指出中华书局的重要特色是培养“学者型编辑”,要注意学术积累,要在学界有“发言权”,对我日后参与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是莫大的启示和教诲。先生在1985年9月10日第一届教师节时有一幅题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体会,这种发自内心期盼学生成材、学术进步和书业兴旺的“辛勤快乐”,伴随了先生70年教师生涯,也是一位高尚教育家的心灵独白。从80年代开始,启功先生出于对中华书局的挚爱,几乎把他重要的著述都交由书局编辑出版。如他最为看重的《启功丛稿》论文、题跋、诗词、艺论四卷,他的“捅马蜂窝”之作《汉语现象论丛》以及他和金克木、张中行先生合著的《说八股》等,还有他曾参与点校的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等,都为提升书局品牌效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对书局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的支持,启功先生也十分重视普及类知识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书局80年代初创办的《文史知识》杂志在文化、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启功先生在刊物创办五周年时题词勉励办刊编辑:“五年有如一日,宏扬文史知识。诸公再展新猷,学人受惠无极。”该刊百期纪念时,我正担任《文史知识》编辑室主任,先生又欣然题写了一首五言贺诗:“民族凝聚力,首在知文史。理工还要办,自亦识厥始。百册今初盈,千里此一跬。题辞祝宏猷,不自愧其俚。”表达了他对书局刊物提高民众文史修养的高度肯定。
进入21世纪,启功先生因年迈体弱,已不便用毛笔书写。即便如此,他还坚持用硬笔为书局出版物题签。其时我在汉学编辑室工作,策划编辑出版“世界汉学论丛”译著,先生特地将他多年前从东京旧书肆上购得的线装《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一函交给我,说此书对研究日藏敦煌文书很重要,但无中文译本,希望我找人翻译后出版。我遵嘱请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李德范研究馆员翻译完成,此书出版时先生还专门用硬笔题写了书名。2002年春,书局举办纪念创办90周年活动,先生不仅专门为纪念册题署,还不顾天气寒冷,再一次到位于丰台区太平桥西里的书局办公楼看望老朋友。先生指导的博士朱玉麒和北大荣新江教授合作译注了日本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在书局出版前先生也用硬笔题签。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费十年之功编著了《戴名世年谱》,启先生不仅两次与他面谈自己对戴氏《南山集》的认识,也为之题写书名。
行百里者半九十
启功先生晚年时,曾多次临写颜鲁公所书“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将它作为警示自己的治学指南。他对自己著述的不断修订精益求精,对读者意见的重视,对书局编辑工作中疏忽的提示,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书局准备将北师大出版社印行的《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合编为《启功丛稿·诗词卷》时,启先生特意寄来原《韵语》的校字本和《赘语》的清样,写信告诉我如何编排,如何插补,告知总序的写作,商量扉页的安排,使担任责编的我和刘石编审心中有数。2004年春,《启功丛稿·艺论卷》校样排出后,先生不顾因眼睛黄斑病变造成的视力障碍,仍坚持亲自核看校样。又如有一位周姓读者写信给书局指出启功先生的手写本《诗文声律论稿》中似有讹误,我将信转给先生后,他非常认真地进行核查,很快便给我写信就读者指出的误字予以确认,一一予以改正,并要我回信转告这位读者,表示:“周君校出,深可感谢!”《说八股》一书印行后,先生在校阅中发现有一页文章里的一段话居然完全重复了,而责任编辑并没有发觉,成为“一大笑话”,要我一定叮咛那位年轻的责编重排时将此页“改正为祷”!这是先生对编辑工作中粗心大意的批评,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已印行多年,学界反响也很好,但是先生自己仍不满足,一直在做修改补正的思考。在他年届90之时,遂对该书手写本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当时负责此书修订的责编是语言编辑室的陈抗主任,也是一位非常专业而细心的编审,在编辑之前的认真通读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启先生非常重视,十分高兴,连着给陈抗写了七封信,体现了诚恳、谦逊的精神,也高度称赞了陈抗及其他书局责编的工作作风。有一封信的开头写道:“今晨承示拙稿蒙仔细校勘所见诸疵累,既深感荷,又见编辑工作之细入毫发的注意力。不但鄙人衷心佩服,又见无数作者未必俱能亲自体会,而读者草草过眼,又无人能见到、觉到乃至意识到尚有无名英雄在背后曾付出极大精力;而作者争稿酬、出版社扣效益,不知责编获得一句由衷的良心话否?”我相信,先生在话中对编辑工作的肯定,不仅仅是对陈抗个人的赞扬,也会使书局其他编辑“于我心有戚戚焉”!如前所述,先生晚年因视力衰减已不便用毛笔书写,但他为了便于手写本《诗文声律论稿》的修订,硬是用硬笔在若干绵纸上书写了修补内容,并一一注明补放在何处。当他把这一叠耗费了极大心血的绵纸交给我时,我真是满含热泪,感动不已。先生早年曾发表过论述《千字文》的论文,晚年时听说发现了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中有多件《千字文》唐写本后,就让我提供其中最完整的影印本,说要根据这些新材料写新的考论文章。可惜先生当时身体已衰弱到无法拿起纸笔,这个愿望终未实现。
启功先生在他85周岁时曾就教师的职责写过一幅字:“先圣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今吾职业已为师矣,将如何以免其患?惟有心无所欺行无所愧,不强不知以为知,庶几有免患之望。”这是一位执教70多年教育家的真实心声。
启功著作绵延不绝
2004年夏日,我几次到师大小红楼启功先生家里探望,告诉老师我已年届花甲,即将从书局如期退休。启先生非常惊讶,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为什么要退休啊?”“你还要编书吗?”我当然知道老师不希望我从他看重的书局编辑岗位上退下来。我则向先生保证:即使退休了,我还愿意为编辑事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别是应该为像他这样的前辈学者专家出书贡献力量。2004年9月,我应邀到台北市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担任一个学期的专任教授,讲授敦煌文化与敦煌学,其间还和启功先生通过几次电话,知道他急切地盼我回京见面。2005年1月13日,我回京后到先生寓所探望,他的身体已十分衰弱,不久即住院治疗。一次我去医院探视时,他在病床上忽然跟我说:“咱们的出版印刷工艺要赶上日本的二玄社,真想跳起来大干一场!”我知道,他仍关注着出版事业,尤其对他特别关注的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荣宝斋寄予厚望。
启功先生仙逝后,我协助一些年轻编辑先后在书局出版了《启功给你讲书法》《启功给你讲红楼》《启功讲唐代诗文》《启功韵语精选》(线装本)和《启功日记》等先生的著作;也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启功谈艺录》,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启功说唐诗》;参与北师大出版社编辑《启功全集》。2012年,为纪念启功先生100周年诞辰,书局不仅重印了先生的若干著作,还特地推出一套《启功三绝》的宣纸影印本,我也特地请先生家属为此书提供了先生的书画作品影印件,提供了我保存的先生手稿复印件。启功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著述有学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特点,即积淀丰厚,亦庄亦谐,平实易懂,雅俗共赏。
据我粗略统计,截至今年7月,书局累计出版的启功先生著作已经超过50万册,其中《启功给你讲书法》的普及本和典藏本,特别受到广大读者青睐,多达近30个印次,总印数累计也达到了30多万册。我想,这是中华书局对自己的一位“家人”,也是亲密师友最好的纪念。
传承文化的主体“人”和载体“书”
2006年,在启功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香港两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写的《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一书。在书中,我特别提出能得到像启功先生这样好老师的教导,是一生的幸运。通过这几十年跟随启功先生,我对“好老师”的理解和感受不外乎几个方面:第一,是他自己有真学问;第二,他有把自己学问教给学生的好方法;第三,他不仅教给学生做好学问,而且也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这样的好老师,当然也是出版社最欢迎的作者。我是想把我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做人态度告诉大家。其实,这也是启功先生从他的几位老师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等先生,特别是恩师陈垣老校长那里学到并传承给我们的。2012年,在纪念中华书局和启功先生百周年之际,我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高山仰止——论启功》一书,想进一步将自己多年来“阅读启功先生这本大书”的点滴心得告诉年轻的朋友。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当中的师承关系,私塾也好,蒙学也好,有它的精华。我们过去总是在讲,中国的封建教育如何腐败,如何落后,如何不好,一棍子打死。就像恩格斯讲的,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块倒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洗澡水”,有脏东西,但是它的核心,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精彩的东西,如果能取其精华,并不断汲取现当代教育的营养,就可以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
2012年3月22日,在中华书局创办百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致信中华书局,指出:中华书局恪守传承文明职责,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和学术新著,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体会,守正出新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宗旨。对我们出版社来讲,守正,是遵循出版方针,遵守学术规范;出新,是要追求文化创新,推进出版事业。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是人,教师与出版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提高国民人文素养、道德修养的重要保障,也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而图书则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1924年,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近百年来,中华书局与启功先生之间的因缘故事,生动地印证和实践了这位书局创办人的殷切期盼。
(作者:柴剑虹,系中华书局编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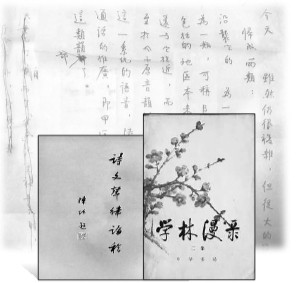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