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之后,诗人的身份意识亦趋浓厚,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自编诗文集,特别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此风尤盛。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考察了45种可以推断编辑经过的唐人别集,其中,诗人生前直接参与编撰的有19种;这19种别集皆出现在大历之后,中唐7例,晚唐有12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粹的诗集和诗歌比量更大的别集出现的数量也更多。(内山精也著,张淘译:《媒体变革前后的诗人和诗集——从初唐到北宋末》,《长江学术》2016年第2期)中唐之后,还有不少诗人因仕途蹇塞,转而专攻诗艺,甚至以此为平生大业。例如,杜荀鹤出身寒微,中年始中进士,亦久未授官,其《秋日怀九华旧居》称:“吾道在五字,吾身宁陆沈。”因此,晚唐孟棨《本事诗》记载他们的事迹时,往往不冠以官衔,而径称“诗人”,如称“诗人许浑”“诗人刘希夷”“诗人张祜”等。这表明“诗人”作为一种身份类型逐渐得以确立。
“诗人”作为一种新的身份类型确立之后,一方面激发了人们对诗歌创作的热情,很多读书人因诗得官,因诗扬名,“诗圣”“诗仙”“诗佛”“诗家天子”等称号不胫而走,“诗人”仿佛风光无限。但另一方面,很多诗人的现实境遇与理想中的“诗人”又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无奈感。在传统“诗教”中,“诗人”的“成功典范”无疑是《诗经》的作者,因为他们以诗“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倡“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代表着风雅精神之极则。然而这种“成功典范”,后世诗人往往很难企及。
白居易曾极力高扬诗歌的价值:“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与元九书》)可当他审视自我创作时却说:“予不佞,喜文嗜诗,自幼及老,著诗数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诗流。”(《序洛诗》)“落”字有“沦落”之意,可见白居易虽嗜好诗文,著诗甚富,却又不甘于“诗人”这个称号。杜甫《宗武生日》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赠蜀僧闾丘师兄》又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这既是杜甫对家世的自矜,亦是他对“诗神”的最高礼赞。但仔细考察,这两首诗都是杜甫辗转、流寓蜀地时所作,“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理想幻灭殆尽,唯以诗歌作为最后的精神寄托。明乎此,我们便不难体会陆游《读杜诗》中的嗟叹:“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而陆游之所以有这样“同情的了解”,实因他亦有同样的体验。乾道八年(1172)冬,陆游从抗金前线迁调成都,途经剑门关,细雨蒙蒙中,骑着蹇驴低吟:“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抒写的是壮志难酬的无奈与自嘲。陆游还说:“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初冬杂咏》其五)又说:“本慕修真谢俗尘,中年蹭蹬作诗人。”(《老学庵北窗杂书》其一)济世不能,修道未成,蹉跎蹭蹬之后,唯有作诗人而已。白居易、杜甫、陆游的言论表明,无论是最初的志向或者最终的谛视,“诗人”都不是他们的第一身份选择;似乎只有在功名理想破灭之后,才有可能认同这一身份。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如杨万里“诗家杂压君知么,压尽三公况九卿”(《跋汪省幹诗卷》其二)的自信言说,但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声音并不洪亮,更为主流的是“百无聊赖以诗鸣”的悲情表达。
古代诗人审视自我身份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普遍意识到“诗人”具有“薄命”“例穷”的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写诗难以支撑起诗人的生计。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诗人,诗人利用写作而谋生的现象并不普遍,国家与社会也没有赋予或规范诗人以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将“诗人”的身份置换为“官员”的身份时,才有可能获取维持生存的利禄。然而在古人眼中,“做官”与“写诗”往往难以两全,“官运”与“诗运”常相背离。《宋史·欧阳修传》云:“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欧公看来,“吏事”与“文章”的作用全然不同,前者可济天下,后者只能独善其身。宋人杜范《康秋惠诗和其韵二首(其一)》云:“自怜民事冥烦日,却是诗人得句时。”(《清献集》卷四)这种观念似乎可通过史实得以印证。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像唐代的孙逖,当其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之时,创作水平反而走下坡路;而像张九龄、苏轼等诗人的创作高峰,正是他们失意外放之时。因此,清人余云焕《味蔬斋诗话》卷三论赵翼说:“瓯北‘既要作好官,又要作好诗;势必难两遂,去官攻文辞’。又曰:‘诗有一卷传,足抵公卿贵。’余谓官职、诗名两俱入手,能有几人?显晦听命于天,著作操之自我。”“官运”与“诗运”的背离,意味着诗歌不仅难以谋得利禄,甚至还不利于助成事功。
个人自我身份的选择和认同,从根本上说,还受到了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影响。古人更认同的是他们借以“立德”“立功”的身份——阶衔、封号和职业,而非“文人”“诗人”“辞人”等身份。曹植《与杨德祖书》云:“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亦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晁补之《海陵集序》甚至说:“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至于诗,又文学之余事。”这种文化心理,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死后墓石上镌刻的头衔,因为这一头衔具有“盖棺定论”的意味,故古人待之慎之又慎。我们看到,古人墓石上镌刻的头衔一般是他的官职、科第或封号,而极少题为“诗人”“文人”“词人”等称号,尽管前者的声名远不如后者响亮。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特例——元好问和吴梅村,他们的三尺碑石分别书以“诗人元遗山之墓”和“诗人吴梅村之墓”。不过,这是他们出仕新朝而误尽平生的痛悔,不是一种常态之下的书写,背后透显的反而是无尽的悲凉,闻之者无不唏嘘嗟叹。
总之,中国古代诗人在审视自我作为“诗人”的身份时,大多流露出一种自嘲、无奈、焦虑的心态,“诗人”并非他们的第一身份认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诗歌自身,而在于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因此,想要摆脱这种困境,消解焦虑,则必须努力祛除世俗观念的影响,回归诗歌和诗人的本质。
首先,规避世俗的眼光,拒绝媚俗,执着于自我理想的追求。例如,中唐苦吟诗人大多运命蹇塞,却甘于贫穷和寂寞,躲在阴冷的禅房、廨署,雕琢着精巧的诗句,视诗歌为生命的归宿,甚至出现了像刘得仁那样“为爱诗名吟至死”(释栖白《哭刘得仁》)的殉道者。这种与现实的对抗方式,多少具有几分悲壮的色彩。
其次,从理论上重新探讨“诗人”的含义。特别是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性灵诗学推动之下,不少诗论家提出了他们理想中的“诗人”形象。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引王西庄(王鸣盛)语说:“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真诗人”取决于作者胸境是否超脱,气质是否温雅;而作诗、吟诗只是一种外饰,并非判定“诗人”的必要条件。“真诗人”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的“诗人”观念,它既非指典范的诗人——《诗经》的作者,亦非泛指一切写作诗歌之人,而指向的是一种生命境界或生存状态。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非常接近。因此,袁枚称赏此言“深有得于诗之先者”。
中唐以来人们总结的诗人“薄命”“例穷”等特征,其实是仅基于社会学层面的认识。相对而言,明清诗论家对“诗人”的探讨,因更注重于诗人的性灵、天分、人格等方面,从而更能捕捉到“诗人”的某些本质特征。黎遂球《顾不盈和拟古乐府诗序》说:“今天下多言诗之人,然而无多诗人。夫所谓诗人者,而必深居泉石,钓弋简出,置世故于不闻而后为诗。”(《莲须阁集》卷十八)黄宗羲《景州诗集序》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不散。”(《南雷文案》卷一)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则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近人陈楚南题背面美人图云:‘美人背倚玉阑干,惆怅花容一见难。几度唤他他不转,痴心欲掉画图看。’妙在皆孩子语也。”所谓“置世故于不闻”“天地之清气”“不失其赤子之心”,强调的是诗人任运自然、绝尘息虑、天真无滓的品格,这显然不同于传统“诗教”所设定的“典范诗人”。
(作者:李舜臣,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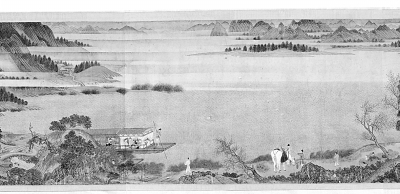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