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学人小传
马大正,1938年9月生于上海,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64年任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历任副主任、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始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唐代、清代边疆史研究。当前主要从事中国边疆治理、中国边疆研究史以及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构筑领域研究。1978年以来,独著、合著、主编、合编学术著作、论集、资料集7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策划、主编丛书及学术专栏20项,在国内外学术演讲300余次,独撰或合撰调研报告200余篇,主持或承担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部级研究项目30余项,培养博士生6人。
人的一生,春华秋实,二十青葱,四十不惑、六十从容、八十如典。岁月把马大正先生带到八秩之年,回望数度春秋,他六十年治学研史,勤奋执着,孜孜以求,以赤子之心、学人担当谱写人生华章。
民族史的探索
大正先生1938年9月出生在上海,1956年至1964年,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完成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不承想,大好时光竟被十年“文革”耽误了。直至1975年,在著名学者翁独健先生的指导下,他才参与了《准噶尔史略》一书的写作工作,并走上了民族史探索的道路。
准噶尔原是我国清代卫拉特蒙古族的一部,明末清初,准噶尔崛起于西北,统辖卫拉特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一带。《准噶尔史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肯定了准噶尔的历史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上,准噶尔部跃马挥戈,驰骋疆场,外御强敌,内勤牧耕,为开拓和保卫我国西北边疆作出贡献。
《准噶尔史略》是研究卫拉特蒙古部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在这部书的撰写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给大正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至今不忘翁独健先生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专著,不要成为应时之作。”
带着前辈的嘱托,大正先生走上了这条艰辛的学术之路,而且一走就是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他参加对新疆地区蒙古族的考察,多次深入土尔扈特部落探访,后来将一幕幕生动感人的场面记载下来,写成《天山问穹庐》。“我读着这本透着满纸烟云与苍凉的书籍,合书掩卷常思以往的历史,慨叹着曾经失去过的那一片片辽阔富饶的土地,还有蒙古民族那富有英雄传奇般色彩的历史故事,我满腹怅惘,一脸清泪。”一位读者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1982年始,大正先生与清史专家马汝珩先生合作,完成了多篇论文,如《顾实汗生平事略》《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试论渥巴锡》《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等。对土尔扈特部的这些研究极具功力,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大正先生与马汝珩先生合作完成的《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至今为学界乐道。这部书历经十载,四易其稿。在土尔扈特蒙古部的部落源流与王公系谱、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土尔扈特蒙古与俄国的关系、土尔扈特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显示了独特的学术眼光与见解。书中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东归的细节描写尤其让人动容——
伏尔加河1月初的气候,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保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他们冲破俄国的雅依克防线,渡过雅依克河,冒着隆冬的严寒,迅速进入哈萨克大草原,向恩巴河挺进。历时八月有余、行程近万里的东返征程,终于以土尔扈特人的胜利返归祖国而结束。
隋唐民族关系史是大正先生民族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1984年,他参加了翁独健先生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有关隋唐民族关系史的撰写。从《准噶尔史略》到《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通过对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民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在对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中,大正先生通过深入考察,廓清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与边疆的一些重大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隋朝统治时间虽短,但结束了近400年割据分裂、军阀混战的局面,由割据重新走向统一。唐朝推行“以武拨乱”的方针,开疆拓土,抗击突厥,联合回纥,广开北疆,统一西陲,经营东北,对吐蕃与南诏和战并举。盛唐时期的疆域,超过了西汉鼎盛时期的版图,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封建帝国。
大正先生认为,隋唐时期的边疆政策接受了数百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唐高祖对前代的教训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要“追革前弊”,制定更加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边疆政策,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就申和睦,静乱息民”,“怀柔远人,义在羁縻”。这是一个卓有见识的战略方针,为唐代确立比较开明的边疆政策打下了基础,到唐太宗时期这一方针有所发展,如“怀之以文德”就成为唐太宗治理边疆的基本政策。
大量史料的掌握,不仅让大正先生的民族史研究扎实可信,也为他日后研究道路的拓宽打下牢固的基础。他不仅在浩瀚的史料里爬梳整理,而且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奔走前行,考证史料记载,收集鲜活资料,让自己的学术底气更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行走边疆,研究边疆,足迹所至竟达70多万公里。
边疆学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研究准噶尔历史开始,大正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边疆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此后几十年间,他的数十部著述都是围绕边疆展开的。“从古代到当代多个层面追溯边疆历史、从宏观和微观多个角度解析边疆历史,致力于从边疆历史演进中探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规律,从纷繁复杂的边疆历史嬗变中探寻边疆治理的症结和路径。”他的同事李国强研究员如是评价。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日子里,大正先生一如既往地从阅读文献典籍做起,以更多地占有史料。同时,他注重边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边疆历史研究的新思维、新方法、新格局。1994年,他担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擘画统筹,身先士卒,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冷寂的局面,大正先生提出开展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构想,并提出一系列有利于研究深化且行之有效的举措。20世纪90年代,他主持并参与了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研。在他和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优良传统与百年积累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实现了新的飞跃。
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更加清晰。大正先生通过分析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自秦汉至清朝逐步完善,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治边政策,经隋、唐、元、明的充实,到清朝已经比较完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清朝治边政策可谓集封建王朝治边政策之大成,是中国国情的特定产物,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影响的深远性等特点。形成这些特点的重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治边政策与治边思想,它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加强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推进了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总结过往,是为了今天与未来。借助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深入研究与对疆域的考察,大正先生发前人之未发,提出许多极富价值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审视。从历史上看,当代中国边疆是两大历史遗产的平台,这两大历史遗产一是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二是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遗产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边疆这个因素,就不成其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边疆地区存在,那么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各民族可能也进入不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范围里。
“回顾我在边疆中心工作的岁月,大体上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为开展三大研究系列的研究出谋献策;二是为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的展开身体力行;三是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尽心尽力。”大正先生躬身力行的这三件大事,其潜在的作用、价值与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凸显出来。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除了总体上的协调组织,大正先生的个人研究与调研丝毫没有松懈,完成了从民族史研究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跨越。他的研究领域从民族史拓展到中国疆域史,特别是在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中国疆域发展的综合研究、清代新疆地方史研究、中亚史和新疆周边地区史研究、东北边疆史尤其是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当代中国边疆稳定特别是新疆稳定与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用力尤甚,用功最多,他的研究,彰显了恢宏的学术视野与崇高的时代担当,由他主编或撰写的相关著述多达15种。其中,他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他参与主编或撰写的《清代边疆政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等著述获得学界好评,多次获得图书大奖。
新疆既是大正先生研究的起点,又是他研究与考察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完成了12个调研报告,而新疆就占了一半。30多年间,他60余次来到新疆,走遍了新疆绝大多数边境线、新疆周边的邻国,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了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和察哈尔的“西进”。他通过严谨的论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当代新疆研究上取得常人难以企及并富有价值的成果。
新学科的构筑
随着研究的深入、视野的开阔、史料的充实、理论的支撑,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在大正先生心中日渐清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他认为,面对新形势的需要,应通过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的研究,总结历史上的边疆治理经验,考察当代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制定相关的边疆稳定与发展战略。显然,这样宏伟的任务仅仅依靠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不能完成的,唯有凭借中国边疆学方可达到。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追寻历史的发展轨迹,还应探求中国边疆发展的未来;中国边疆研究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还要开拓未来的发展道路。
正是这样的学术胸襟,推动大正先生的研究迈上了新台阶,瞄准了新目标,达到了新境界。同时,他也非常清楚,中国边疆学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新兴,意味着创业;边缘,意味着艰辛。早在20世纪末,这个目标就在他的心中萌动、升腾。1997年以来的20年间,他写的几十篇论文都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大正先生深知,中国边疆研究面临的任务、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宗教学、哲学、文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因此,中国边疆研究实现向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飞跃,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又是时代的要求。中国边疆研究具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具有众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支持,具有特殊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全可以并入正在发展为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中国边疆学。将中国边疆问题置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边疆学的特殊价值首先体现于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其次体现于对中国边疆及其各个局部的认识,最后体现于对边疆这一抽象的人类社会历史产物的认识,这一特殊性是任何一门学科无法替代的。
如果说上面所述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从理想到现实还需要许多铺垫与转化,大正先生将其视为“过三关”。第一关,从继承到创新。中国边疆研究已有较长时间、较大规模,尚需创出新路。第二关,从分工到合作。要在各学科领域对中国边疆研究进行分工,要有各方面的合作。第三关,从自然到自觉。要逐步将以自然应变为主的研究转变为以自觉为主的研究。与这“三关”相对应的是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研究中国边疆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关系。二是研究服务于社会需求与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关系。三是把握好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客体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关系。
对于学界关心的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大正先生也给出了初步框架。他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可以分为两个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应用研究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考古、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方面。应用研究领域是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发展与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涉及的方面与基础研究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有更强的现实性。这些全局性、战略性见解体现在大正先生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等多部著述中。
《清史》的纂修
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先生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清史纂修工程由此正式启动。对于新编清史,更是提出了明确要求:“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
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的大正先生,又站在了一个崭新的起跑线之上。这一年,他已经64岁了。
盛世修史,责任重大。当宏愿即将实现时,大正先生感到肩上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在戴逸先生的带领下,他与同仁倾其全力,投入了这一宏大浩繁的世纪文化工程中,配合戴逸先生,做了大量协调、组织与撰写工作,许多工作都是亲力亲为,狠抓落实。
16年来,大正先生参与新修《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定稿五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并先后分工负责典志组、史表组、篇目组、编审组、文献组、出版组、秘书组的学术联络工作。他认为,新修《清史》应力求写成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清史研究水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著作。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有待参与这一工程的专家们的不懈努力,最终能否达到此目标,则要由学术界同行和所有关注此工程的人士来评议。
在大正先生看来,在《清史》的纂修实践中,有四个重要因素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一是资料的利用面大大扩展,为超越和创新提供了扎实基础。二是体裁体例的布局和内容的拓展,为超越与创新提供了可能。三是科研组织和管理上的有益尝试,为超越和创新准备了条件。四是树立了从世界视野来创构编纂清史的新体系。这是新修《清史》的创新之处。
2018年10月,新修《清史》送审稿完成,计106卷,104册,另附录6册,随之进入《清史》送审稿送审、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结项与《清史》出版流程。16年的心血,16年的努力,大正先生的学术人生有了特别的意义,新修《清史》即将完成,他80岁的生日也因此平添了喜悦与欣慰。
回顾新修《清史》的学术经历,大正先生十分感慨:“这次纂修清史应该成为清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个坐标,它既是20世纪清史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是21世纪清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起点。”
“在史学领域里,我还是做了些许工作,简言之,一是习史,二是研史。研究工作优劣成败,应由社会评说,我只是做了应做的工作,在所在的岗位上尽了责、出了力,没有虚度年华。”
“中国边疆研究涉及内容丰富多彩。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似苍穹,似大海。而自己几十年研究所涉猎内容虽大都当在其中,但似星辰、似浪花。”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大正先生在《我的治学之途》中这样说。从黄浦江畔走入齐鲁大地、走进大漠荒烟、走向茫茫海疆,从青葱到耄耋,他把自己交付给了学术研究。他不曾动摇,不曾停歇;他心存高远,脚踏实地;他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他人生的行囊里,装满了历史与边疆,装满了使命与担当,装满了艰辛与荣光。
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用一生践行这个理念,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增添异彩,受到人们景仰。大正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学术探索,让人们看到了薪火相传的光芒。他踏着先贤的足迹前行,守正出新,唱响了汇入中国学术洪钟大吕的“三部曲”。对祖国的挚爱、对历史的敬畏、对治学的崇尚、对人生的追求,这正是大正先生学术自觉、学术格局的力量源泉。
八秩之年,大正先生的边疆情怀依旧,边疆激情依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热望中国边疆研究的大发展;呼喊中国边疆学的诞生!”这是一位一生研究边疆、行走边疆、情系边疆、奉献边疆的学者最大的期盼与愿景。他期待着中国边疆学这个“宁馨儿”早日降生,他要在这片热土上继续耕耘,春种秋收。在大正先生八十华诞之际,以上文字若对年轻学子有借鉴意义、对边疆研究有启迪作用,斯愿足矣。
(作者:马宝珠,为本报高级编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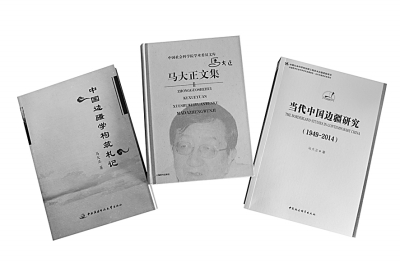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