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有许多名家,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是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如果少了他,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态,将因此而大大失衡。
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通才,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为中国现代的美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更因为,他是一个禀赋奇异、风骨高迈的传奇性人物,用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话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子恺漫画”与“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留给现代中国的两件瑰宝,时过境迁,依然熠熠生辉,滋养了几代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为人生而艺术”的“社会派”(文学研究会发起)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创造社发起)。丰子恺是文学研究会特别推出的漫画家,甚至连“子恺漫画”的称号,都是该会重要人物郑振铎发明的,由此足以证明丰子恺的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系。然而,丰子恺并不属于这一派,他的眼光,不经意间,便会穿透“人生”的表层,直抵人生的“根本”。准确地说,丰子恺对人生社会的关注,是出于佛家慈悲为怀的“护生”信仰。
相比之下,丰子恺与自我表现,崇尚天才的“唯美派”距离更远,尽管他最强调艺术“趣味”。细审之下,其“趣味”的核心,是超越艺术形式的“童心”“真心”和“本心”。因此,如果一定要对丰子恺的艺术创作下一个定义,只能是“为生灵而艺术”。它的存在,意味着现代文学史上除“社会派”“唯美派”“革命派”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生灵派”(属于这一派的,有许地山、叶圣陶、冰心、废名等人),丰子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这一派不合时宜,难成气候,却不绝如缕。时过境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
佛缘与艺缘
丰子恺一生结二缘——佛缘与艺缘。于是派生出一个麻烦的问题:艺术与宗教,情状虽相似,本质却有差别,各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与精神诉求。丰子恺因此难免经受复杂的内心矛盾与纠葛,正如《忆儿时》描写的那样:而立之年的丰子恺,津津有味地回忆童年时代养蚕、吃蟹、钓鱼的趣事,最后总是上升到“杀生”的高度,一面使他“永远神往”,一面使他“永远忏悔”。这种矛盾纠葛,在《陋巷》(1933年)中有集中的表露。
“陋巷”是圣人品格的象征,取自《论语》中“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典故。而今,守在此地遥接衣钵的,是通儒马一浮。文章记述“我”与马一浮的三次见面,禅意深致。通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马一浮在丰子恺心目中是“教主”式的存在。第一次随恩师李叔同拜见马一浮,因听不懂两位长辈的北腔方言(马以不地道的北方音回应李的天津白),愧恨无奈中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傀儡,却牢牢记住了马一浮的奇秉异相:“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一面的深黑的瞳子”。
第二次见马一浮,是16年之后,受弘一法师的委托而去。这次丰子恺能够听懂马一浮的绍兴土白,心境却与之前大不一样:他刚刚失去母亲——从他孩提时代兼尽父职的母亲,丰子恺感到自己未能对母亲尽涓涘的报答之情,悔恨至极,心中充满了对无常的悲愤与苦痛,于是便堕入颓唐的状态。这无疑是接受开解,皈依上帝的最佳时刻。耐人寻味的是,丰子恺最终还是回避了大师的开解。其中这样写道——
M先生的严肃的人生,明显地衬出了我的堕落。他和我谈起我所作而他所序的《护生画集》,勉励我;知道我抱风木之悲,又为我解说无常,劝慰我。其实我不须听他的话,只要望见的颜色,已觉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我心中似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丝,因为解不清楚,用纸包好了藏着。M先生的态度和说话,着力地在那里发开我这纸包来。我在他面前渐感局促不安,坐了约一小时就告辞。当他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感到与十余年前在这里做了几个小时傀儡而解放出来时同样愉快的心情。我走出那陋巷,看见街角上停着一辆黄包车,便不问价钱,跨了上去。仰看天色晴明,决定先到采芝斋买些糖果,带了到六和塔去度送这清明日。但当我晚上拖了疲倦的肢体而回到旅馆的时候,想起上午所访问的主人,热烈地感到畏敬的亲爱。我准拟明天再去访他,把心中的纸包打开来给他看。但到了明朝,我的心又全被西湖的春色所占据了。
这段文字,将丰子恺彷徨于宗教艺术之间的复杂情愫展露无遗。此时的丰子恺,一方面感到“无常”加给他的压倒性痛苦和颓唐,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艺术给予他的快感与慰藉,在双方博弈、难解分难的时刻,丰子恺选择了逃离,因为“西湖的春色”。
第三次见面是两年后,是丰子恺向马一浮请教“无常漫画”之事的自动访问。此时的丰子恺,随着丧母之痛的平复,心似已屈服于无常,准备对无常做长期的抵抗,并从咏叹无常的古诗佳句中寻找漫画创作的灵感。马大师这样开导丰子恺:“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似当头棒喝,将他“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他“感到无限的清凉”。但一走出陋巷,面对岁末景象和雨雪充塞的道路,丰子恺依然感到彷徨,宛如置身梦中。
其实,丰子恺写《陋巷》时,已是一名居士。5年前,丰子恺三十诞辰之日,在恩师弘一法师主持下,在江湾义永里缘缘堂楼下的钢琴旁边举行仪式,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更早的时候,在同样的地方,丰子恺请弘一法师为自己寓所命名,法师嘱他在方纸上写与佛教有关、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丰子恺连拿两次阄,都是“缘”字,于是取名“缘缘堂”。
由是观之,丰子恺在《陋巷》中的表现似乎令人困惑,其实很好理解。作为一名聪慧而虔诚的居士,丰子恺不可能不懂那些“无常”的大道理,他之所以感到愧疚,有意无意回避大师的开解,与其说是因佛缘不够深,不如说是因艺缘之力太强。细审之下,丰子恺的佛缘,是建立在知性的基础上,哲思的基础上,绝无信男善女的狂热和非理性。孩提时代起,丰子恺就被两个永恒的问号纠缠:从邻家孩子从壁缝里塞进来的一根鸡毛,可以追踪到空间、宇宙的无限,从账簿上取自《千字文》中每一个顺序排列字的年头编号,可以领悟到时间的神秘;从一个落水的泥阿福,一根丢弃的树枝手杖,一张烧成灰烬的纸,悟到世上万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都不会真正消失,都被记录在造物主的“大账簿”中。这是一个神童对“无常”与“有常”的先知先觉。
与之相反,丰子恺的艺缘,是感性的,趣味的,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救药的。关于这一点,丰子恺说得很彻底:“趣味,在我是生活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丰子恺的趣味,体现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正如《塘栖》中描写的那样:从石门湾到杭州,坐火轮、换火车只需两小时,非常方便,丰子恺却不喜欢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经常雇一只客船,顺着运河,优哉游哉地走上两三天,沿途闲眺两岸景色,或挥毫写生,或上岸小酌,其间的种种乐趣,真是妙不可言。
可以说,艺术与宗教的纠葛,伴随丰子恺一生,随着岁月推移,人生阅历增长,两者越来越趋于圆融。1948年11月,天命之年的丰子恺到厦门南普陀寺凭吊弘一法师讲律遗址,其间应厦门佛教协会邀请,作《我与弘一法师》的讲演。在解释恩师为何“遁入空门”时,丰子恺给出深思熟虑的解释:人生分三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相对于衣食、艺术、宗教;“人生欲”超强、脚力不凡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由艺术升华为宗教,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丰子恺自愧一直彷徨于艺术与宗教的十字街头,是个不肖弟子,并感叹自己“脚力不够”,只能住在二层,对三层心向往之。
丰子恺的人生三层说比喻机智,且有中国文化特色。然在笔者看来,丰子恺尽管形式上没有出家,一直停留在人生的二层,在精神实质上,丰子恺其实早已登上三层。与恩师李叔同的不同在于,登堂入室之后,丰子恺也没有忘记二层。他在二三层之间,上上下下,自由进出。唯其如此,他的艺术创作迥出时辈,妙趣横生而法相庄严,没有那个时代常有的亢奋、偏激和粗鄙。以笔者私见,丰子恺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并不亚于弘一法师。
“子恺漫画”:功夫在画外
从中国现代漫画史的角度看,“子恺漫画”的诞生颇有横空出世的意味。这并不是说此前中国没有漫画,事实上早在“子恺漫画”之前,漫画界已是人才辈出,只是没有“漫画”这个词而已,“漫画”一词的流行,是“子恺漫画”登场之后的事。更重要的是,“子恺漫画”的艺术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漫画不一样。比如与漫画大师张光宇造型严谨的作品相比,“子恺漫画”显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具有传统“文人画”的味道。
丰子恺走上漫画创作道路,有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假如没有1921年的日本之行,与竹久梦二的画作邂逅,或许就没有后来的“子恺漫画”。
丰子恺原本是为了学西洋油画,实现画家梦而去日本的。孰料一到东京,这个梦就破灭了。后来丰子恺在《子恺漫画》卷首语这样描述当时情形:“一九二一年春,我搭了‘山城丸’赴日本的时候,自己满望着做了画家而归国的。到了东京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的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每天上午在某洋画学校里当model(模特儿)休息的时候,总是无聊地燃起一支‘敷岛’,反复思量生活的前程,有时窃疑model与canvas(画布)究竟是否达到画家的唯一的途径。”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必须记住:其一,丰子恺东京学艺时,发现自己缺乏做洋画家的才力和条件。其二,由此开始思考西洋油画之外的绘画艺术之路。那么,丰子恺果真缺乏做洋画家的才力吗?
平心而论,就一个职业画家必备的造型天赋,对纯视觉艺术形式的迷恋而言,丰子恺的自谦包含着可贵的自知之明。丰子恺的自述显示,他的绘画天赋不算杰出,学画的经历也不值得夸耀,从描印《三字经》《千家诗》的插图,旧人物画谱上的画,放大相片,到临《铅笔画临本》,再到炭笔石膏像写生,都是“依样画葫芦”,缺少天才的表现。但是,如果就艺术家的综合修养,对生命万物的感悟能力而言,丰子恺不仅不是才力贫乏,简直是才力过人,正如其恩师夏丏尊在《子恺漫画》序中赞叹的那样:“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天生诗人气质、文人趣味的丰子恺,与西洋油画这种技术苦重、完成度极高的艺术品种并不相宜,正如他日后表白的那样:“我以为造型美术中的个性,生气,灵感的表现,工笔不及速写的明显。工笔的美术品中,个性生气灵感隐藏在里面,一时不易看出。速写的艺术品中,个性生气灵感赤裸裸地显出,一见就觉得生趣洋溢。所以我不欢喜油漆工作似的西洋画,而喜欢泼墨挥毫的中国画。”
于是丰子恺调整了留学方式,专业的画室训练变成了广闻博见的游学采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竹久梦二进入他的视野。那是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一次随意的翻阅,搅动了他的艺术慧根,使他欣喜若狂。十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回想过去的所见的绘画,给我印象最深而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种小小的毛笔画。记得二十余岁时,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尾至首倒翻过去,看见里面都是寥寥数笔的毛笔sketch(速写)。书页的边上没有切齐,翻到题目《Classmate》的一页上自然地停止了。”
这幅题名《同学》的画,描写两名成年妇女道上偶然相遇,一个坐在人力车上,衣着豪华,手里拿着大包装潢精美的物品;另一个让在路边,蓬头垢面,背着一个光头婴儿,面色局促不安。当年平等亲密的同学,如今一个变成贵妇人,另一个沦为贫家之妻。丰子恺被深深打动了,内心感到悲哀,感到痛楚,情不自禁对不平等的人类社会组织发出诅咒,最后赞叹道:“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
乍一看,“子恺漫画”脱胎于竹久梦二的漫画,其实只是一个触机。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梦二的漫画,好比一把强劲的东风。在此之前,丰子恺的中西绘画修养(书法与素描)各行其道,一时找不到自己的艺术方向。与梦二漫画邂逅,丰子恺如得神启,其收获有三:其一,以毛笔抒发的“寥寥数笔”;其二,令人咀嚼的“诗的意味”;其三,融化东西的“造型之美”,后来成为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三大艺术要素。
仔细考量,“寥寥数笔”与“诗的意味”,向来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拿手好戏。竹久梦二是日本南画(南宗文人画)的现代传人,又是诗人作家。自幼磨墨吮笔、吟诗诵词的丰子恺与他发生艺术共鸣,是很自然的事。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照亮丰子恺。因为在当时压倒一切的“西化”历史氛围下,艺术能否“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从这个角度看,给丰子恺带来决定性启示的,是梦二绘画融化东西的“造型之美”。正如丰子恺评价的那样:竹久梦二的画风“熔化东西洋画法于一炉。其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总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有了这样的“熔化东西”,“寥寥数笔”,“诗的意味”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名正言顺跨入“现代”的门槛。
“子恺漫画”的诞生,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件妙事。它以不可复制的个人化的方式,实现了传统“文人画”的现代转型,创化出一种雅俗共赏的“新文人画”,妙趣横生而法相庄严。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风靡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滋养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那乘兴落笔,俄顷成章,意在笔先,意到笔不到的“寥寥数笔”,是画家深厚的书法功底、相当的素描基础、文人的情思、哲人的胸怀、禅家的定力,加上不变的赤子之心,化合而成。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不足为奇的。
“缘缘堂随笔”:更上一层楼
作为一种通俗的新文人画,“子恺漫画”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相比之下,“缘缘堂随笔”主要是在文化圈、知识界广受关注。然而,与功夫在画外的“子恺漫画”相比,“缘缘堂随笔”艺术上更高一筹,理由很简单:丰子恺的文才高于画才;而且,对于丰子恺那样哲思深邃、妙想联翩的人,随笔散文的艺术载体,比起“寥寥数笔”的漫画,无疑具有更大的表现力的发挥空间。郁达夫当年就指出:丰子恺的散文有哲学味,“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平心而论,“缘缘堂随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构,妙趣横生、法相庄严中,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深邃。然而,在民族矛盾、阶级斗争纵横交织,文化激进主义应运而生的大时代,它注定被误读,被诟病,被矮化。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这样评价丰子恺:“文笔轻松通俗,趣味很浓,常有使人发噱的地方。但他的观察众生相的态度于悲悯洒脱中夹有旁观玩世的意思,不能算是健康的看法。”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丰子恺的早期散文“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矝的社会风气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时过境迁,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更,这些观点已显得简单、局促和偏狭,为学界扬弃是自然的事。
也许是旁观者清。1940年“缘缘堂随笔”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译者是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译者前言中,吉川这样评价:“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读了“缘缘堂随笔”,异常兴奋,为此专门写了评论,其中这样写道:“这本随笔可以说是艺术家的著作。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
两位日本有识之士的眼光,令人佩服。前者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了丰子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人格与人品(赤子之心与风骨),并从中国文学史的精神脉络中,对丰子恺作出恰当的定位(现代陶渊明、王维);后者心有灵犀,举重若轻,拈出“缘缘堂随笔”洞微烛幽、点石成金的艺术魔力。
笔者以为,“缘缘堂随笔”的真正价值,恰在“宗教”与“艺术”的圆融之中。表现在思想层面,是“出世”与“入世”、“无常”与“有常”的对立统一;表面在技术层面,是“大”与“小”、“藏”与“露”的对立统一,用丰子恺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缘缘堂随笔”的艺术奥妙,包含在这些貌似老生常谈的范畴中。
《敬礼》是“缘缘堂随笔”中令人拍案叫绝的一篇,其中写道:“我”伏案工作时不小心弄伤了一只蚂蚁,内疚地将它移到一边。间歇中,惊异的发现,另一只蚂蚁拖着受伤的蚂蚁,竭尽全力,往蚁巢撤离,途中两只蚂蚁互相帮助,配合十分默契。此景令“我”深深感动,情不自禁站起身来,举手向两只蚂蚁立正敬礼。文中这样写道:“鲁迅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高大起来,我现在也如此,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只蚂蚁大起来,大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
凡夫俗子看了这篇随笔,定会觉得丰子恺迂腐可笑。迂腐是肯定的,然而,丰子恺的迂腐中含有深邃的大道理。时过境迁,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态美学和地球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丰子恺的“护生”理念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尤其对曾饱受战乱之苦、政治斗争之苦,人性异化严重的中国人,“缘缘堂随笔”不啻是一副对症良药。
“缘缘堂随笔”有宗教的情怀而无宗教的说教,有艺术的空灵而无“为艺术而艺术”的玄虚。这一切,最终归结于作者的童心。这种赤子之心,丰子恺终其一生,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作者:李兆忠,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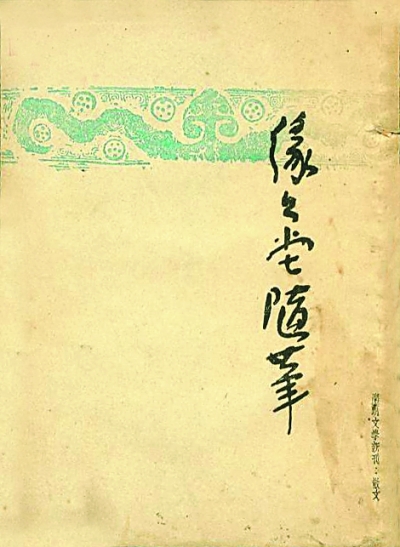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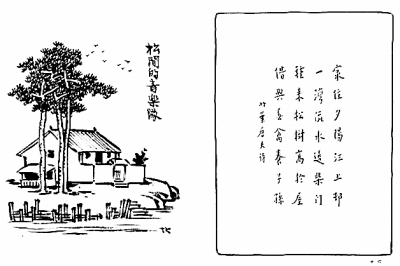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