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作者:刘庆邦,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黑白男女》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等。其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莫言自谦,愿意把自己写的诗说成是打油诗。可他有些诗的内容并不谦虚。比如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左手书法右手诗,莫言之才世无匹。狂语皆因文壮胆,天下因我知高密。”听听,莫言的口气是不是很牛。然而谁不想承认都不行,随着莫言在小说里标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标,随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振,高密的知名度的确随之大幅度提高。或者说,高密已和莫言的名字绑在一起,人们一提高密,首先想到的就是莫言,莫言几乎成了高密的代名词。
红高粱也是。高粱只是一种普通的粮食,而且是一种比较粗糙的粗粮,尽管它带一个红字,也“红”不到哪里去。可是呢,自从莫言以红高粱为题写了系列小说,自从张艺谋把《红高粱》拍成了电影,并获得了柏林电影艺术节金熊奖,不得了,红高粱一下子红光闪闪,大放异彩,不仅“红”遍了全中国,还“红”遍了全世界。
其实我的豫东南老家也种高粱,只不过我们那里一般不把高粱叫高粱,叫秫秫。玉米不叫玉米,叫玉蜀黍,或棒子。也有人把秫秫说成高粱,这样说我们也听得懂,不会把高粱理解成树木。我个人比较喜欢高粱这个名字,因为高粱的确是高,它比大豆、谷子、芝麻、玉米等任何庄稼都高出许多,叫高粱名副其实。我还喜欢在高粱面前冠以红字,这样它就以其独具的特色与其他粮食区别开了。是呀,别的成熟的粮食大都是黄色,也有绿色、麻色、白色、黑色等,只有高粱成熟后呈现的是红色。
记得小时候,我们生产队每年都种高粱,有时整块地里种的都是高粱,一种就是几十亩,甚至上百亩。我很喜欢钻进高粱地里去玩,高粱地带给我许多乐趣,给我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有一种高粱不结穗子,我们叫它“哑巴秆”。它的秆子比较甜,我和小伙伴们就把它挑出来折断,当甘蔗吃。还有一种高粱,仰脸看着它鼓泡了,里面孕育的却不是高粱穗子,是一种黑黑的叫“乌墨”的东西。我们把“乌墨”剥出来吃,吃得我们的手和嘴都染上了黑色。我们在高粱棵子钻着钻着,面前会陡地出现一座坟包,吓得我们毛骨悚然。我们遇到意外的惊喜,那必是在高粱棵子的稀疏之处摘到了一个或几个野生的小甜瓜。在初中毕业人生最苦闷的阶段,我曾一个人躺进森林一样幽深的高粱地里,一支接一支唱歌,直唱得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沉沉睡去。我多次参与收高粱。我们收高粱的办法,是待高粱接近成熟时,先逐棵把高粱的叶子打去。这个活儿不算重,但大刀片子一样的高粱叶子的边缘有许多锋利的小刺,那些小刺会把我的手臂拉出一道道血口子。据说这样做是便于高粱地通风,是让高粱全身的养分都集中在高粱穗子上,再把高粱的颗粒充实一下,也是便于高粱晒米。这时高粱秆子成了光秆,火红的高粱穗子被高高举起,重点得到充分显示。若大面积望去,集中连片的高粱穗子如天边的红云,壮丽极了!当高粱红得不能再红,我们用一种钎刀把高粱穗子钎下来,然后用镢头铲子连根把高粱秆子刨出,高粱才算收完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我还在高粱地里抓过鱼。有一年我们那里发大水,河水漫过河堤,河里的鱼就跑到高粱地里去了,挺大的鱼像狐狸一样在高粱棵子里乱窜。我把父亲带我在高粱地里抓鱼的事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发大水》。
是的,我们那里差不多每年夏秋之交都要下大雨,发大水。大水一来,那些诸如红薯、豆子、谷子等拖秧子的或矮秆的农作物就泡汤了。只有高粱在大水中屹然挺立,如浇不灭的火把。雨下得越大,“火把”似乎燃得越旺。朋友们知道了吧,我们那里为什么热衷于大面积种高粱呢?高粱因其站得高,立得稳,大水不能淹没它,就有了鹤立鸡群般独特优势。
可惜我们那里现在不怎么种高粱了,几十年都不种了。不仅高粱很少种,其他种类繁多的杂粮也不怎么种了。不种高粱的原因很清楚,一是水系通过治理,不再发大水,高粱的优势尽失;二是高粱产量低,价钱也低;三是高粱粗拉拉的,不好吃。那么肥沃的地里种什么呢?玉米,清一色的玉米。东地西地,南地北地,千家万户,种的都是玉米。玉米也是粗粮,也不好吃,大家干吗都种玉米呢?人们种玉米并不是为了吃,每年夏季所收的小麦都吃不完,谁还去吃玉米呢!说白了,人们一哄而上种玉米,受的是经济利益的驱使,玉米产量高,收购价也高,谁不想多挣钱呢!我每年秋天都回老家,看到田里种的都是玉米,一棵高粱都没有,品种和色彩一点儿都不丰富,未免有些失望。高粱呢?我的高粱呢?高粱真的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不成想在电影银幕上看到了红高粱。在劲风的吹拂下,一望无际的红高粱连天波涌,如同赤色的海潮。同时伴以高亢的的唢呐声,所有的高粱都随之起舞,似乎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欢状态。这样的画面和音乐深深触动了我,并震撼了我,使我得到了灵魂放飞般的艺术享受。
不用说,这样的红高粱是莫言的小说里写的,是电影的场景里规定的,是属于高密的,也可以说是属于莫言个人的。据说莫言写高粱也是一种回忆状态,他的家乡后来也不怎么种高粱了。但为了在电影里重现红高粱,高密东北乡必须把高粱种起来。高粱种子播下了,出苗了,由于天气干旱,高粱苗子却迟迟不能长高,可把拍电影的人急坏了。好在老天爷终于降下甘霖,遍地的高粱才生长起来,才最终以火红的面貌呈现在电影里。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从此被以电影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设想,不管过多少年,我们只要再看《红高粱》这部电影,都能看到莫言家乡的红高粱。
那么,电影拍摄的任务完成之后,以巩俐、姜文为主要角色的电影演员“刀枪”入库之后,高密是不是不再种高粱了呢?不是的,从那以后,三十几年来,高密年年都种高粱,而且每年都不少种。加上后来又有电视剧版《红高粱》在高密的拍摄,高粱的种植面积再次扩大,遂使高粱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每年都会吸引不少中国乃至世界的游客前去参观。
我去高密去得有些晚了,直到今年秋天,我才有机会经潍坊,过青州,之后到高密走了一趟。作为与莫言相识多年的文友,我去高密当然是冲着莫言的故乡去的,同时有一个不必否认的念头是,我也很想看看久违的红高粱。莫言家平安庄的老房子已无人居住,大门口一侧挂的是“莫言旧居”的牌子。门外的一个书摊上,卖有莫言的许多著作。我在书摊上买了一本莫言大哥管谟贤写的《大哥说莫言》一书。此书使我了解到,莫言的家乡和我的老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高密东北乡也是平原,也是地势低洼,涝灾频繁,所以才广种具有抗涝能力的高粱。还有一个更为相似的情况是,我们那里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匪横行,十分猖獗。而高密东北乡处在三县交界处,地广人稀,芦苇丛生,野草遍地,又有两三米深的高粱地构成的青纱帐作掩护,旧社会也是土匪出没活动的天然场所。就是因为此地太不平安,人们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才把村庄叫成平安庄。莫言的大哥说:“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在家当了十年农民,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作青贮饲料),砍高粱,卡高粱穗,吃高粱饼子,拉高粱屎,满脑袋高粱花子,做了十年高粱梦,终于成了大器。”
总算又看到红高粱了,时隔几十年之后,我终于又看到了大面积的红高粱。一走进红高粱影视基地,我就仿佛一下子扑进红高粱的海洋里,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拥过来的全是高粱。如同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欣喜油然而生。我赶紧来到高粱地边和高粱丛中,对着眼前的高粱照了一张又一张。我不仅照了远景画面,还把手机贴近高粱穗子,照了一些特写镜头。在特写镜头里,硕大的高粱穗子颗粒饱满,每一粒高粱米都像一只瞪大了的红色的鸽子眼。我看着“鸽子眼”,“鸽子眼”也看着我,似乎在对我说:“我是不是很好看?”我说“那当然”!我走进为剧中的土匪搭建的屋子,透过一个桥门洞往外一看,门外密密麻麻,站立的全是高粱。登上居高临下的观景台呢,“百里高粱地,风吹赤浪天”,景象更是壮观。
在高密东北乡,不但有红高粱影视基地,连新建成的美食城也是以“红高粱”命名。
这样说来,红高粱就不仅是粮食和物质意义上的红高粱,还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文化,升华为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红高粱。世界上不管什么物质,一旦被文化,一旦被赋予精神的意义,它的价值就会大大提高。比如玉。在外国人眼里,玉不过是一种石头。可在国人心目中,由于它的文化和精神意义不断积累,其价值竟超过了黄金。再比如紫砂壶。起初紫砂壶不过是一种茶具,但由于它后来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艺术品位不断提升,文化价值也超过了实用价值。我看红高粱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吃的,也不是用来酿酒的,而是用来观赏的,用来想象的。随着红高粱的文化价值不断增加,若干年后,谁知道红高粱会红火成什么样呢!
作为“红高粱之父”的莫言,也会为之窃喜吧!
(作者:刘庆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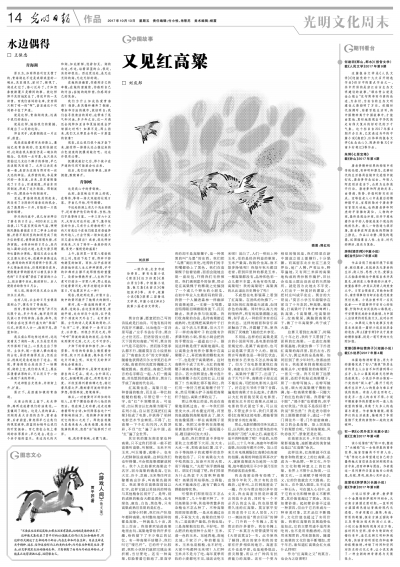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