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驻守查果拉哨所的军人将一棵白杨树拥抱成故土亲人的爱与爱情,南海小岛上的渔民夫妻将一棵椰子树拥抱成对大陆和祖国的深深眷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我将一棵胡杨树拥抱成用来流芳的诗歌情怀。60年前,一群以塞罕坝名义的人,紧紧拥抱着这棵在荒漠上独自生长了数百年的落叶松时,所表达的是坚毅、坚韧和坚定,是科学与经验的决断与求是。
在一块石头都活得无比艰难的沙漠,一棵树活得很好。
不仅很好,那一棵树还活成了别人的活路,活出了别人的活法。
行走在无比瑰丽的塞罕坝林海中,任何一棵树,任何一根草,任何一朵花,任何一滴露,都能招引出内心深处某种能量的隐隐奔突。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眼前却分明浮现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熟悉,同时心里在感受着亲切得不能再亲切的亲切,这熟悉与亲切,不是前世,不是轮回,不是重生,是实实在在可以的拥抱,可能的拥有和可爱的存在。
比如,那被林海紧紧掩藏的亮兵台,历史说的是一个王朝的强盛,并将那赭红色巨大山石做了一代大帝,壮硕的落叶松横竖成行,确实有着无敌大军所向披靡的威风。公元1681年,从康熙大帝开始,直到嘉庆皇帝驾崩前三年的1817年,136个春秋中,有百万八旗子弟来此秋狝80余次,共计千余天。几代帝王在此林深树密飞禽走兽多多之地,用狩猎替代实战,为的是训练八旗子弟护佑朝廷的本领。由此,我想起另一番情景。1998年夏天在喜马拉雅山上的查果拉哨所,见识一位年轻的士兵,那位士兵在这世界最高的哨所上守卫两年,终于下山回到位于日喀则的军营后,竟然抱着一棵大树放声大哭。在那海拔5318米的高度上,除了偶尔可见的苔藓,任何一棵略带绿色的草,都像平常家族中的高祖那样,极为罕见。共和国军人眼中的泪渗透着对生命本质的爱。只要有这份爱,即使生命禁区长不了树,心中也怀有偌大森林。反过来,一个人的王朝,秋狝声势再浩大,也还是朝不保夕。
又比如,林海中那被诗歌致敬为伟大的寂寞,一秒钟也不放过峰巅上的看山小屋。一个值守11年的三口之家和一对值守12年的夫妻,与世隔绝的4000个日日夜夜,小小的山屋筑起了森林的防火墙。这样的现实,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2016年夏天,我到那星星点点散布在南海上的几座小岛,那是真正的弹丸之地,它们小到在我父母之亲的鄂东山地与江汉平原,随便哪块忘了插秧的田头、不记得种棉的地角,都比它们的规模大。但身在南海,才深刻体会到,哪怕是只供浪花嬉戏的一块礁石,都是命中注定的国门巨锁。或夫妻俩,或兄弟仨,用来自祖国大地上的泥土与淡水,一棵树种一年,两棵树种两年,硬是将被苦咸海水泡了10万年的海滩变成伟大祖国的绿色明珠。南海上最大的寂寞是让人显得过于渺小的惊涛骇浪,塞罕坝林海的最大敌人是火灾,为防患于未然而时刻保持警惕的看山人,最大的寂寞偏偏不是将青烟当成狼烟,而是当成千年等一回的某种亲情。
还比如,1999年夏天,第一次去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茫茫沙漠中遇见一棵无限苍凉的胡杨树,当时很大的风沙吹打在汽车车身上,发出极为夸张的噼啪声。我很努力地钻出车门,迎着风沙去看那胡杨树,潮湿的眼眶无法变成心灵中的小小气候。在随后的记述中,我奋力地写了一句:独木的意义,不用成林!在塞罕坝这里,真的印证了那句不是名言的名言:隔壁的诗人是个笑话。独木不成林,这“隔壁”的千古真理,也成了塞罕坝的笑话。不是塞罕坝人不恭敬,也不是塞罕坝人没有学问,实在是由于有些真理没有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一旦有了偏颇,就成了塞罕坝人最早试种的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树苗,要么成为失意的淘汰者,要么干干脆脆、利利索索地成为不含轻蔑意味的笑话。
天交立秋,上午出门时,阳光还是满满的夏日情怀,走过吐里根河上的一处河口,穿过一道几公里长的白桦林,远远地看了几株种在某个林场女工窗前的虞美人一眼,一场秋意浓浓的大雨便不期而至。一蓬蓬的山丁子迅速将明晃晃的鲜红变幻成幽幽如紫。一团团缠在白桦林梢的清云,顺着我们的眼皮眨一下就变成浅雾,再眨一下又变成了雨幕。一垄垄的向日葵,并不是失去方向,反而更加坚决的面向大地。山坡上,平野里,所有落叶松、樟子松和云杉,将身上的针叶尖尖尽数挂上小水晶球。
来塞罕坝三天了,从最低的吐里根河谷到最高的望海楼,从一年生的、指尖大小的树苗,到与林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参天大树;从一只用来预警森林病虫害的区区试验笼箱,到足够两只老虎分封领地的广袤林区;从一套可以看清55公里外车牌号的高清监控设备,到一座可以透视60年前奋斗历史的窝棚。一切的人,一切的事,都在指向那一棵树。如此,来塞罕坝的第三天也就理所当然地奔向那一棵树。天空不早不晚地降下这场雨,似乎是在刻意强化,那一棵树的不同凡响。
按最早降雪和最短无霜期的年份计算,再有半个月,到了八月底或九月初,就有可能下成鹅毛大雪的阵势了。恰好是半个月前,我在唐古拉山下的三江源地区遇上一场大雪,在那一片树叶也不曾有过的地方,再柔软的雪花也会生硬地砸在地上。雪花砸在脸上清凉地痛,即便这样,我也不会想念任何一片树叶,因为在那片名叫可可西里的地方,除非像旗帜一样用手高擎起带有体温的树叶,否则,纵然望穿20万只藏羚羊的柔美腹部,也找不到一片绿叶的踪影。半个月前,站在藏羚羊站过的地方,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眼前遍地青枝绿叶,万里长江将会退化为何种模样。半个月后,走上兴安大岭,又是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眼前这无边无际的人造森林,那么沙暴会将北方大地肆虐成怎样的惨不忍睹?
大雨落了不到两个小时,皮肤上的感觉便从初秋的清凉进入到深秋的寒噤。身在塞外大漠,这雨落下时自由自在,没完没了的样子,有点不同寻常。浩瀚的浑善达克沙地,曾经是著名的有水沙漠,那些个深不见底的水泡子后来终于见底了,那些个暑天冰凉沁骨的泉水河也成了烫手的流沙沟。曾几何时,塞罕坝同样渴求一水而不得,似现在这样,被大雨追着撵着满森林团团转,三天两头成一回落汤鸡,实在是前辈人求之不得的美妙。如果北方沙地上的雨全部落成这种样子,500倍于塞罕坝的浑善达克大漠,也会变成500座如塞罕坝般的绿洲。绿洲的魅力令天上的云雨也难以自禁,好不容易才有的积雨云,分明应当落在别处,偏偏宁肯多走上一程,非要飘飘荡荡地来到塞罕坝。自从有了绿洲,塞罕坝年降雨量比附近地区多出50毫米,比整个浑善达克大漠的年平均降雨量多出整整100毫米。
在塞罕坝,有雨的日子让人人美妙得如同微醺。去往那一棵树的路,塞罕坝人说,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像是真的陶醉了,那个在塞罕坝当过18年教师的女子,坐在车上,眼盯着前方的路,还是走错了,不只错一次,还错了第二次。女子很惭愧,作为塞罕坝的主人,竟然将塞罕坝的客人带到塞罕坝之外,而这本是一眼就能看见分野的。女子只怪自己,没有怪那雨,那让人看不清路的大雨有一千种好!一万种好!但一千种不好和一万种不好,都是自己的不好。一旦怪罪错了,下一次雨不往塞罕坝落了,那才是最大的不好。不只是那女子,只要一提起雨,塞罕坝人立即表现出明显的崇敬,还连带说些关于左邻右舍的好话,仿佛言辞稍有不逊,在相同气象条件和相同地理环境下,好不容易比别处多落下来的那些雨,就会不再有了。
塞罕坝的雨来自九天,却带着鲜明的塞罕坝标记。从朝霞消失后开始,到晚霞升起来时结束,中间只消停了半小时。而这半小时,刚好让我们用来第一眼望见那一棵树的树梢,再在那一棵树下完成所有礼赞。那一棵树下密密麻麻尽是徘徊的脚印,偶尔也有明显深入地下的脚印,那是像我们这样与大树一同驻足的伫立者留下来的。我没有寻找,也从没有过试图寻找的念头。60年过去了,在这荒草稀疏,黄沙滚滚的大漠上,除了眼前这棵树,一切印记都不可能保持60年。在没有任何人工措施的前提下,就算放一块石头在地上,别说60年,只要6个小时,那石头是不是原来的样子,都无法确定。唯有这棵60年前的大树,一直保持着雄姿孤立于荒原。
对林海一样的塞罕坝来说,这为纪念曾经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而写满得幸天意的唯一的树,还有什么值得她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不减苍碧?还有什么需要她在沙暴滚滚的时光中独立标志?或者啊或者,也许啊也许,在岁月的老虎牙齿下有幸存活下来,在时光的钢刀利斧中侥幸逃得生天,哪怕是一根草也会具有大使命,何况是方圆数千平方公里以内仅存的一棵大树。我宁肯相信,正是为着60年前的那一天,在原始森林生长了200年,又在由原始森林退化而成的荒漠上生长了200年的这一棵树,才站在那里一年年地痴情等待,直到终于等来了自己要等的一群人。
驻守查果拉哨所的军人将一棵白杨树拥抱成故土亲人的爱与爱情,南海小岛上的渔民夫妻将一棵椰子树拥抱成对大陆和祖国的深深眷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我将一棵胡杨树拥抱成用来流芳的诗歌情怀。60年前,一群以塞罕坝名义的人,紧紧拥抱着这棵在荒漠上独自生长了数百年的落叶松时,所表达的是坚毅、坚韧和坚定,是科学与经验的决断与求是。这棵树也是如今塞罕坝上千平方公里的人工森林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这棵树叫一棵松。当地人说一棵松时,并不是说这棵树,而是指围绕这一棵松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偌大一片荒原。黄山没有因为那棵黄山松而被称为黄山松,泰山也没有因为那棵泰山松而改名为泰山松,华山当然也不会因为那棵华山松便改名为华山松。别的地方是树随地贵,塞罕坝这里是地随树贵。一棵松的作用大了,影响大了,名气大了,这地方便跟着叫起了一棵松。后来者怀着神秘的向往,站在一棵松的荒野上,寻找那一棵松。最终站到一棵松树下,用潮湿的双眼望穿连绵不绝的林海,找到那些以一棵松为榜样的云杉、樟子松和落叶松,还有那用深藏在林海的每一棵树下的泉水,汇聚而成的永远不再有干涸的七星湖、羊肠河、撅尾巴河和吐里根河。
与只有短短60年的塞罕坝林海相比,这唯一的老得不能再老的沙漠大树,是祖先一样的存在,却不是祖先。这唯一的霸气得无法再霸气的荒原生物,是霸王一样的事实,却不是霸王。这唯一的执拗得不能再执拗的旷野灵魂,是神仙一样的奇迹,却不是神话。所以,塞罕坝人才用既朴素又普通的称呼,称呼这棵落叶松为塞罕坝百万亩林海中的“第一树”。
做祖先容易,只要活过了,死后多少年,祖先的身份也变不了。做霸王也不难,打胜仗时皆大欢喜,失败了也还可以卷土重来。做神话则是最容易的,有人愿意传说就传说,没人传说时,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损失。做人做到第一却很不容易,第一是一种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点一滴作为典范,任何时候,任何情境,第一的意义并非荣誉而是起点。在第一之下,身后必须有从第二直至千千万万的其他人。做第一树,也必须有从第二棵树直至绵绵延延许许多多的树才行。
这样的第一,是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是深圳特区那样现代中国发展的第一桶金,是永暑礁那样中国边疆的第一哨位。做第一,必须经得起从第二开始的无数证明与考验。通过无数考验后证明,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中国革命的真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中国科学进步的真理,深圳特区的第一桶金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真理,永暑礁第一哨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真理。
塞罕坝上的第一树,同样是一种真理。
这样的真理是用来表明,无论是人,还是树,要扛得住一年60天的大风天气,耐得住一年只有64天无霜的日子,受得了一年7个月的满地积雪和最低达到零下43度的低温,经得起一年平均蒸发量约1400毫米的枯旱——所有这些堪为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
真理之树常绿。60年前,这个真理看上去只是帮助塞罕坝发现真正适合栽种的树,本质上是替塞罕坝发现了塞罕坝,前者是枯黄沙漠的塞罕坝,后者是绿色林海的塞罕坝。常绿的真理之树,说明了自然界一个极为简单,但常常被人搁置一旁的知识:能够生长第一棵落叶松的地方,就能够生长第二棵落叶松、第三棵落叶松、第四棵落叶松,直至让同样的沙漠上长满相同的落叶松。还有一个知识,也是人所熟知,却是人所难得做到的:这个世界不曾有过会自由自在地跑到沙漠上生长的树。尽管塞罕坝有过原始森林的历史,然而,那些人称死亡之海的,哪个不是脱了原始植被的胎,换上谈虎色变的沙漠之骨!
身为塞罕坝第一树,也不是在沙漠上发芽生根的。
塞罕坝第一树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一座原始森林的兴衰,从60年前的那一天起,又开始见证自身的兴旺。见到塞罕坝第一树之前的那个黄昏,曾登上海拔最高处的望海楼。在我的故土家乡,这样的森林瞭望台都被称作看山屋。塞罕坝的看山屋,同样看的是山。眼前的林海,每一棵树,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都是由塞罕坝人一手一脚地栽下去,扶起来,小的时候,一勺勺地浇水养育,长大了还要一个个虫子地消除病害。老天爷所能提供的帮忙,是夏天里下点雨,冬天积些雪。除此之外,便是用云遮雾障来掩饰过往历史,不让后来者回到这林海的源头,不再提及大自然与历史曾经合谋的劣迹。
60年可以是人的一生,用一生与一草一木做伴的塞罕坝,有太多的事令人难忘,有太多的人令人赞叹。在所有听到、看到和读到的人与事中,最是一句话令人暗自泣泪。从塞罕坝下来,在围场县城那个名叫六十三亩的小区里,见到几位塞罕坝林场的老人。六十三亩本来只是塞罕坝林场在大雪封山后于山下一块立锥之地的面积,也是长年累月植树造林习惯使然,塞罕坝人理所当然地将其当成了地名。创业之初,老人们正值青春年少,问起那时最难的事情,有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最难的事是说白天干的事就白天干,说晚上干的就晚上干。也有人说,冬季栽树最难,山上都冻成了冰,先是无论怎么费力也爬不上去,好不容易爬上去了,等到要下山时,又无论如何也下不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将铁锹往怀里一抱,人坐在地上,从山上一直溜到山下。说完之后,再有人补上一句,其实这也挺好玩的!说话时,那些沧桑面孔还露出浅浅一笑。人生最苦,莫过于苦中作乐。生命极难,莫过于视死如归!将往日的苦难当成一种笑谈,所达到的感动,才是千金不换的人生真谛。
塞罕坝的山岭与平野,没有哪一棵树不是由小手指大小的一年生树苗长大的。在伺候过这些树苗的女人日子里,同样是生长在塞罕坝,一年生的树苗比一岁的孩子幸福,两年生的树苗比两岁的孩子幸福,三年生的树苗比三岁的孩子幸福。一岁的孩子总是被母亲用布带系在炕上,任由其翻来滚去,只要不掉到炕下就行。两岁的孩子会走路了,母亲会用布带将那小人儿系在拖不动的家具上,任由其在屋子里的空地上做孩子想做的事。三岁的孩子用布带系不住了,要么将孩子反锁在屋子里,要么敞开大门,任他们像小猫小狗那样随便想干什么去。女人说,孩子有毛病了就会哭叫,树苗不一样,既不会哭,也不会闹,等到发现有毛病,也就没办法治了。所以,塞罕坝的女人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树苗生病出问题,却不记得亲生骨肉何时有过高烧腹泻,有没有被外面的锋利之物弄得伤痕累累。
也是因为树苗,那位刚好80岁的老人说起闻所未闻的“假植”。60年前,在没有弄清楚一年生的树苗想要安全过冬,必须让植株完全木化的奥秘时,只能将苗子从地里拔起来,放进专门的地窖里,铺一层树苗,再铺一层沙土,再铺一层树苗,再铺一层沙土,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树苗不会冻死旱死。一座分场一处地窖,一个冬天只有一个人照看,这个人往往是最年轻的,在大雪封山之前,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必须将大半年的日用食物贮备好。从大雪落下来,到来年冰雪消融的7个月里,再无第二个人出现。每天里太阳不出山,再大胆子的男人也不敢开门。太阳出山了,男人才会挑上水桶,到附近河里,砸开冰层,一担担地挑些水回,洒在埋有树苗的沙土上,不使树苗因为脱水而干死。60年后,说起这些,老人的眼神中还有20岁的忧郁在闪烁。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总有许多人和事,令公众心生感动。1998年夏季的大洪水洗劫万里长江上的簰洲湾时,那棵用自己的九死一生来拯救一个小女孩于九死一生的大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表现而成为植物界耀眼的明星。南方天时地利,插根扁担在地上也能开出花来。南方的树,只需要塞罕坝这里三分之一甚至更少一些的时间就能长大到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北方的塞罕坝,北方的树,从第一棵到第无数棵,树树皆有阻断风沙之功勋,棵棵都是改变地理天相的英雄。这样的功勋,这样的英雄,纵然数目多如星月,也不妨碍成为北方的胜境美景。原因是这用青春梦想和壮年岁月一锹锹造就的百万亩林海,这六亿多棵比原始森林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参天大树,无一不是塞罕坝人用汗水和泪水培育长大。
以对自然的不屈来表达对自然的无上敬畏。
以对人生的决绝来表达对人生的无比热爱。
常说树有多高,根有多长。那山的自然有多高?那水的人生能流多远?塞罕坝上敢问,谁说独木不能成林?这个世界更要懂得,独木何以成林?
2017年8月11日写于塞罕坝返回东湖途中
(作者:刘醒龙,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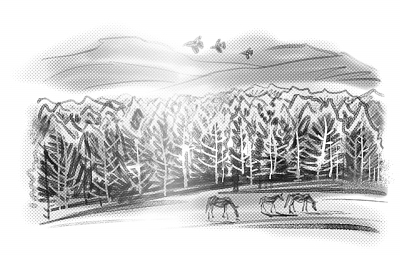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