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不再是“弱者”,也不再是“落后者”,而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我们不仅在探索中国的未来,也在探索着整个世界的出路。今天,我们期待青年作家可以讲出新的中国故事。
首先,青年作家要有“历史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其中的每个人也都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青年作家对这些变化更加敏感,如果能够真正写出这一巨变,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将会是重要的经典作品,我想这也是不少作家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写出这一剧烈的变化,我们不能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将当下的现实视为“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需要具备一种“历史感”。我们需要在历史的变迁中考察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衣食住行的变化,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时代。具有了“历史感”,也就具有了“现实感”,这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生活更加敏感,也可以在现实的变化中去把握未来。
其次,青年作家要有新的“世界视野”。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考察当代青年作家的创作。在今天,青年作家不必再以追赶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我们拥有对我们自己文化、我们所走的道路以及未来的自信,可以用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去观察与思考,这可以说是一个新视野。我们的青年作家与其他国家的青年作家共同面对着这个世界,他们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写作”,我想这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坐标。我们不仅在创造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且有可能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这是时代为我们的青年作家提供的机遇,当然他们尚需要通过作品去充分证明自己,但我想这对于有追求的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值得去努力的。
再次,青年作家要有一颗“中国心”。最近在文艺界有“中国风”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巨大历史变化的一部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再以西方文化为圭臬,而开始以中国文化的眼光打量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让“中国风”转变成真正表达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精神的艺术,怎么从“中国风”变成“中国心”。我们可以说“中国心”是当代中国人正在蓬勃发育中的民族精神,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创造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只有有了“中国心”,我们才能从内在的角度更深刻地把握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才能呈现出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心”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它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而是既“现代”又“中国”的新文化,是在当代中国现实中熔铸而成的新的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样的新文化尚在形成之中,而我们青年作家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或许可以为新的民族精神融入自己的力量。
(李云雷,男,1976年生,中直代表团代表,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代表作品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
诚实,是诗人面对世界的首要方式
在我看来,诚实是一个诗人面对世界的首要方式。即是从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遵从内心的情感,听从内心的呼唤,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因此,每一次写作我都试着从灵魂深处迸溅出我最真实的声音。我写下对亲人的爱,对故乡的牵挂和回望,对生活的感激和信心,对孤独的生命被荆棘刺破后带来的疼痛和颤栗,对贫苦的底层人民抱紧骨头也要顽强生活的感动……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努力去要求自己不要哗众取宠,不要随波逐流。即使遭遇写作的困境,我也努力去要求自己脚踏实地,不逃避,不偷懒,不投机取巧,不夸夸其谈,不矫揉造作。当然,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倍加努力,在前方漫长的道路上诚实地面对世界,用心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力争在创作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自我、面目清晰的自我。
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强调文学的“真善美”。“真”,在我看来就是诚实。说起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也许有人会不屑一顾,甚至是嗤之以鼻,但扪心自问,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在面对诚实写作的问题上,我们都需要持续地反思自我和审视自我。在这不断的自我检阅和自我反省中,我相信大家都有着相同的感受,那就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上面目模糊、千篇一律的伪写作异常泛滥,特别是在一轮轮的题材热点和诗歌话题中,很多写作都是争先恐后的模仿和跟风。不可否认,我们丢失了很多宝贵的诗歌品质,丢失了很多汉语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随着博客、QQ空间、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不断充斥我们的生活,有不少诗人在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没能再去展开想象的翅膀,在面对日益含混的内心也未能保持独创的勇气。
当我们摊开一张白纸,或是面对电脑的空白文档进行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论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是欢笑还是泪水,是悲伤还是喜悦,都是世界对我们慷慨的馈赠,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一笔财富,因而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这个世界,以心灵博大的过滤器,去掉浮华的尘埃和光鲜的泡沫。当我们拥有一颗诚实之心,我们就会自觉地投身到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脉动中,自觉地对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和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发出真实的心跳和呼吸。我们也会自觉地保持着一份自省、自律的写作意识,保持着一份向难度挑战的创作勇气和信心,如此才会具有创新、探索、突破和超越的精神,才会更深刻地表现出人类心灵的宽广性、灵魂的多样性和精神的复杂性。
(熊焱,男,1980年生,四川代表团代表,诗人。现为《星星诗刊》编辑,代表作品有诗集《爱无尽》。)
生活远比想象更精彩
世纪之交,马烽老还健在,当时我正编辑着《山西日报》的文学副刊,马老让他秘书给我送稿子的时候,经常会附一张小小的便笺,叮嘱我要学会多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要我牢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说实话,我当时完全不理解这句话。当时我正处于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就是写个人体验,但是很快出现了问题,激情依然高涨,技法也日渐成熟,但是写作素材重复使用率越来越高,我开始恐慌,第一次,我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把表现对象从个人体验转移到社会大众。正巧省作协物色青年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我就被派回故乡洪洞县挂职县长助理,并且积极地投身了当地的实际工作。
然而,我没有想到,作为一名作家,我缺乏的,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了解,更是对时代变化和社会状况的基本认知。即使回到了我的故乡,再次面对我熟悉的人,也带给我强烈的陌生感。比如说,在许多人眼里,更多的是在文学作品里,乡村干部的形象都是欺男霸女、贪污腐败,然而就我接触过的干部,大多都是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我想举一个乡镇书记和县文化馆老馆长的例子。2007年底在鲁院学习时,突然接到县文化馆老馆长的电话,说我们花费两年心血的三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专家评审会,要在北京大学举行。我第一次向学校请了假,来到北大参加评审。我的右边,是婚俗项目所在地原来的乡镇书记,在最近的干部调整中他调到了别的岗位,新的继任者已经上任,但他还是坐了一夜火车,赶来北京开这个会。我的左边,是年龄大我两轮的县文化馆长,他已经到龄,回去就要卸任了,但他依然毕恭毕敬地请专家们发言,一丝不苟地回答着他们的提问。这位干了一辈子的老馆长,长着一张黝黑的农民脸庞,五短三粗,所有的指纹里全是黑色的风尘。作为作家,我们有时习惯于想当然地从别人的作品里获得自己对某种身份的人群的判断,或者类型化、概念化地看待某一类人,而我们其实对很多原本应该真正了解的事情所知甚少。
挂职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从对社会的了解到对人性的思考都太匮乏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不自信,为了抵消这种情绪,我投入到了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包村子、跑项目、出差、下乡、开会,和各种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我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基层干部,那颗敏感的内心也坚强起来,生活让我从一个多愁善感的作家变成了阅历丰富的勇敢者。同时,我对这个时代大众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有了一定的把握。
多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同样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从热衷各种探索和实验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发现现实主义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现状,同样直面人的精神境遇,他们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李骏虎,男,1975年生,山西代表团代表,小说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兼创研部主任。代表作品有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慢慢活,慢慢写
在写作上,只要是我能慢下来的时候,只要是我真正地慢了下来,慢这个字都会给我丰厚的馈赠。我稍微像样一点儿的作品,比如《拆楼记》和《最慢的是活着》,都是我以慢状态来创作或者以慢状态来积累才得以收获的。我深知,作为一个才华非常有限的人,正是因为慢,我才可能做出了一点儿成绩。因此我会常常奢望,并用这种奢望来试图要求自己: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如果你更慢一点儿,可能会写得比现在好上一些。
这个世界,快,处处可见,在每个行业每个领域每样事物里,少而珍贵的都是慢。写作也是一样。所以我想,也许我们真的不需要跑那么快,我们需要慢一些,再慢一些,更慢一些,远远地落在众人的身后,落在众声喧哗之后,在万籁俱寂里,拿起自己的笔,敲动自己的键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她本身就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精神事业。在这个到处都呼喊着“更快,更高,更强”的时代,她就是一棵棵长得很慢的树木,像银杏,像冷杉,像黄花梨,像檀香。我们应该有耐心也必须有耐心等待着自己跟随着文学的心跳慢慢地承受和享受,才有可能抵达我们所期待的境界或者梦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像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的队伍里,唐僧最弱,最慢,因为这弱和慢,他必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取经的队伍里,只有他是最笃定的取经人,所以在精神的意义上,他又最强大。怀着对这世界的大天真和大慈悲,他慢慢地走过了一山一水,而所谓的真经,也正是因为被他坚实的步履一笔一划地书写了出来,才能够呈现出最宝贵的意义。你能想象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去取经吗?
三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曾送给了我三个字。她说:“要从容。”她雍容宽阔,著作丰硕,自己就非常从容。这几年,我一直记着这三个字,要从容。对于写作这个领域而言,在座的各位都很青春,都很年轻。所以我知道,你们一定常听前辈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对此,我要说,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青春和年轻只是一种很普通很普通的概念性资源,没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人都有,也都会有,如果你以为以此就会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那只是一种客气的理论。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世界不是你们的,也不是我们的,归根结底,世界是文学的。每一个写作者都试图在用文学来抵抗岁月,抵抗生死,抵抗虚妄,要想让自己的抵抗变得坚实有力,我想,除了让自己在从容中获得慢,在慢中获得从容,然后以这从容的慢和慢的从容去淘漉出文学的金子,也许我们没有更好的立场和选择。
最慢的是活着,最慢的也是写作,最慢的是在活着时写作,最慢的也应该是在写作中活着。
(乔叶,女,1972年生,河南代表团代表,小说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散文选刊》杂志社副主编。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散文集《坐在我的左边》。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胸怀中国梦 传播正能量
通过这几年的创作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切切实实端正方向,扎扎实实体验生活,结结实实担当责任,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是一名青年作家的天职和使命,也是一名青年作家健康成长、不断进步的关键!
双眼:切切实实端正价值取向。世界观是人生的方向盘和指南针,代表着一个作家的价值向度和精神高度。2008年,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决定选择广东省原省委书记任仲夷为典型,反映这一时代主题。但有朋友劝我说,任仲夷已经去世多年了,不如去写在任的官员或企业家,既能交朋友,又能提供赞助。但我没有动摇。我费尽周折,多方采访了任仲夷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2010年,“道德模范”郭明义的事迹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这位鞍钢最基层的工人就是体现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典型。于是,我深入到他工作的班组和生活的小区,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幸福是什么》。
双脚:扎扎实实走进生活现场。为了真正走进大工业生活,我决心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炼钢炉前体验生活,而且越是节假日越要与工人们在一起。那一年除夕,我在火红的炼钢炉旁和工人们一起值班,当外面的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猛地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整个国家的工业系统就像一个无形的须臾不可停顿的巨大链条,环环相扣,隆隆运行。这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脉博!我的心底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热辣辣的感应。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起事故:钢水大喷。那一刻,我亲眼看到了什么叫做赴汤蹈火!我写出了自己的工业题材作品《宝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双肩:结结实实担当社会责任。作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所以,作家,特别是我们青年作家,要有血性,更要有担当。眼里有深情,心底有大爱。责任在胸中,使命在肩上。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当天夜里,我就主动请缨参战。我背着睡袋、干粮和饮水,步行在滚石乱飞的山路上采访,几度死里逃生。回来后,我创作了一部长篇和3个短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又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18个小时,几次昏倒,只能依靠吸氧和喝葡萄糖维持,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了4篇报告文学。
这几年,面临国家的重要宣传活动,只要组织一有召唤,我都是不讲任何条件,立即出发,保证完成任务!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们一定要胸怀中国梦,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书写,为文化大繁荣的春天敬献上各自的青枝绿叶和姹紫嫣红!
(李春雷,男,1968年生,河北代表团代表,报告文学作家。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宝山》《木棉花开》。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青春的继承和选择
祖辈作家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几乎都在谈自由、战斗、国家前途这些宽广宏大的主题,和他们相比,我们的追求显得过于现实、自私、软弱无力。如今我们有那么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人生选择,我们对文学却没有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深沉情感了。我们远不如我们的长辈那么天真、纯粹,满脑子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早熟而又自负,缺乏社会阅历和责任感,难以抗拒物质和功利的诱惑,思维方式几乎相同,我们这代人正在被这个娱乐化的时代撕扯、伤害、损坏,我们被手机、微信、网络和各种商业娱乐资讯淹没,既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欠缺文化经典阅读的积累,再加上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时间支离破碎、物质诱惑太多……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敌人,我们在继承前辈的文学精神方面存在巨大的障碍。
我记得有一位好友对我这样说:我们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有能力做好其他任何繁琐复杂的工作,但可能就是无法做好文学,因为文学是最具创造性,也是最为内心化的精神产品。文学需要我们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有细致的感悟,但目前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基本脱离了这些,我们不断地书写青春,试图用文字留住青春,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迅速走向了世俗,走向未老先衰的所谓成熟。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写作上最大的难题,在于怎样把握并表现时代与个人的精神冲突。
无论是在文学的语言风格上,还是在写作者的个人品格上,我们都需要向前辈作家学习,写出那些既有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又有当代文学创新精神的作品,反思并且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每当我发现自己沉浸在肤浅的娱乐当中时,内心会感到非常不安和不甘。我知道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必须大量地阅读经典文学,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发现生活的美好与事物的真善,以青春的叛逆精神,去抵制那些非文学的虚假写作。
(冬筱,男,1990年生,浙江代表团代表,小说家。上海海事大学学生。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流放七月》、小说《塔岛》。)
用童话与生活对话
与生活对话的方式有千万种,很幸运,我找到了童话。
我庆幸能够用童话的眼光来看世界。柔软,并不是软弱,它包含着宽容,柔韧和永不散去的某种温暖。这种眼光,是我与生活对话的方式,也是我与世界对抗的方式。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一种渴望。我希望当人们读完我的故事,再看到身边的生活时,会感到有些许的不一样:在堵车路上,有一个用笛声放牧车辆的毛毛球;在城市上空,有一片自由自在的海洋;在收破烂的小巷里,有一把庇护着我们的透明伞;在闷热的工地上,有一台会奔跑的挖土机……
这样的想象,不能改变生活,却能让人在一个短短的瞬间,感到与生活同在,却很少被念及的一种美好。
发现美好,想象美好,品味美好,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很弱小,却很重要。
无论我们年龄多大,无论我们身份如何,我们都渴望着一个美好的世界,不是吗?渴望美好,才可能创造美好。
与生活对话的方式有千万种,我选择童话,选择手举光亮,并把这点儿小小的光亮做一颗种子送给和我一样,最终将从童年离开,独自面对未来的孩子,以及已经从童年离开,在生活中奔波挣扎的大人们。
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童话写作绝不仅仅是“鸟言兽语”或者“镜花水月”。和所有的文学创作一样,它承载的是写作者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会。这种感悟与体会来源于实实在在的个人生活,来源于蓬勃鲜活的个体生命。童话写作者当如珠贝含沙,坚韧地含入生活的沙粒,用自己的生命去感受它,用语言文字去润泽它,最终将一颗光亮美好的珍珠奉献在孩子们的面前,让他们喜爱它,亲近它,记住它的光亮与美好。待到他们长大,真正在生活的沙尘中穿行时,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需要温暖和鼓励的时刻,能够回想起他们童年时记住的那种光亮与美好,然后抬起脚来,继续前行。
安徒生说,最好的童话其实是人的生活。我愿意用童话与生活对话,并深深感谢童话让我听见的,生活另一面的美妙声音。
(左昡,女,1981年生,中直代表团代表,儿童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代表作品有童话《住在房梁上的必必》《像棵树电影院的奇闻轶事》。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童话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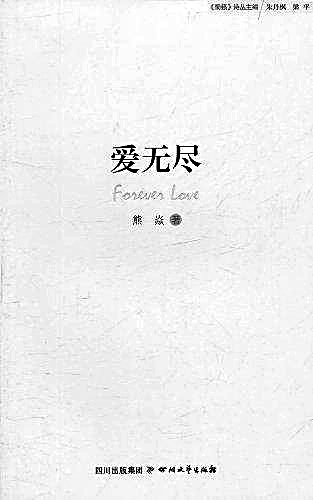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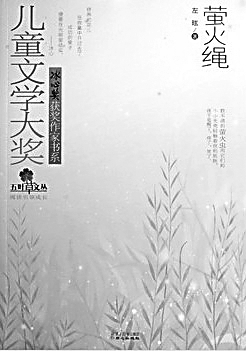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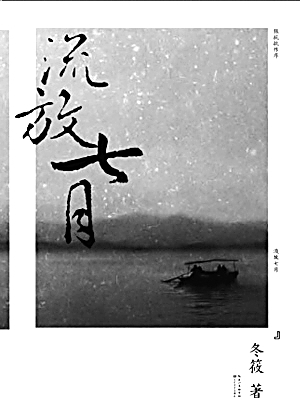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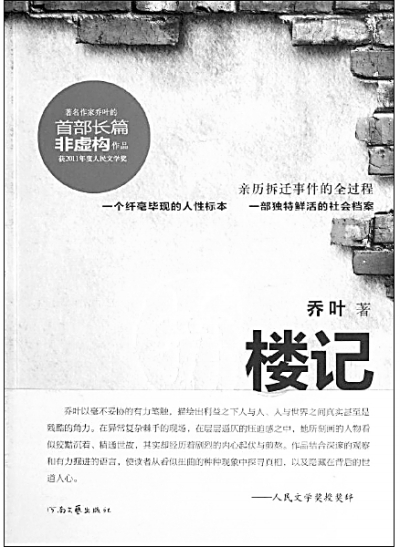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