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先父祥凯先生的墓志铭上对他的书法有着墨:“工书,兼擅各家之长,又独出机杼,下笔严整有度,苍劲峻拔,一如其为人。”父亲的本行虽为医生,于药性药理是行家,但他最钟爱最精通的却是书法。
初中未毕业,父亲就辍学回家,因瘦弱不宜扛农活,便去拜师学医,那年15岁。师父是一位老中医,见了面,看看父亲写下的几个毛笔字,就收下了他。他的师父很注意培养徒弟们的文化素养,除了学专业,还要求他们多读古诗词,练习毛笔字。父亲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真练习书法的。
参加工作后,父亲仍坚持临帖,除了颜体,他还临过何绍基、欧阳询、赵孟頫,最得意的还是柳公权。他的柳字险峭坚硬,一丝不苟,一如其为人。此外,他很注意练习行书和草书,草书讲究随意,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父亲的草书也是自由发展,自成风格。
“文革”时,父亲正当青春,公社每年的水利建设都要派他去当卫生员,同时做些宣传工作,写诗作词、印制小册子、写墙报,对于有书法基础的父亲来说,可谓如鱼得水。甚至,家乡的一个大坝竣工后,其上题写的五个大字都出自父亲之手。后来,父亲调动了工作,但无论做什么行业,父亲对于书法都是一往情深,不懈习字。
父亲对书法的爱好,使得我们家文化气息渐浓,墙壁上处处贴着父亲的字画,老杜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陈与义的“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等等。每年春节前是父亲最繁忙的日子,请父亲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老家那边的习俗,春节中堂上要贴一整张白纸书写的诗词,两边伴以喜庆的红色对联。中堂需用大字,父亲蘸饱浓墨,从容运笔,犹大匠之挥钝铁。清代书家何子贞每书至大汗淋漓,我想也不过如此吧。我奉母亲之命去接父亲回来吃年饭,但总是很难把他接回来。他的面前堆着很多纸张,他说,人家一年到头就求这么一回字,应该满足人家。来求春联的人总是买一支笔或一瓶墨汁送来,算是笔润。而我呢,则成了父亲的帮工,他写字的时候我帮他把纸扽平。待到终于可以回家了,家人早已望穿了双眼。
我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偶尔回家,仍然感觉到父亲对书法的热情。他一有闲空就展纸濡墨,任情挥毫。每当父亲的书法作品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了,他总会在来信中提上一笔。父亲来北京小住,最喜欢跑书店、看字帖,自己中意的就买回家收藏,不厌其烦。有一次,趁着父亲在京,我从市场购回几轴空白条幅请父亲写字,父亲非常高兴地写了一幅“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我立即将它挂在了墙上。
后来父亲病重,期间偶尔需要留下一些文字的东西,下笔时仍然非常认真,如锥划沙。
如今,先人已矣,父亲留下的书法我都珍藏着,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总能看到父亲当年青春飞扬的影子,忆起父亲这一生与书法割舍不断的情丝。父亲对于书法的执着,以及与之有关的为人处事之道,我也谨记在心,生怕对不住父亲一生的努力。
(作者为某出版社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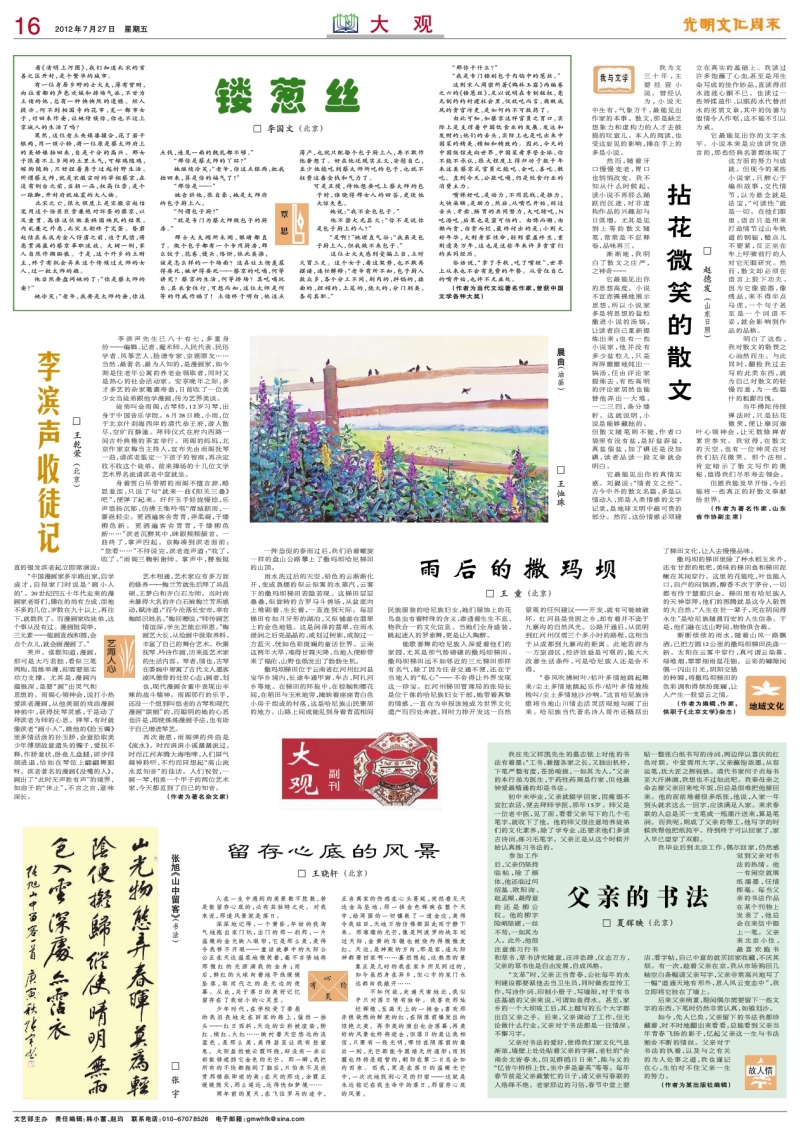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