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本栏目选载了陈寅恪童年时的点滴旧事。
1902年3月,未满12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寒假回国后,因健康状况欠佳未再赴日。后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1909年秋,由亲友资助,独自远赴德国留学。此后几经周折,于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修梵文及巴利文。
1921年秋,父亲结束了在哈佛的研习,离开美国,重返德国,申请入柏林大学哲学门,11月3日入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教授,吕师治学领域广博,除精于古印度语文外,对碑铭学、多种古文字学也有卓越成就;法西斯政权想利用他的声望为其政治服务,他为人正直,不愿与纳粹合流,于是1935年悄然提前退休。父亲随吕师深入研究梵文及巴利文等约四年;同时还聆听其他著名学者的讲座,如治学领域广博的东方学家缪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ueller)等,也深受他们影响。父亲并努力学习藏文、蒙文、满文及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在国外他还学习数学、天文等数理知识。1961年美延由复旦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前,蒋天枢先生向她出示父亲所寄存的一些练习本,大多是在德国学习各种语言文字的笔记,美延取了其中几册父亲演算微积分的练习本及天文星图,带回广州。美延素来知道父亲一直对此颇为爱好,并且想培养幼女对这方面的兴趣。所带回广州的练习本、星图,经历“文革”业已无存,幸而留在蒋先生处的本子,未遭湮灭。
父亲此次由美国转学德国,与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在柏林学习期间,两人也过从甚密。父亲与俞大维从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1921年至1925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窗七年,朝夕相处的共同学习生活经历,奠定了他们日后的深厚情谊。二人都好学深思,孜孜不倦,说诗谈词间论经史,每多共识,志趣相投,深为默契。他们不仅经常谈论学问、理想及人生,还注意国际国内时局动向。生活上也同甘共苦,有一次,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从美国来到德国,父亲和俞大维招待他们看歌剧,将客人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离去。赵、杨感到诧异,父亲才解释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戏票了。若也陪你们看戏,就得吃好几天干面包。”赵元任夫妇领了这份情,感慨万千。父亲和俞大维海外留学,不时遇到“经济危机”,有时是因公费接济不上,或与其他中国留学生经济上相互支持,更多时候是手上有钱都拿去买书了,所以生活不免常会拮据。哈佛同学都知道,陈寅恪和俞大维是中国留学生中,在海外藏书最多、搜购书籍最勤者。父亲在德国学习期间还与傅斯年(孟真)、毛凖(子水)等我国留学生交往较多。傅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由于同窗共处,时时交流,俞大维对表哥寅恪的治学重点、目的和准备,了解多,体会深。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诸大家。”“诗,佩服陶、杜,……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对于史,他无书不读……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他除学梵文外,还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等,充分掌握了可直接阅读蒙古史资料的文字工具,完全可写出一部新的蒙古史,可是由于战乱的时代背景,“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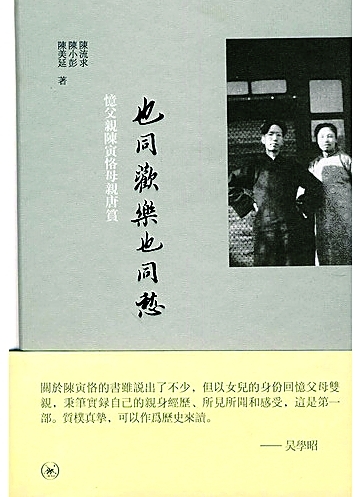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