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哈密瓜都是一个神,用自己个体的方式守护着古老的家园。哈密因为拥有了哈密瓜,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城。哈密的密与“蜜”谐音,而哈密瓜又充满甜蜜,这让哈密这个词语有了一种被植物包裹的滋润,一种别有洞天的丰盈——
丁燕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市签约作家。
再甜不过哈密瓜
桑葚才肥杏又黄,
甜瓜沙枣亦饭粮。
村村绝少炊烟起,
冷饼盈怀唤作馕。
林则徐在《回疆竹枝词》中,描绘了新疆很普遍的一种饮食习惯:以瓜代饭。
我家的屋后就有个大瓜园,很容易就能吃到甜瓜西瓜。吃瓜之前,母亲总会叮嘱我:先吃西瓜,后吃甜瓜;甜瓜要少吃,西瓜则可多吃。哈密人并不把甜瓜叫哈密瓜,就叫甜瓜(像北京人从来都说去八达岭,而不说去长城一样)。甜瓜糖分足,吃多了容易上火;吃了甜瓜再吃西瓜,嘴里就会没味。
我并不知道自己吃的就是“著名”的哈密瓜。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间或咬两口馒头或者馕,也就饱了。吃完瓜后,手指间黏黏的,几乎分不开。瓜皮很薄,像根面条,母亲不让乱扔,收拢在盆子里,喂羊。
父亲将瓜摘下来,装在麻袋里扛回家。解开扎在头部的麻绳后,瓜就四散着滚了出来,躺在床底下。吃的时候,拔拉出来一个,先放在渠沟里泡半个小时,再切,又冰又脆。西瓜要从中间切,甜瓜则从一头切到另一头。
哈密瓜非常适合生长在哈密。
有人从哈密拿走瓜的种子,试图在别处试种,也结瓜,但口感和黄瓜差不多,不甜。哈密瓜就喜欢哈密这样的气候、土壤和雨雪,对哈密可谓情真意切。但我对哈密瓜的感情,却是离开了故乡后才与日俱增的。
盆地塑造了哈密,给了它甜蜜无比的哈密瓜;但同时,盆地这种锅底的造型,也局限了哈密,让它很容易满足于自己的圆。在少女的我看来,这个炎热、干燥的地方,处处充满了守旧、固执。我要离开它,像飞蛾扑火——热情中携带着不可名状的毁灭性。但我知道,那蛾一直暗潜在我的体内,仿佛深处的胎记,不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一种搔痒的呼唤。
我是二十二岁时离开哈密盆地的——这是一个成年人的出走。我两手空空荡荡,就跑到了另一个城市,开始了颠簸不定的异乡生活。离家的那一天,我对母亲说,我要走。那是九月,哈密的金秋季节。她只是点点头——她不知道我的决心有那么大,根本不是出去走一走,而是打算一走不回头。
那是一个黄昏。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回望那个如血的黄昏。我推开那扇褐色木板门,站在田埂上,夕阳就垂挂在眼前的树梢上,无言地辉煌着,似乎要将胸中所有的鲜血都吐出来,只为求得这一刻的平静。
我不能回答自己的大胆,只是朦胧中有种警醒。许是甜蜜的哈密瓜吃多了,想自己找点苦?我试图反抗的力量那么微弱,但又那么尖锐执拗。这个盆地于我,更像是个蜜罐般的水潭,我若贪恋它现实的甜美,就将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将如何拯救自己的未来?
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子,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最终找到了“文学”来夸张自己的责任。既然手推车不好玩,既然种菜不懂行,既然初恋已破灭,既然没有什么好工作等着我干,那么,何不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一切?!
“另一个城市”——一个真正的城市。我跌跌撞撞地上了一趟开往他乡的火车,将这个烤焦的盆地甩在脑后。我以为我从此可以脱胎换骨变新人,殊不知,我的雏形是在这里的阳光中锻造出来的,我那火暴的脾气,透明的无知,坚韧的耐力,无不是这个果园里结出的果实。
我无法摆脱哈密,就像我无法不看见哈密瓜一样。超市中,我和哈密瓜仅仅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但我知道,在我和这个水果之间,相距十万八千里。而这,正是我和哈密的距离。我们如一对苦恋的情人,可以相互凝望,却无法合而为一。直到我不再能随意享用甜瓜时,我才发现,“哈密瓜”含义繁杂。
每一年的冬夏秋冬,对于哈密瓜来说都一样——诞生、通婚、死亡……这个水果有它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它是它自己的国王,在一个封闭循环的制糖流程中维持着物种的尊严。它独立运作着,千年不变。和那些树木、花草、鸟与风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繁衍生息,轮回复转,没有卑微,亦无高尚。
每一个哈密瓜都是一个神,用自己个体的方式守护着古老的家园。哈密因为拥有了哈密瓜,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城。哈密的密与“蜜”谐音,而哈密瓜又充满甜蜜,这让哈密这个词语有了一种被植物包裹的滋润,一种别有洞天的丰盈。
“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
我不信上帝,但却无法忘记童年里吃过的哈密瓜那特殊的滋味。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楼群密布,植物稀少,几乎看不到昆虫和鸟类。人们目光所及,皆为水泥、钢筋、汽车和广告牌。人们对于季节和自然的感受力和敏感度大大下降。刮风如何?有玻璃挡着;下雪如何?有空调开着;人们可以面对电脑电视,持续十几个小时,独自微笑,或独自哭泣。
我常幻想,如果我是一颗长在瓜秧上的哈密瓜,我将在自己的身体里涌动波浪,寻找甜蜜,传播甜蜜,还要像候鸟那样去找寻祖先的栖息地。我要查看一下,一颗哈密瓜“来”的道路,难道就是它“去”的道路?
如果上帝注定它不是那些开在深山野林的自生自灭的小花小草,而是凭借着独特的魅力,骄傲地在人世间走了个来回的王子,那它一定有一套自己计算得失的系统。我想参透这些玄机奥妙。
可是现在,我却只能默默地注视着它——当它被长途运送到异乡,作为商品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感到心跳加速,有了再一次逃离的冲动——虽然这次,不用再向母亲通报——我也许该走得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故乡,看看记忆中那个有着褐色门板的院子——是不是事情就是从那里开始错起?我已经得到了太多的结论,留下了太多的过程,却要异想天开地希望重新回到从前?
我曾在很多城市吃过哈密瓜,味道几乎令我愤怒——我不相信这是产自哈密的哈密瓜;就像现在,我看见那棵放在玻璃橱窗里的哈密瓜时,居然有了回乡的愿望。
我不相信,我真的那么没心没肺。
虽然时代大变,到处都是摩天大厦和立交桥,许多人都拥有了私家车,忙着在豪华包厢里K歌,而我却越来越言不达意,落落寡欢。深夜中惊醒,常常有种突兀的伤痛之感,发现自己多么焦灼狼狈,似乎身后被一群土狼追击,一直无处藏身。
没有瓜,会像我家院子背后瓜地中结出的哈密瓜那样甘甜;没有人,会像故乡老屋中的母亲那样,将我左右惦记、日夜思念;
我想要重回故乡,看看那里的天与地,尝一尝那里的哈密瓜。我愿一个人潜行在夜空的乡间小路上,让自己的脚重新触摸到一种久违的柔韧。
也许我应该有这么一次远离。如果我闭上嘴,回到我的乡村我的老屋,我将会发现寂静多么喧嚣——任何声音都会被衬得膨胀了好多倍。风吹过堆满柴的屋顶,呜呜咽咽;溪水从院内的小渠流进瓜园,熙熙攘攘;木门吱吱一声就开了,邻居家的狗吠和婴儿的啼哭一起一伏……
惟有哈密瓜沉默不语。它像一个神话部落的王子,日趋成熟。当它长到足够大时,整个哈密就成了它的后花园。
亲爱的哈密瓜,和你重逢,是时候了。
瓜的活历史
在哈密贡瓜园内,有一处哈密瓜历史文化馆。
木门,墙外凹陷着几个对称的壁龛,旁边搭着茅草棚。馆内墙角坐着留长辫子的瓜农雕塑,墙上钉着种瓜用的各种农具,地上躺着各色哈密瓜,还有一幅幅大型浮雕,配合着电视里讲解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已将哈密瓜的历史介绍得足够清楚。
旁边是个塑料大棚,进入后,看到一些绿色的秧苗攀附在麻绳上往上爬,样子很像豆角,但却是哈密瓜。蹲下细看,各种不同品种的瓜,叶片的形状完全不同。有的像葡萄叶片,是五角的;有的像萝卜叶片,六、七片小叶子组成一个不规则的圆锥形。再看那花儿,有的黄花拥挤成一片,有的则间或有那么一两朵。在有的小黄花下,悄悄肿起了一个小宝宝,手指肚子那么大,就是小小的哈密瓜!
也有大一些的,顶端的黄花开败了,一团干枯的花儿蔫了,但还缀着。在这样小的瓜上,就已经能看出纹路了。仿佛婴儿的小手小脚,一出生就带着掌纹。
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眉毛的,脸上身上同样也长着一层细茸毛。而在这些哈密瓜的身上,同样也覆盖着一层白茸毛,细细密密地包裹在表皮之上。阳光下,这些小瓜的模样真像是睡着了的婴儿。如果从侧面看哈密瓜的叶片,会发现它背面的纹理较之表层更深刻凸凹得多。从主干道上分开些岔后,越到叶片的末端,纹路越细,最终连成了一个网。
极少有人能看到哈密瓜开花,就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马铃薯的花有香味一样。那些开在绿藤上的五瓣小黄花,是哈密瓜特别的笑脸。它们天然而多样,每一朵与另一朵都不相同;每一朵花儿都像是携带着一个微型爆破筒,在你看到它的一瞬间,“啪”地炸响,裂开那事先没有预设的笑容。
此刻,哈密瓜的苗子已有半人高了。大棚内温度较高,能看到田垄上覆盖的薄膜上聚集了很多小水滴,大大小小连成一片。就是这些水滋养着哈密瓜的秧苗。每一滴水,都会面对每一朵花。没有浪费的。
哈密瓜和西红柿、茄子等植物一样,需要打岔,就是将两株并排生长的嫩芽去掉一个,好让养料只充分地滋养一株即可。
小时候,我常和母亲给西红柿打岔,至今仍记得那从植物身体中流淌出来的绿色浓汁非常汹涌。打完后,满手都染着墨绿,用肥皂或洗衣粉皆洗不干净。母亲甚至用半块砖头在手掌上搓。
现在给哈密瓜打岔并不直接用手,他们用一种微型的小剪刀,咔嚓,随着一股汁液流出来,一根瓜秧就歪下了脑袋,仿佛一起宫廷内战,瞬间就消灭了对手,将领土让给了惟一的头领。但这并非残忍。对任何动植物来说(包括人类),若有两个物种并列出现,一定会呈现出一个强而另一个弱的态势,绝对不可能两强或两弱。若保证物种更好地繁衍,必定是干脆将另一个去掉,从根本上消灭了可能,好让养料充分得到利用。
哈密瓜秧太娇嫩了,几乎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往高长。他们就拉了一道麻绳,让它依附着攀爬。远看,是一道风景;耳边,响起那首著名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如果没有人的帮助,这些瓜秧应该爬行在地上。
这些长在大棚中的哈密瓜,虽然和田野中的仍有很大差别,可这里毕竟已经有了植物的清香,泥土的甜腻,让人的内心感觉平和踏实许多。
在我们注目这些哈密瓜时,真的有了一种前身今世的知遇之感。它们的叶,它们的蔓,它们的花,它们的果,难道不是一部活历史?
没有什么,比活物更形象生动。
老式哈密瓜
哈密瓜极富营养。
单那含糖量百分之十五的指标,就足以令它鲜美。
在每一百克瓜肉中,含有蛋白质零点四克,脂肪零点三克,灰分元素两个克,钙十四毫克,磷十毫克,铁一毫克。请不要小看这一毫克铁,它对人体的造血功能和发育有很大关系。
哈密瓜中的铁含量较之等量的鸡肉多两倍,鱼肉多三倍,牛奶多十七倍;维生素含量比西瓜多四至七倍,比苹果多六倍,比杏子多一点三倍。这些成分,皆有利于心脏、肝脏及肠道系统。
对于多数人来说,吃瓜图个味道,很少能想到营养指标。
农艺师阿不列力木·阿不力米提吃过很多不同品种的哈密瓜,但他最喜欢吃的是8501,是个新品种,在哈密已种了有十几年。椭圆形模样,瓜不大,最大也不过两点五公斤,糖度含量为十七度左右。他家里常常存放几个8501,想起来就切一牙。
他的夫人喜食红心脆。夏天时,两天就能吃掉一个三公斤的瓜。他的丈母娘在花园乡二队,不仅种棉花、葡萄、红枣等,还种了五亩地的哈密瓜,多为老式品种。每公斤瓜可以卖到三元以上,一年可收入一万五左右。
他的儿子十二岁,很挑嘴,只吃老式瓜。
每一种瓜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人吃瓜,就像男人找女人,顺着自己喜欢的味道,一路嗅过来。无论路有多远。
在市场上,我们常能看到一些小而难看的老式瓜,被拣在一边。和那些个头硕大浑圆的新品种相比,这些老式瓜像个蜷缩的老人。
我母亲喜欢吃老式瓜,常在自己家的菜园子里种香瓜。秧扯不长,瓜也小小的,比拳头大些,橙色皮子,一棵秧上只结三四个,味道奇甜,有一股很浓郁的特殊香味。切开后,像个小南瓜,但瓤不是红的,而是白的;还有一种梨瓜,皮薄,洗后直接啃着吃,不用削皮,瓜肉发脆,在嘴里一股清香。
一个人选择了一种瓜的口味后,就像选择了一种个性和命运,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瓜。瓜的世界,就像人的世界。
红心脆的模样为长椭圆形,基部稍大,皮色浅黄绿,上布青色斑点,网纹粗而稀,肉浅橙红,质细嫩,入口香脆。吃后,浑身散发着一股香味。
网纹香奇甜,瓜面上布满细密网纹,瓜肉绿白色。含糖量达百分十五,高者可达二十二,咬一嘴,就是一口糖;百仙可奇也称为老汉瓜,瓜肉绵软,口感香软,几乎不用啃,肉就掉了下来,老人吃着不费牙。
加格达皮厚味醇,吃时发出清脆的响声,满嘴咔嚓,铿锵有力。
黑眉毛为长椭圆形,姜黄皮色上布满粗糙的网状,一缕缕墨绿的长条像极了眉毛。果肉绿色,肉质软而多汁,味甜蜜(维吾尔族人以浓眉毛为美。他们将植物奥斯曼的汁液涂抹在眉毛上养眉。他们认为女孩眉心之间的距离,就是嫁出去之后离家的距离)。
新式瓜产量大,生长期短;老式瓜产量低,皮薄,不易储存。若不能及时销售出去,很容易坏。
越鲜美,腐烂得越快(葡萄和无花果等水果也是这样)。
有些老式瓜,譬如白皮脆,已经很少能在市场上看到。有的瓜农也种,不卖,自己吃。已经很少有人能认识这种瓜了。知道它滋味的人大多已经逝去,买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如果有一年,他们忘记种了,或者仅有的几颗种子叫老鼠吃掉了,这种作物就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哈密瓜的原产地就在哈密。在它的改良道路上,一些老品种逐渐被淘汰,另一些新品种又渐次出现。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每改良一种作物,就会丢失一些老品种。没有人会为这些老品种留下样品。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哈密瓜是什么味道。
这条改良路,是条不归路。
有时候,我们因为一种作物的味道发生改变而对整个世界产生怀疑。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对一些事物进行命名。随着时光推移,名字在,但内容已发生了改变;有时候,名字和内容一起消失,彷佛从来都不曾出现。
贡瓜人的后代
尼牙孜·哈斯木是贡瓜人的后代。
他的瓜园外有一圈围墙,双扇的大门虚掩着,门板上刷着天蓝的油漆。推开门后,望见一架拉着长长白线的飞机掠过瓜园上空,远处天山顶上的积雪格外清晰透明。
我们先找到了他的家,锁着门,想走,邻居说他一定在瓜园里干活,果然,在这里找到了他。这是一年中的深秋,大地即将安眠,他正忙着收拾瓜地。
他住的这个地方离哈密市中心有十七公里,叫“卡日塔里”,维吾尔语意为“榆树茂密得挡住了阳光”。可是,在他的瓜园周围,却很少能见到榆树,而多为士兵般的杨树。
他小时候,这里曾长着一片连着一片的榆树。解放后,砍倒了很多榆树,为了腾出地来种粮食。人要活命,就来抢榆树的生计。后来,村子里又种了些桑树,大伙也很高兴。桑树是最好的树,一年当中,它早早就成熟了,让人可以吃到甜甜的桑葚。在去年储存的麦子吃完,新麦还没有打下来的时候,桑葚可是救了不少人的命。
新疆有很多叫“榆树沟”的地方,大多是因为长满了百岁以上的老榆树。榆树的样子古怪朴拙,不好修饰。杨树却一副听话的模样,可以做房梁,最终,讨得了人的喜欢,人就伐榆种杨。
天池脚下有一片古榆树,黑乎乎的树干,乱蓬蓬的树枝。远望,整个天空都纠缠在榆树的枝枝蔓蔓中。榆树的杆不直,不是做家具的好材料,有些像葡萄藤。但葡萄藤上还结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榆树呢?!
一个物种就在人的取舍中发生了改变。
好在,人对哈密瓜的热情一直持续,甚至从他的祖爷爷就开始。专门为哈密王种贡瓜,让他们这户人家有了一种特别的尊严。
他戴着礼帽穿着西装,鞋上套着一双布鞋,一脸清瘦,眼窝深陷,是一副典型的维吾尔人的长相。
显然,他的眼神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瓜农。
虽然贡瓜之路早已决断,但是贡瓜栽种的技术却一直在这个家族中秘密传递着。到了他这里,依然能够栽种出比别人甜美的加格达。这足以让他略显特别。
这个七十多岁老人,在没退休之前,曾是卡日塔里村的支部书记。他能听懂汉语,自己说上几句也没问题。但他显然非常慎重,害怕自己表达不清楚,总是先叽里咕噜说一番维语,等着翻译转述给我们。
尼牙孜·哈斯木祖祖辈辈种加格达,到他,已经传了七代。
他说:“我家的秘方,从不外传,儿子可以传,别人不行。”
这块“榆树茂密”之地,曾是哈密王的狩猎场。尼牙孜·哈斯木的老祖宗吾鲁古·吾守尔最早就居住在这里。那时候,这里仅仅住了四户人家。吾鲁古·吾守尔为人聪明机灵,善于学习,种的加格达比别人甜,哈密王就叫他到王府的瓜园里专门种加格达。
王府的瓜园有一百五十亩,枣园、葡萄园有三百五十亩,全部都叫他看管,报酬是一亩地给四十五公斤麦子。
直到现在,贡瓜人家的秘密武器也不过是这几样:施苦豆子、农家肥、油渣,不加塑料薄膜,不打农药……这样种出来的瓜含糖量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种瓜的根本是种子要好,再用苦豆子做配料,浇上好水,就行了。
瓜这个东西怪得很,吃起来那么甜,却要吸苦东西身上的养分。不知道瓜是怎么把苦变成甜的。
存储哈密瓜也有技术。尼牙孜·哈斯木在一间凉房子里搭起木架子,架子上先放上麦草,再把瓜放在麦草之上,可储存半年之久。草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到底要多厚多薄,只有他才知道那个准确度!
尼牙孜·哈斯木的叔叔活到了一百零三岁。在他一百岁的时候,和他聊天时,还说起他的爷爷和哈密王一起上京贡瓜的事。爷爷是和九世哈密王沙木胡索特一起去的。开始去的时候,不仅带着加格达,还带了很多他们自己酿制的瓜干。据说,康熙皇帝每天吃完早饭后,都要吃上几牙哈密瓜才去上朝。
他的爷爷一共去了三次北京,每隔五年去一次。每次坐车要花三个月时间;如果骑马,则要两个月。
爷爷虽然去世了,但尼牙孜·哈斯木家族种哈密瓜的历史却一直没有中断。
他现有四十亩地,瓜地六亩,其余还种了棉花、玉米、葡萄、红枣、沙枣等。他有四个孩子,毕业于新疆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三个工作了,一个刚毕业。
深秋的瓜地里一片灰黄。
从一只干枯的瓜秧上,尼牙孜·哈斯木找出了几个晚熟的哈密瓜,在地埂边用小刀切开,让我们吃。
一瓣瓣冰凉的瓜牙,咬在牙根上浑身透凉。
抬头之时,再次看见了钢蓝色的天空,天空之下,是那有着银亮积雪的天山。
我们正在喝天山上流淌下来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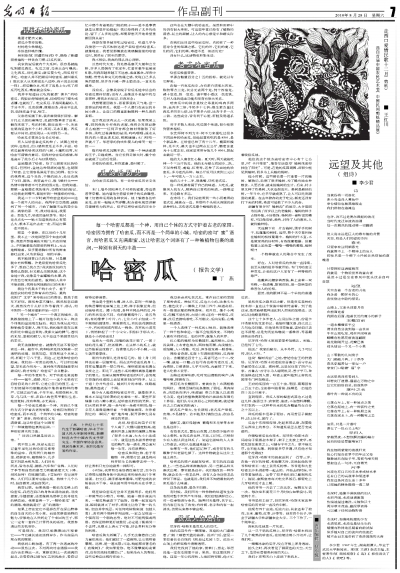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