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特别进入民国,“西方”俨然已化为一个国人心头爱恨交织的强势词语,驱之不能,学之且难。然1918年却成中国人重新审视西方尤其欧洲文明的拐点。是年年底,梁启超赴欧参加巴黎和会。沿途梁氏穿过欧洲诸国,与随行记者一道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西部战场、莱茵河右岸、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足迹遍及比、荷、瑞、意、德等国,可谓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返国后,梁迅即提笔写下《欧游心影录》这一篇反省欧战的长文。
于此文中,梁结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认定“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既然欧洲文明已遭破产,如何涅槃重生,药方何在?梁指出,其实“众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良剂却在“灯火阑珊处”,即中国的“孔老墨三位大圣”。于是他文末呼吁:“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梁氏此番言论,折射出其积极反思现代性之文化自觉。正基于这种亲身观感,梁主张须重新审视自晚清以来不断推崇的所谓“西方”。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正在国内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评判的态度”也应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其二,反对“科学万能”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亦即“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其三,切勿一味追慕西方,主动提高自身文化力,“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梁对时局变换、潮流更迭之敏感确异于常人,故梁漱溟赞叹“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其“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
··Ⅰ··
其实,国人对于欧洲19世纪末以来思潮递嬗的考察并由此引发就现代性的反思,并非始于梁任公欧洲之行。据郑师渠先生的研究,最初反思现代性的文章,当是鲁迅作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该文已颇为犀利地意识到19世纪的欧洲文化虽促使科学发达,物质丰富,但却失之于偏。其缘由即在于迷信“物质万能”,却贬抑了精神与情志。德国哲学家尼采等学者开始揭示物质文明的“伪与偏”,这预示着20世纪的文化已异于上世纪。鲁迅自信“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20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不过此文刊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河南》杂志,故在国内影响不著。真正于中国本土最早推介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刊物,非《东方杂志》莫属。1913年2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刊登了章锡琛译自日本《万朝报》的一篇题为《新唯心论》的文章。是文指出,欧洲自法国大革命后,思潮变动的趋向是科学藉煤铁工业而大昌,哲学上与之呼应,唯物论取代了唯心论。因之“科学的人生观即唯物的人生观”盛行,“一切归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终为物质”。看似物质极大丰富,但物欲横流、信仰尽失,“我欲与过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现实生活,又足以使我绝望”,难怪近来欧洲自杀者与日俱增,且堕落者亦多。“呜呼,末世纪之悲惨,固若是哉!”也正因对此现象痛加反思,欧洲的生命哲学兴起,“欧坎、俾尔先生,皆创新唯心论”与唯物论相对峙,此乃“新时代之精神也”。要之,这篇译文不仅介绍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讯息,还指出了柏格森、倭铿是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如今细数刊布于欧战前或期间的文章,大多转述日本思想界的观点,故问题思考难得深入。所以真正意义上将欧战反省现代性思潮带回国内且引发广泛关注的,仍是梁启超、张君劢诸辈。他们主动反省的态度,首先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观察,从而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结果。胡适曾这样评价《欧游心影录》,称它如同放了一把“野火”,使得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继之而起,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是彰显出东方文化的魅力,这恰恰是与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相映成趣。其次该群体也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倡导西学,批判中学,本无可厚非,然倘一味采用简单化的视角与态度,不免失之于偏。此问题在欧战后反省现代性的映照下便愈加明显。陈嘉异便讲到“(新文化人)一谈及东方文化,几无不举首蹙额直视为粪蛆螂蜣之不若”,“以国人而自毁其本族之文化若是,此虽受外来学说之影响,而亦国人对于己族文化之真正价值初无深邃之研究与明确之观念使然”。况且,梁启超等人高扬传统文化大旗的深层次目的,恐怕还是以期借复兴民族文化来实现中华复兴。梁漱溟在谈到自己之所以决心要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的动因时,坦言现在对于中西文化问题“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这可视为中华民族觉醒的一种体现。
一言以蔽之,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群体的文化立场可用中西调和、复兴中华文化来概括。诸位学者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本国固有文化,在得其精华的基础上再与西方文化碰撞融汇,以期创造出民族新文化,为世界文化尽一分绵力。不过他们未能深窥西方文化之精髓,简单地把中国文明归结为儒学传统,导致片面强调了文化的承继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故他们的调和中西创造新文化的主张,时代性不足乃其硬伤,终陷入恋古情结之中。
与此同时,彼时主政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也注意到一战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然以其为首的老派学人群体素来钟情传统,既不希望新文化星火燎原,又认定单纯追求物质文明是一战爆发的根源,“故欧洲学人,咸以为欧洲于物质发展,已达极点之后,遭此番摧丧,使非于道德方面,另求立国之道,恐不足以收拾涣散,扶持倾危,其道云何?舍我孔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谁属乎?”进而最终提出“由中学以融西学,仍归于人道而已”的主张。可见其学术立场竟因比照欧战惨境而更趋保守,故与时代潮流颇有些相悖。不过此等态度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以往研究视野往往囿于“求新”而“厌旧”,其实该群体值得关注。
··Ⅱ··
然此际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认为须反思现代性。比如系统接受英美教育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便执着于对现代性之追求,认为欧战并非引来世界思潮的巨大变更。1921年,胡适在其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单独拿出一节集中谈论了柏格森的哲学。胡适认为,科学家们的基本信条是承认人的智慧能力,但他们难免有时“于信仰理智太过了,容易偏向极端的理智主义,而忽略那同样重要的意志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颂赞正在高唱的时候,便有反理智主义的喊声起来了”。故“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种很高的反理智主义的抗议”。表面观之,胡适似乎客观地肯定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互有长短,但实际上他是强调后者充其量只是起一时补偏救弊的作用,势必不可能成为重要的时代潮流。所以,他明确地强调了三点: 第一,柏格森的哲学无大价值。生命哲学的核心理论,即所谓的“生命冲动”,无非是在倡导一种“盲目的冲动”而已,“柏格森批评那机械的演化论,很有精到的地步。但是他自己的积极的贡献,却还是一种盲目的冲动”。第二,柏格森强调“直觉”,但这并无新意,因为包括杜威在内,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早已承认‘直觉’在思考上的重要位置了”。所以,“就可以明白柏格森的反理智主义近于‘无的放矢’了”。第三,胡适始终固执地认定19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现代思潮没有发生重要变动。所以他在第六节开头便说: “这一章名为‘晚近的两个支流’。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但我个人观察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思潮,自不能不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派思想为哲学界的一个新纪元。”显而易见,对于19 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发生的重要变动,胡可谓熟视无睹。
甚至胡、丁诸位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其实不过是“谣言”而已。“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然而“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反观梁氏提倡的东方文明,“其实呢,这是活死人的文明,这是懒鬼的文明”,“这种文明其实只是一种下贱的唯物的文明”。可知虽同倡扬新文化,但梁、胡等人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已呈大相异趣、针锋相对之态势。胡适这种近乎偏见般的拒绝反省现代性思潮,实际上弱化了个人的思想张力,其在新文化运动后于思想界影响力日渐消退,恐与此颇有关联。
··Ⅲ··
与此同时,彼时思想界在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一种新的重要动向正潜滋暗长,呼之欲出。这便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起初亦深刻反思现代性。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的开篇大作《敬告青年》中,正是借重了尼采和柏格森诸人的思想,以激励青年。例如,在该文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标题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标题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标题下,他又写道:“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实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1916年11月,他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中更明确指出,柏格森哲学代表了欧洲最新的思潮:“法兰西之数学者柏格森氏……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 ,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同年夏天,李大钊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8月他发表《介绍哲人尼采》,更进一步强调反省现代性思潮对于中国青年的意义,他指出以尼采、倭铿为代表的哲人“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以立主我思想之基础,极力攻击凡俗主义、物质主义”,“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囚锢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于是陈、李诸人积极倡导文化调和与融汇。可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他们便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随着认识之深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们终皈依马克思主义。从反思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内在演进脉络,确是以往甚少措意之处。
··Ⅳ··
以往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往往容易将其简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概括固然不错,但难以揭示当时思想界之丰富性。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我们不妨喻之为“倒放电影”。“倒放电影”手法之优点,在于结局早已知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彼时事件亲历者未能措意之关键处。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重要的发展,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但此手法亦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这样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熹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况且“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研究者常为避免枝蔓,勇于剔除那些与主题看似关系不大的史料,结果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但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毕竟如此裁剪势必遮蔽掉了历史本该有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偶然性。
或许有时候,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明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越看上去有些粗枝大叶甚至不修边幅,其实越能折射出“整体”的时代意谓。作为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皆先期经历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洗礼,这绝非偶然。正是迈过了1918年中国思想界的三岔口,他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到底需要何种主义。事实表明,后者正构成了他们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所谓注重观察思想创造过程中的多重价值,就是注目其思想在发端时,或还未充分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注目其要素中还未充分显示的丰富的可能性”。正是借助欧战前后西方物质文明遭遇困厄的契机,通过镜鉴国外哲人对现代性思潮之反省,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空前的裂变:从新文化运动一枝独秀,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及东方文化派三足鼎立的格局,学术主张上也渐趋多元并进的态势。这是历史演进的自身逻辑,亦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新文化运动日后的走向,深深受到这一裂变的影响。
(作者简介: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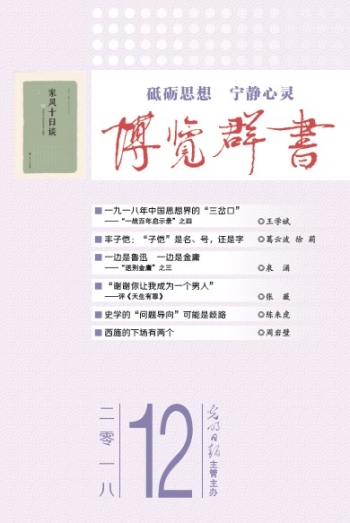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