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孙玉文老师门下读博士。2006年底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现在回顾起来,三年多的时间,孙老师不仅传我绝活,而且注重性格的磨炼和长远学术规划的绸缪,是学术道路的领路人。
当时汉语上古音领域正在进行十分激烈的争论,涉及复声母、汉藏比较、上古音研究的材料、方法等重大问题。照我的个性,遇到矛盾纷争宁愿绕道走;但是孙老师鼓励我要敢于迎接挑战,积极参与学术论争,在论辩中学习和锻炼,茁壮成长,并为我选定了博士论文题目。
这么选题还有一个深意,就是引导我处理好汉语内证材料和外部证据之间的关系。从长远来看,要想使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必须熟练掌握汉语内证材料,学习分析处理汉语内证材料的方法,这一步是无论如何也省不掉的。当时我在这方面的训练还比较缺乏,孙老师要求我博士论文要立足汉语内证材料,打好基础。这个安排为我后来能够胜任高校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对音研究,因为对音研究离
不开传统研究的底子,传统研究的盲点有时靠对音材料才能发现,二者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孙老师当年的安排至今令我受益匪浅。
如何看待汉藏比较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作用是我写博士论文时遇到的难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近些年来,孙老师带领大家在音变构词领域深耕细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使我认识到如果从词义引申规律的角度检验,目前各家找出的汉藏同源词,争议恐怕就更大了。历史上藏语和汉语接触密切,留下的古文献相对较多,结合语言实际从多角度把这些材料充分利用起来是更加务实的做法,不要局限于同源比较,这样或许能够发掘新的研究材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通过具体指导写论文,孙老师传授我三门绝活,即历史观与系统观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语文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我研究主题属于上古音,孙老师却让我首先从中古材料入手,全面调查《经典释文》中来母字的注音,后来逐步扩大到《史记》《汉书》音注、《文选》音注、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其他音义材料,又扩大到《切韵》残本、《广韵》等韵书、字书材料以及从两晋到隋唐的梵汉对音材料等,这样中古以前关于来母的书面注音材料几乎收集完备了。中古音是上古音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古音的相关材料较为丰富,而直接反映上古语音信息的材料相对而言较为零散,只有以中古的演变结果为背景,才能得出有关上古音的较为稳妥的结论。这种研究思路体现了鲜明的历史观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精髓,即便是在当今也是非常超前的。
我研究的是上古声母问题,孙老师引导我要有系统观,从语言的系统性出发评价现有学说。高本汉是复声母学说的奠基人,也是现代音韵学的开创者,他的《汉文典》为上古时期出现的字全面标注了上古音。为了弄清楚他的学说,我整理出了《汉文典》的音节表。孙老师特意在课堂上从音位配合角度分析高氏的拟音,指出如果构拟复声母,那么就会在大多数韵部与相关单声母音节形成互补分布。这使得我对相关争论豁然开朗,现代音韵学建立在音系学的基础上,划分音位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处于互补关系的音素一般情况下要归为同一个音位,复声母是构拟出的音位,如果构拟的结果造成大量互补关系的出现,那么显然是有违音系学的基本原则的。这使得高本汉学说深层矛盾重重。
以前的复声母研究,往往着眼于《说文》所谓“特殊谐声”以及中古时期的某些的音注,认为这些现象是上古有复声母的主要证据。可是这些现象到底占多大比例,以前还没人能说清。孙老师嘱咐我要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拿出具体的数据。经过统计发现《经典释文》中来母字只注来母音的占97.5%,《说文》中来母声首只谐来母字亦只占77%。以往当作复声母主要证据的谐声、异读现象只能算作例外,不能根据例外
现象去谈普遍规律。当然例外现象要进一步探讨其成因,谐声的层级性就是一个新的发现。
语音研究要和语义相结合是孙老师格外强调的。音义结合体的确定是语言研究最基础的步骤,以往的相关研究,对这一点往往有所忽视。孙老师要求,对于书面注音材料,要尽量回到最初的语境涵咏文意,从中提炼与语音相搭配的词汇意义,这离不开传统语文学的功底。把握住音义关系,许多先前比较模糊的认识可得以澄清。比如,从音义结合的角度看,大多数词的声母,只能证明上古有一个读法,以前说的异读,多是记录不同的词。又如高本汉通过文字谐声讨论语音规律,对字音和词音的区别重视不够。总之,从音义结合的角度来看,复声母学说确实存在诸多缺陷。
在孙玉文老师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最大的收获不在于弄清了上古复声母的有无,而在于初步掌握了研究上古音的方法,这使我对上古音的研究不再畏惧,培养了信心、磨炼了性格。近些年来,我主动参与学术论争,在论争中有所坚守,坚持走自己的路。如果对学术发展有些许贡献的话,那全归功于孙老师的悉心培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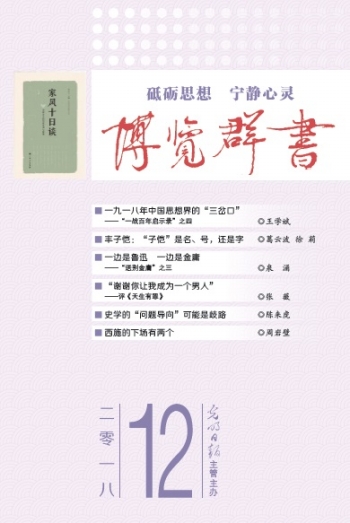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