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英日同盟的阴影”是解释在“英日同盟”(1902-1923年)存续的21年期间,中国从清末到民初,经历了清帝国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该同盟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内政、外交造成什么影响,对东亚世界秩序造成何种影响。
/壹/
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可以认为,缔结于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体系解体之后的一个过渡时代的产物。甲午战争之前的东亚体系是一个宗藩体系,这个东亚体系基本上被甲午战争给摧毁了。大清朝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而日本则是耀武扬威。日本就想凭借战争的余威,取代清帝国而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但是,日本的霸主地位要能如愿以偿,单靠武力征服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与强国进行外交结盟。在20世纪初,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日本20世纪对外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结盟。此次英日同盟,既有军事国防上的战略性意义,也有文化上的象征性意义。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脱亚入欧”,要效仿欧洲强国建立民族国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规则和西方列强交往。日本虽然在思想上抛弃了中国的那一套过时的华夷秩序观念,却无法改变其在东亚的地理位置。换言之,“脱亚入欧”论让日本人的“心思”朝向了欧洲,但身子仍然留在亚洲。经历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后,日本在1902年想成为东亚霸主的野心已经很明确了。1903年,俄国人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由此大大增强了俄国在远东的军事作战能力。日本当时的首要目标是控制朝鲜,为了防止俄国的干涉,就需要与俄国人决一雌雄。打仗之前,日本认为有必要获得英国的外交支持,于是就有了英日同盟。
英国为什么能跟日本结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俄国,他们可以联手抵制俄国。从日本的角度看,如果获得英国的支持,在东北亚地区形成攻守同盟,就可以确保日俄战争的胜利。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初步实现了称霸东亚的野心。在其后的七年间(1905-1912),中国人还没有感觉到英日同盟对中国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故而清政府官绅阶层和一般读书人还是把日本当作学习的榜样。在政府层面,清政府派出留学生,学习日本先进的军事、政治、法律和教育经验;在民间层面,像康有为这样的保皇党、立宪派,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都跟日本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一时期的英日同盟主要是用来对抗俄国,同时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对朝鲜的占领,还没有对中国实施侵略行动。因此,中国的民族精英和清政府外交决策层还没有感觉到日本的直接威胁。
/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大隈内阁怕错失良机,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和外务大臣加藤高明都是野心勃勃的侵华分子,他们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大总统很快就能把中国统一起来。如果日本再和过去那样依靠支持中国的反对派来建立侵华政权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孙中山这股势力已经被袁世凯清理得差不多了),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武力强占中国的一些关键区域。于是,日本就改变了之前扶植中国的反对党——革命党的手段,变为通过直接的外交和军事手段来实现其侵华野心。这时,日本就千方百计地利用“英日同盟”的关系,以对德作战为借口,伺机占领德军驻守的中国北部战略要冲——青岛。
根据英日同盟的规定,一旦英国与另外一个国家交战,日本作为同盟国就有义务出兵,日本可以借此理由夺取青岛。由于当时的青岛被德国人控制,英国人其实并不希望日本出兵青岛,因为这样会直接威胁到英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利益。英国那时陷入欧战,它当然不希望东亚也发生战争,如果那样的话,就会让英国在欧洲和东亚两个战场同时受累。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深谋远虑,当一战爆发不久,他就建议,中国应该在日本动手之前先把青岛收回,那样日本就没有借口攻占青岛,但是袁世凯过于谨慎,他觉得在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有利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青岛问题,中国将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更何况,日本海军已经提前封锁了青岛周围的海域,中国军队无从下手,即使是英国远东海军部队也没办法制止日方的行动。事实证明,日本正是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把英日同盟作为其出兵青岛的借口,在1914年11月完全占领了青岛。
紧接着,日本在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试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属国。面对日本的淫威,袁世凯无可奈何。此时中国没有力量可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扩张。但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暗中帮助,中国政府绝处逢生,最终迫使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上做出重大让步,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损失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为了挽回日本的国际颜面,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在二十一条交涉上做出让步,1915年5月25日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相比,在内容上做了很多删减。此次中日交涉,也是一战时期,弱国通过公众舆论在外交上战胜强国的经典案例。这是袁世凯在任期间发生的事情,当他1916年6月6日去世后,问题就来了。从1882年跟随淮军统领吴长庆出兵朝鲜以来,袁世凯一直是坚定的“反日派”。1912年,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之后,奉行的是“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远交”是联合“欧美”,“近攻”就是抵制日本。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则开始奉行亲日政策,其标志就是1918年的中日军事结盟。
在中日军事结盟之前,日本在1917年与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都签署了秘密协定,所有这些秘密协定都有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求这些国家支持日本对青岛、胶济铁路的控制。在所有强国都跟日本结盟的情况下,段祺瑞政府非常现实,他认为既然那样,那么中国也要跟日本结盟。其中的一个现实考量是,日本人给段祺瑞政府提供了一些诱惑性条件,承诺给大量贷款,段祺瑞想用这笔借款达成他的政治诉求,武力统一中国。从中国的民间舆情看,此时段祺瑞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是违背民意的,也是不明智的。在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中国社会已经表现出很强烈的反日倾向,但是段祺瑞政府丝毫不顾及这些,一味认为只要有了经费,有了武器,就可以掌握一切。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结盟,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日本的压力,日本政府是想通过“中日结盟”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的“合法控制”。
/叁/
1918年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军事结盟时,美国已经参加一战一年有余。美国的参战,改变了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略军事平衡,协约国的胜利已经在望。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的口号是“用战争结束一切战争”,同时,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和平演说”,主张公开外交,这种和平之声很快发展成一股席卷全世界的和平潮流。在世界愿望和平,中国民间反日的新时势下,段祺瑞政府却看不清世界大势所趋,竟然与日本进行军事结盟,显然是把自己置于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而不自知。当时的国内知识精英,还有美国的在华企业、传教士、大学等,在宣传威尔逊主义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威尔逊主义就是要反对政府秘密外交,而1918年中日军事结盟就是秘密外交,是在中国公众舆论的反对之下而强行签订的。
1918年5月,中日两国签署陆军、海军军事协定时,中国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并回国串联,联合国内学生,共同抗议,但是反对无效。出人意料的是,1918年8月日本发生了米骚动,米骚动就是由于日本政府将大量资金支援海外,导致国内民生凋敝,引发社会暴动。其后,日本文官出身的原敬上台,一上台之后他就不再愿意履行中日同盟,他主张跟美国搞亲善。这样一来,段祺瑞政府就很尴尬。日本原敬政府不愿意履行中日同盟的规定,不愿意给皖系军阀提供军事贷款;同时美国人又主张中国要南北议和,停止内战。为了响应威尔逊主义,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张謇领导的江苏省教育总会等机构团体,发表和平主张,组织和平运动,批评段祺瑞政府的穷兵黩武政策。当1918年的中日军事结盟条约公开后,皖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亲日立场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在一战造成的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亲日派顿时陷入被动境地。这是因为在1918-1919年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中国人开始相信美国,但不相信日本,认为只要跟日本沾边的就是卖国的,只要是亲日的就是卖国的。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跟日本结盟,段祺瑞主导的北京政府就变成了一个卖国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国了。谁越是反日,或者说谁越是表现得很反日,谁就越能掌握舆论的话语权。在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等人都表现的很反日,要打倒亲日派,于是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
上海总商会因为发出一份要跟日本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电报(史称“佳电风波”),引发全国的反对,被认为是卖国行为。这样一个舆论转向,跟一战后卡尔·克劳(Carl Crow)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在华分会的幕后推动有关,也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梁启超的研究系发起的反日宣传有密切关系。
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5月4日的六个月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来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让中国人如此崇拜的。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由于中国人太乐观了,天真地认为威尔逊主义作为代表人类正义的“公理”,一定能够战胜“强权”。出人意料的是,1919年4月底,威尔逊总统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代表团妥协,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消息传来,中国人失望至极。北大教授陈独秀气愤地说,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到头来都是“空想”。中国人对威尔逊总统的幻想破灭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相信俄国列宁主义,决定走俄国的革命道路。
虽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威尔逊很失望,但是威尔逊主义包含的“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口号,却是五四时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勃兴的精神动力所在。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就以公开外交为理由,在五四时期积极鼓吹国民外交,动员国民起来上街游行、集会、发表公电,通过此种方式来展示“民意”,干预政府外交决策。一般而言,“外交”代表着“国家利益”,外交工作高度的专业性、机密性决定了外交事务只能由职业“外交家”来去执行,然而在五四时期,“国民”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也要参与“外交”。
然而,此种“国民外交”往往是与国内的派系政治联系在一起。“国民外交”是通过“公众舆论”和“集会游行”的方式而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结果会使外交官为了其个人“政治利益”的需要而被迫牺牲掉“国家利益”。对此问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有切身的感触,他说,“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或是日本,或是俄国,或是英国,来巩固支撑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趋向。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某个外国的外交政策的工具。”所以,顾维钧是不赞同“国民外交”的,他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国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曾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肆/
如今回顾“一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我们可以发现“英日同盟”因为“一战”的爆发而沦为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在和平年代,英国可以通过“英日同盟”来制约日本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扩张行动。在一战期间, 英国不仅完全陷入欧洲战场而无法自拔,还需要日本的军事援助。故而,日本政府能够趁机利用“英日同盟”来胁迫英国,以满足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此外,“英日同盟”还大大限制了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空间,面对日本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除了美国威尔逊政府给予中国有限的道义声援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帮助中国。因此,英日同盟的存在让一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处于恐惧的阴霾之下。
正是这样的考虑,段祺瑞政府才放弃了袁世凯时代的“远交近攻策略”,终于在1918年春与日本政府实现了军事结盟。但是,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为之一变,美国威尔逊政府积极主导战后世界秩序,筹划建立国际联盟。在此背景下,皖系军阀主导的北京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悄悄实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尽管在时人的印象中,北京政府是“亲日”的,但是北京政府无论是从其自身的统治利益需要出发,还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得不“见风使舵”,在巴黎和会外交上“联美制日”。简言之,从1918年春的“中日结盟”到1919年春的“联美制日”,北京政府的外交结盟也一直在随着国际时势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史、民国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UCSD)访问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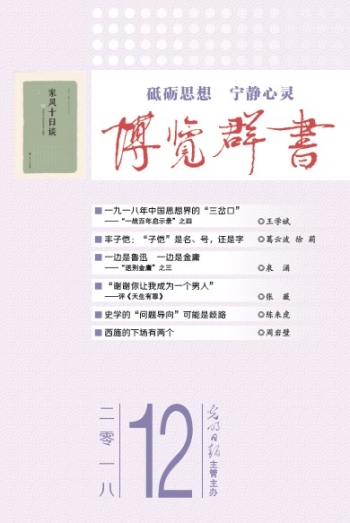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