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台湾青春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登陆内地,开启大陆青春电影的新模式,到2013年赵薇执导《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简称《致青春》),吹起一股青春电影的旋风,之后几年,青春电影每年都会创造不同的票房神话,形成一股青春电影的风潮。由此,关于青春电影的批评文章数量也随之增加,但是票房的火爆和批评文章的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相应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引发广大普通大众的共鸣,才能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而不是成为庸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附庸,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文艺。从这些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标准来看,当前青春电影确实还存在“小”的特点,这也必然导致青春电影批评的“小”。
青春电影的“小”首先来源于其空间的“小”。一提起青春电影,人们头脑会立即跳出“小清新”这个词,其标志性符号必然是都市、校园、教室等。青春电影表现的主人公也大都是都市青少年的生活与经历,甚至说是其校园生活经历,他们好像生活在伊甸园中,不食人间烟火,与现实社会没有关联,连中国校园中青少年必须要面对的考试都很少提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似乎只有爱情的关系才是真实的。这种舞池叙事的模式很容易产生人物之间简单的多角关系,让青春电影走向扁平化。都市青少年活动在狭小的社会空间中,农村青少年却在青春电影中几乎不见踪影。中国有近一半的青少年生活在农村地区,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青春成长和心理焦虑是这个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但是在青春电影中却几乎绝迹。《乘风破浪》打破都市青少年的范围限制,表现了小镇青年的成长,同时也突破了多数青春电影中的校园叙事,走向了无业青年的社会叙事,这是一个进步,但青春电影狭窄的人物设定、人物活动空间的狭小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次青春电影还存在时间上的“小”。多数青春电影反映的时间一般都限于青春期前后几年进行集中时间叙事,把时间进行狭窄的限定,又以青少年独特的生活感受作为表现对象,很难引起不同年龄观众的共鸣。不过近几年青春电影中又掀起一股重返现象的热潮,比如《二十八岁未成年》《重返20岁》《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等。这些电影通过成年主人公的重返视角来观照当年的青春,这与《致青春》所引发的系列青春电影的怀旧风不谋而合,反映了青春只是用来回忆与怀念的事实,表现的其实是一种成人视角,这是东亚文化圈崇老文化的遗迹。即使电影通过重返与怀旧的模式拓展了一定的时间,但这种狭窄的时间叙事仍然无法产生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再次是青春电影主要观众的“小”。据统计,中国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2.4岁,也就是说,目前电影院里的主要观众是90后的年轻人。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观众结构严重失衡,好莱坞进口的电影,中国自己拍摄的电影,都要依据这个年轻的观众群体来设定前提,青春电影更是由此形成票房神话。电影艺术不应该限定观众,一部优秀的电影应该具有广泛的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而不是只拍给某个特定年龄段的观众并只与这个年龄段的观众产生共鸣。比如日本的动画片是给成年人观看的而不是只针对孩子。其实,在中国,年龄大的电影观众并非没有观影的需求,而是这种需求无法在电影院中得到满足。中国观众的市场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是青春电影却主动限定了这个观众空间。
青春电影本身的“小”也让青春电影批评陷入了“小”的怪圈。这一点某些敏锐的电影批评家已经意识到了,戴锦华在《电影批评:理论的演武场》中说,电影批评很多都是印象式、感发式和经验式的书写。这种片段式的批评本身丧失了电影批评应该具备的独立性,丧失了对青春电影创作的前瞻性指导作用,也呈现出“小”的特点。
第一是其价值观的“小”。目前的青春电影批评无法从价值观的角度对青春电影的创作提出前瞻性的指导。例如青春电影中由于其人物关系的简单化存在父辈缺席的状态,父辈与老师即使在青春电影中出现,也是作为青少年的对立面或者反抗的对象而存在的。他们总是呈现单薄的刻板化形象,父母总是唠唠叨叨不关心子女成长,老师总是墨守成规一味关注考试成绩,比如《李雷和韩梅梅》中的父母与英语老师的形象就是这种典型的父辈形象。这些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价值观,容易引导青少年仇视长辈,反叛社会。而青春电影对青少年荷尔蒙的过度表现更是多见,青春电影大多表现青少年刚刚萌发的强烈性意识,通过青少年的视角对成熟女生的身体性吸引加以呈现,比如《少年班》中对江依琳美丽的身体和诱人的胸脯展现远远超过对其脸部的表现,更超过对其精神世界的描绘。江依琳诱人的身体成为少年班几乎所有未成年男生的追求对象,并引诱他们做出各种啼笑皆非的怪诞行为,最后甚至造成了被开除的结果。这种身体性欲望的过度表现很容易给青少年形成价值观误导。这些价值观误区有一些批评文章也注意到并提出来,却并没有深入挖掘其存在的原因,更没有对电影剧本的创作提出好的建议。这方面,有些学者的批评精神值得学习,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放映后,周黎明即对其提出强烈的批评,尽管遭到某些郭敬明粉丝的攻击,但是他在《从评论〈小时代〉看中国影评的现状》中仍然认为:“我批〈小时代〉不是因为它描写了年轻人,也不是因为它描写了大都市里的年轻人,甚至也不是因为它描写了大都市里非常富有的年轻人,我反对的是影片做此描写时所流露的潜台词和价值观。”这种对价值观的固守和批评的锐气与勇气应该是每一个青春电影批评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第二是格局的“小”。电影批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性,如果不能达到独立性,电影批评就容易成为商业的附庸。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带着商业营销的目的,在消费时代中,电影更成为了一种艺术商品,带来的结果就是许多影评人也扮演了电影商业中的重要角色。正如戴锦华在“电影批评,理论的演武场”活动发言中说的,专业的影评人和电影理论工作者扮演着消费指南者的角色,这与电影批评本来应有的独立性背道而驰。青春电影大多是从网络著名的IP小说改编而来,天然带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为了达到商业宣传目的,电影变相“雇佣”影评人为其大力吹捧的现象也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一些学院派的影评者一本正经地写文章为青春电影的推广提供营销策略。目前,一些青春电影批评者也看到了这种现象,并对此提出了批评。近年来青春电影大多数是叫座不叫好的状态,票房大卖,但是在专业影评人这里的评价并不高。这表现了青春电影批评的一个进步。正如李建强《电影批评像批评了》中所欣慰的,电影批评正在逐渐走向深入,敢于对某些消费丑相进行批评,“我们期待多年的中国电影批评和反批评的两性互动,正在孕育和躁动之中。”
第三是批评深度的“小”。一方面青春电影批评很多停留在现象总结水平,对青春电影中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符号进行了总结性陈述,却无法透过现象看到青春电影发展中的本质问题。另一方面有的批评文章能够发现问题,却在分析问题上无法找到文化根源性。例如分析大陆青春电影的怀旧症候的文章,很敏锐地指出了《致青春》及之后青春电影中的怀旧症候,也对这种症候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索,从青春电影的主要观众“泛80后”在全球下语境下远离家园漂泊的焦虑感找到这种怀旧元素产生的根源,并在文章中对这种怀旧青春电影的发展前景感到担忧。但是,这种都市漂泊族的无根现象并不是“泛80后”的特质,其起源于农耕文明的安土重迁文化心理,是东亚文化圈共有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不乏文人骚客抒发乡愁的羁旅之作。因此,这种怀旧的文化之根存在于整个东亚文化的谱系中。如此,将怀旧症候根源定位于“泛80后”的社会心理特点就并不能切到问题的本质。
第四是批评媒介的“小”。互联网时代,网络影像空间成为电影传播的一个重要空间,网络电影批评也成为电影批评的重要阵地。青春电影的主要观众群体是伴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长大的一代,很多迷影者通过豆瓣等网络平台汇集并发生观点交流与碰撞。青春电影的网络评论的口碑直接影响大部分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及评价。而在电影批评领域更为专业的精英学者却大多更为信赖与习惯纸质媒体,并不屑于在网络空间中传播自己的观点。纸质媒体的更新速度过慢以及普及性低造成了精英学者与广大的迷影观众的巨大媒介鸿沟。两种话语各说各话,互不交流,甚至互相对立。由此,精英学者的青春电影批评的声音无法到达观众,更无法产生传播效果。对此,部分敏锐的学者已经发现了青春电影网络评论对观众群体的重要影响,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比如陈旭光在《互联网时代的艺术批评问题断想》中就提出了网络批评对电影生态的影响,并呼吁建立一种综合多元开放的电影评价标准体系。另外也有学者进行了网络时代电影批评的梳理与解读。青春电影批评的研究还有待于在此基础上推进一步,构建精英学者与普通电影观众的网络交流平台,推进青春电影的批评。
总体而言,青春电影本身存在的“小”与青春电影批评之间的“小”共同构成了青春电影发展的生态环境。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达,让青春电影得到青少年乃至成年人的情感认同,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在这方面,青春电影创作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青春电影批评中的文章多精品少的现象也亟待改变,虽然如前所述,青春电影批评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批评勇气和前瞻意识的批评者,但是目前整体批评局势还不容乐观,期待青春电影批评出现一大批独立、锐利和富有勇气的批评声音,能克服阻力,直面电影创作中的矛盾,才能改变目前的批评“小”格局,实现“大”批评,引领青春电影更好的价值取向,与青春电影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促进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良好生态环境建设。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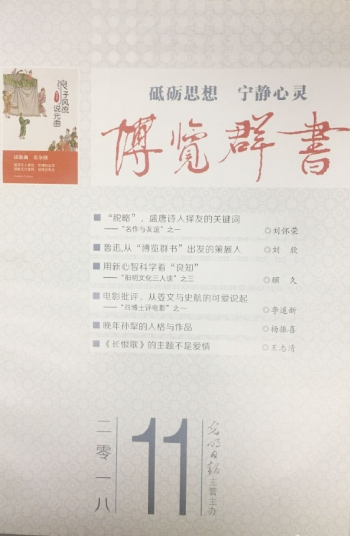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