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教化是儒家最突出的主流文化思想,教化不仅关乎个人修身,人格培养,更关乎维护社会秩序,国家治理,儒家的教化思想始终体现出道德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孔子指出从政“四恶之首”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他倡导通过礼乐教化使民知“仁”循“礼”,遵循做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的道德规范以达到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可见儒家仁政的治国理念是以教化为前提和基础的。并且孟子坚信人具有先验的道德本性——仁、义、礼、智之善端,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教化即是借助人本性中的善端,扩而充之,达至道德的理性高度。宋明理学上承孔孟之道,在新的历史时期拓展了儒家的教化思想,从本体论高度论证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同在于人性之中,将人性教化的内在依据、可能性,人性教化变换气质的必要性、现实性,作了辩证的统一。宋明理学所倡导的为学教化,即是改变气质之性,恢复天地之性,坚守住与生俱来的道德本性——仁义礼智信。
王阳明继承了孔孟之道,也承接了宋明理学的教化思想,但他开辟了一条心学的路径,成为理学中重要的另一学派。与程朱理学将伦理道德视为外在“天理”不同,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且“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立足于“觉民行道”的政治理路下,其教化思想展现出万物一体的人性教化光辉。王阳明的教化思想与教化实践,不仅是他一生教育的使命,也是他政治治理的重要内容,他深知社会风气的好坏,直接关乎社会治乱,而醇化民风的关键在于教化。王阳明的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乡风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觉民行道”的政治理路及教化思想
王阳明生活于明代中后期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正德三年王阳明为营救弹劾宦官刘瑾的戴铣、薄彦,向皇帝上书《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得罪刘瑾,被处以“去衣廷杖” 残害肉体且羞辱人格尊严的刑罚,并被贬谪贵州龙场。阳明历经百死千难,终于在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之说,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治国路线,开辟了一条启迪大众之本然良知的“觉民行道”下行治国路径。
王阳明的教化思想与其“觉民行道”的政治理路密不可分。他将自己的教化宗旨概括为“致良知”,声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阳明认为制约人伦道德的并非是外在于人心的“天理”,而是人人本有的良知,“良知即天理”。他所秉持的教化思想,体现出与朱子“得君行道”思想不同的向度。余英时认为,王阳明将“天理”导入“良知学”话语中,将“天理”与“良知”视为一体,不仅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还有实现良知学与民间思想贯通的用意。居于“觉民行道”的良知教,体现出王阳明教化思想的大众性、平等性、实践性特点,对于儒家精神在民间的传播、落实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乡村公序良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依据“心即理”的思想,肯定“理”(良知)存在于人人都有的本心本性之中,阳明说:“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他肯定无论贤愚都有良知,将教化的目光投向大众,他希望通过教化使大众明觉本然良知,提升生命境界,表现出他以唤醒民众良知的方式,来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个个心中有仲尼”,“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体现出王阳明在良知或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教化思想。居于这种平等思想,他甚至要求良知学说的讲学者将自己置于与愚夫愚妇同样平等的位置,他对学生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他认为这才是教授良知教应有的态度。王阳明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通过“致良知”教学活动进行了积极的实践。龙场悟道之后,他的教学活动由士人集团向下扩展到民间市井、村落、田野,讲学对象也不分男女老幼,农、工、商、贾。只要有机会和可能,王阳明就讲学施教,尽可能地整顿制度秩序,淳化礼俗风规。
阳明的“致良知”教化思想,体现出他对于世道人心塌陷沉溺的忧虑和悲悯,他以拯救人心的方式来治理社会。阳明曰:“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可见,阳明的良知学说是出于“民之陷溺,则为戚然痛心”的济世情怀,是要通过“致良知”将人们从沉伦中唤醒,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良知教的出发点是肯定良知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因受到狭隘贪欲的干扰,被私心杂念遮蔽,道德缺失,沉沦退堕,背离良知。因此,王阳明要通过“致良知”治疗各种人的“气质之性”使他们回归本然的“天地之性”(良知)。
阳明的“致良知”教化思想,具有世间关怀及修己治平的实践性特征。“良知”不仅仅是个人成圣的基石,也是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前提,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阳明的良知教,不是知识学意义上的说教,而具有修己治平的实践功夫,君子惟务致其良知(修己),必须怀有“一体之仁”的济世情怀,将生民之困苦视为自己的困苦,才称得上有“是非之心”(良知)。若世之君子都致力于良知之修为,具有是非之心(良知),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哪有不治之理!阳明的良知教既着眼于个体之修心,也着眼于整体社会的治理。
王阳明以教化为主导的乡村治理
对于乡村治理,王阳明继承了孔孟施仁政、重教化的传统,倾注了他良知学体系中的“亲民”思想。阳明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 王阳明将《孟子》所言“亲亲仁民”理解为“亲之即仁之也”,亲民即是以仁心善待人民。“亲民”是要使民安富足,安民的前提是“修己”,“修己”便是“明德”。阳明引用《尧典》和《论语》的言说,将“明明德”与“亲民”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只有“明明德”才能做到“亲民”,必有“亲民”的行为才能视为“明明德”。“亲民”更兼有教化与养育之含义。在“安百姓”的治理思想中,孔子提出的“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就是“亲民”的具体实践。阳明在乡村治理中正是实践了儒家的“亲民”思想——为“富之”而维护地方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为“教之”而施行教化、纯化民风。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他以剿抚并施的策略平息了当地的起事,但军事上的获胜,并不能解决社会秩序的混乱,不能解决人心无根,民风浇漓、道德下滑的现实。王阳明进而推出乡村治理办法,他针对治安管理推出《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编十家牌》《申谕牌增立保甲长》等法规,之后又转为从施以教化入手,唤醒良知,整顿民风、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他所制定的《南赣乡约》,体现了他“觉民行道”的政治理路及教化思想,对当地的风规民俗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乡约中王阳明遵循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倡导民众从修身齐家做起,修己修德,纯化家庭伦理,再拓展至乡里,《南赣乡约》序言写道:“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乡约不仅有教化的崇高理念,也具有接地气的可操作性,体现出王阳明务实的实践性智慧。
首先是选贤任能。乡风的建设需要有组织者、执行者、管理者,这是决定乡约能落到实处的保证,也是教化得以实施的前提。乡约中规定 “约长”应是“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约长作为地方治理的最高管理者,必须是道德服众的道德楷模,而具体办事的副约、约正、约史、知约、约赞等,可按各自德行和才能,如公直果断者、通达明察者、精健廉干者、礼仪习熟者,委以他们相应的职责。乡村中的具体事务可交与副约、约正等其他职务去处理,但乡约规定必须将“彰善”与“纠过”作为约长的要务,可见对乡民教化的重视。
其次是以教化为主,刑法为次。乡约规定了对“彰善”与“纠过”的处理方式,“纠过”,注重教化,讲究言辞用语、方式方法,所谓“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对说服教育仍不能觉悟的,视其态度和悔改程度采取逐步严厉的手段,如条款所规定:“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乡约体现了阳明以心法为教化的主要手段,将刑治视为次于教化的辅助手段,只能是针对极少数恶人而设。
再次是借助礼仪,醇化民风。乡约对于婚丧嫁娶,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以礼仪教化移风易俗,醇化民风的治理思想。王阳明非常重视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其作用在于使人“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培养人们的羞耻之心、道德自律。《南赣乡约》对集会礼仪的规定非常细致、周到,集会的程序、步骤、礼节、场景、言辞都有详尽的说明。集会的礼仪活动不仅凝聚乡民,更起到教化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彰善”与“纠过”的仪式过程,强化了乡民的廉耻心,逐渐培养起他们的道德自觉。
王阳明的教化思想对当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启示
今天的乡风文明建设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更应该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动力、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社会良俗和生存智慧。文明建设所涉及的信仰 、道德、风俗、社会秩序,必然以人为中心,乡风文明建设也一定离不开对人道德自觉性的教化。王阳明的“致良知”即是对人的道德自觉性最好的教化,“良知”之教,非知识学上的“教”,而是生命之“教”,“心灵”之“教”,性情之“教”,觉悟之“教”,对今天的乡风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建立乡村德育讲堂,带动乡风文明建设
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教化思想及教育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30多岁开始讲学授徒,前后达25年之久,每到一处任职,就修建书院,倡办社学,利用从政之余进行讲学。他讲学的着眼点是改善人心,启发人性,醇化世风。他在《颁行社学教条》中说:“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而凡教授于兹土者,亦永有光矣。”立足于培养乡民道德自觉性为目标的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知识的普及,而是涉及人性修养的德性教化,诚如阳明所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书院、社学是传统社会乡村民众的教化场所,担负着醇化乡村的教化任务,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完全可以借鉴书院、社学的传统做法,在乡村中建立人文教化的讲堂,以教化人性为宗旨,带动乡风文明建设。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已经出现了类似书院讲堂的新型讲学教化场所。如果还能依托乡村“社学”“书院”或“儒学讲堂”建立起帮助乡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及困难户的自救帮扶组织,使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深入人心,以行动儒学带动乡风文明建设,将更有成效。
2.推行礼乐教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儒家的教化非常看重礼乐的作用,对百姓施以教化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灌输受教者仁、义、孝、诚、敬、忠、恕等道德观念,一是通过礼乐教化,培养人们的行为规范。王阳明十分重视礼乐教化,他认为礼乐教化是一种合乎天性的教育手段,指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将“习礼”“读书”“歌唱”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方式,这是以启发取代强制,儿童易于接受这种顺乎天性的教育,他们在歌诗吟诵唱和的快乐中,不知不觉达到了调理性情,默化粗顽,合于礼仪。阳明关于“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的观点,厘清了的“德”与“乐”之间“本”与“用”的关系。他指出:“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王阳明对于礼乐教化之宗旨——以仁为本,始终把握得很好。
对于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功用,他指出:“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决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诚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强调作为教化百姓的乐曲必须以德为本,以善为先,于风化有益。阳明礼乐教化的思想对乡风文明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借鉴乡约,强化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固然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扶,但乡村的自我治理更其重要。王阳明制定和推行《南赣乡约》,正是为了使乡村自我治理走上正途,有效治理混乱的乡村秩序,建构良好的风规良俗。《南赣乡约》的内容不仅涉及乡村行政机构的职能,还涉及风序良俗与道德规范,包括孝悌、诚信、婚嫁、丧葬及集会礼仪等的要求和规定。他试图通过乡约的规范,使管理者行使责权有章法,村民们有约(法)可依,在乡约公共舆论的制约下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现他在序言中提出的“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共成仁厚之俗。”乡约中贯穿着以教化为主导的管理思想,强调通过教化使民风淳厚,从修身齐家做起,修己修德,纯化家庭伦理,再拓展至乡里,共成仁厚之俗。王阳明将其心学体系中“致良知”的思想也融入其中。乡约中写道:“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一念而恶,即恶人”,只有不断修德修身,自我约束,才能存善去恶。王阳明的“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都直接影响了这部《乡约》的制定。《南赣乡约》的实行,对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相关县志中记载:瑞金县“近被政教,甄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日有渐矣。习欲之交,存乎其人也”,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物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南赣乡约》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及其实践,对我们今天的乡风文明建设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乡约》是本乡本土民众共同认可的规约,起着规范乡民行为的作用。由于《乡约》是乡民共同认可并遵守的约法,它就具有公共舆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不端行为的威力,可以配合道德教化强化乡风文明的建设。
(作者系贵州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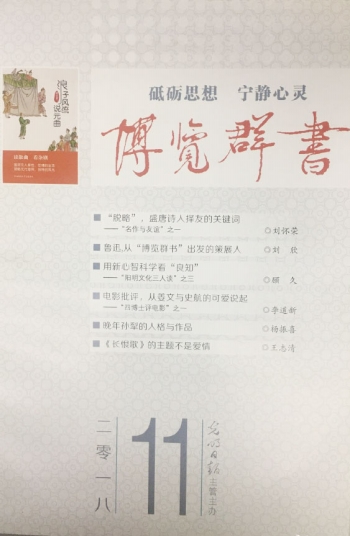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