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因为写得太凄美了,感天动地,曲尽情致,使特殊的男女情事,获得了普泛性的意义,而让人当成一种表现美丽爱情的“风情”来欣赏了。本意并非美化李杨而歌颂爱情的《长恨歌》,也因为其“侈丽宏衍”的审美特质,而让人误读为一首爱情诗,一首歌颂爱情的诗,认为“爱情是《长恨歌》的第一主题”。
为什么《长恨歌》不是爱情主题的诗呢?
/看创作初衷/
白居易创作初衷是“欲惩尤物”,或者就是说,是作为讽谕诗来写的。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的冬天,诗人时任盩厔县尉。其时,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他们相约,以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素材创作,陈鸿写一篇传,而白居易则作一首诗。关于这一点,陈鸿在《长恨歌传》的最后还作了特别说明:
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以传文得知,白居易成诗在前,陈鸿作传于后,陈鸿自称他作本传以和白居易之歌。
陈鸿的《长恨歌传》,有几个传本,文字各有异同,以载于《文苑英华》的较好,选入《唐宋传奇集》和《唐人小说》里。《唐诗三百首》本,曾以陈传载于白诗之前,二作衔接处如:“至宪宗元和元年,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自为《长恨歌传》。居易歌曰: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相得而益彰,相辅而行,流传颇广。
而在这段传文中,明确告诉读者,他们的创作初衷是警世讽喻,无论是传还是诗,都是政治批判的主题。明代张纶言亦有点赞,他指出:“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毕,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戒来世。”(《林泉随笔》)
因此,无论是从作前的初衷与预期看,还是从作后的自我评估看,抑或从后人的认知与评赏看,《长恨歌》不是歌颂性质的,不是爱情主题的,而是“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之警世讽喻的。
/看作者背景/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的冬天,白居易时年三十五岁。是年春,白居易罢校书郎,与元稹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撰成《策林》七十五篇,批判社会弊端,力主改革时政,对其时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白居易同年授盩厔(周至)县尉。
我们将此时期,归在白居易讽谕诗创作期。是其讽喻诗写作高潮到来之初期,或为讽喻诗创作的准备期。白居易存诗三千余首,为唐朝诗家存诗之首。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的,也是他自己特别看重的就是讽谕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谕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年(806)至元和四年(809)。宽泛点说,约自其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开始,到元和六年(811)四月丁母忧回乡守制为止。这段时间里,白居易参政热情异常高涨。《长恨歌》即作于此时,作于诗人讽谕热情高涨期。写作《长恨歌》后之次年,白居易调往京城,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他更是“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指陈时政,甚至面折廷诤,写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等。
《长恨歌》作于其大量写作讽谕诗的前期,可谓其《秦中吟》《新乐府》组诗创作前的热身。换言之,《长恨歌》作于白居易对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时弊大加笔伐与规谏时,作者是断然不至于将这个应该批判的题材而写成歌颂主旨的。写作《长恨歌》后的两三年,白居易所完成的《新乐府诗》五十篇里,也有多首写到杨贵妃。或者说,是他意犹未尽,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特殊的爱情题材。如《胡旋女》中把杨贵妃与安禄山相提并论,认为杨贵妃也应该对酿成祸乱负责:“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如《李夫人》中指责杨贵妃“尤物惑人”,诗中写道:“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国色。”而其《上阳白发人》,则是写李隆基的荒淫无度给无数宫女带来了悲剧性命运的。其中“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之类,也只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另一种表达。可见,白居易作《长恨歌》与作《新乐府》时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只是后来对杨 贵妃、对李杨爱情的批判更加直接与深刻罢了。
作为写作于白居易讽喻诗创作高潮到来时的《长恨歌》,这个用诗来叙述的故事,应该不会是爱情主题。白居易的讽喻诗近于诗中的杂文,泼辣尖刻,狠重猛烈,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白居易自己说就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长恨歌》与他的这些讽喻诗所不同的是,采用了“主文而谲谏”的婉讽,类似汉赋“劝百讽一”的写法,仍然是批判的主题,属于政治性的批评主题,而绝非歌颂性质的爱情诗。
/看艺术表现/
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也相当满意,十分自赏,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写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人则据此而将《长恨歌》误判为“风情”诗,甚至直接解释为“是作者与湘灵(白居易的初恋)刻骨铭心的爱情长恨”。也有人直斥其诗格调不高,败在“风情”上。唐汝询就说:“‘一篇《长恨》有风情’,此自赞其诗也。今读其文,格极卑庸,词颇娇艳;虽主讥刺,实欲借事以骋笔间之风流。其称‘风情’,自评亦当矣。《品汇》收《琵琶行》而黜此,为其多肉而少骨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唐评也在理,只是夸大了骋笔风流的负面效应,而忽略了婉讽讥刺的批判性深意。风者,讽也。风者,刺也。风情者,风雅兴寄之风致也。白居易诗将“风情”与“正声”同举,互文见义,互辞相释也。“正声”者,雅正之乐声也。意谓《长恨歌》与《新乐府》同,皆是为承“诗三百之义”也。如果这样解,结论就是:《长恨歌》不仅不是格调低下的雪月风花诗,而且也是一种“正声”,是近乎《新乐府》的讽喻诗。
首先看语言。诗人于题上即曰“恨”,且为“长恨”,寓于无限的讽喻讥刺意味。其首句直斥唐玄宗云:“汉皇重色思倾国”。此七字笔力千钧,一篇之纲,提挈全篇,奠定了全篇基调,也揭示了悲剧的渊源与讽喻的意义。其中之诗句如“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讽刺辛辣,出语沉痛。最大讽刺是借托蓬莱仙山盟誓爱情,畅述长恨,虚无缥缈而荒诞不经。诗人这样“美丽”地向我们讲述悲剧故事,讲述悲剧的主人公原来就是悲剧制造者的故事,难道不是在讽喻而却是在歌颂吗?爱情误国的政治悲剧,一个是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是娇媚恃宠的妃子,这种误国爱情岂有什么美丽可言?误国爱情即便是再美丽,也没有可颂之理。欲不可纵,乐不可极,乐极生悲,长恨无尽。这才是诗人的创作初衷,才是诗人所要讽喻君王、正告世人的道理。《长恨歌》的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有的美丽,全落实在一个“恨”字上,而且是“长恨”,无休无止,没完没了,哀艳之至,亦讽刺之极也。像这样的语言表述,揶揄戏谑,冷嘲热讽,以至于尖酸刻薄,应该不会是歌颂爱情的主题吧。
其次看情节。《长恨歌》的情节荒诞不经,貌似歌颂,对李杨生死不渝“爱情”的歌颂。陈鸿《长恨歌传》写李杨的“爱情”故事,先述开元时杨妃入宫,迄天宝末缢死于马嵬坡的始末,后写玄宗自蜀还京后思杨不已,方士为之求索贵妃魂魄,李杨再见之于海上仙山而“好合如旧”。白居易的诗,情节与传大致相同,只是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用想象和虚构手法,以及戏剧化和神话化的描写,浓墨重彩,极具浪漫色彩,使得全诗风情摇曳,极富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笔下的李杨的爱情传奇,感天动地,从人间发展到天上,似乎二人也完全免除了宫廷荒淫所应该担负道义责任,而显得非常的纯洁与崇高。殊不知,越是将他们的传奇写得越传奇,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也就越能够强化爱情的悲剧性,越具有讽刺性。
再次看作法。《长恨歌》采用的是类似汉赋“劝百讽一”的作法,典型的汉代讽喻文学的作法。所谓“劝百讽一”,语出扬雄《法言》,扬雄认为,汉赋总是以极宏大的篇幅和极夸饰的辞藻来铺叙极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只是在最后稍加讽喻,用隐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过失而点到为止。李隆基和杨玉环虽然也是人,也有常人的爱情,但毕竟不是一对普通男女,作为唐朝子民不宜也不应直言君王之过失。以“劝百讽一”之作法,就是白居易“为尊者讳”的一种智慧了。《长恨歌》恣肆铺叙,奢辞侈丽,即具有百“劝”之“美”。“劝”是手段,“讽”是目的,是一种欲讽先劝、寓讽于劝的“劝百讽一”的典型作法。正因为是“劝百讽一”的作法,百“劝”而一“讽”,其规讽之辞远不及颂美之辞的美丽,甚至美丽得让人把握不准其批判主旨而误以为是歌颂的了,譬如他把杨贵妃塑造为爱情女神的形象,譬如他极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死后的思念,譬如他升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盟誓等。这种作法,欲讽反谀,淹没了讽谏主题,即便是有所讽喻而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是,再怎么说,白居易也不会以爱情为主题,因为这样的爱情也不至于崇高到要去歌颂的,这种误国爱情的放纵也不足以歌颂。
白居易在自编诗集时,将《长恨歌》编入“感伤”类,而非“讽喻”类,这也是让人对其主题凭生歧义的原因,而以为是爱情主题或自伤主题。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正处于其人生的“感伤”期,是“江州司马青衫湿”的低潮期。而此诗中对李、杨爱情所给予的无限“感伤”之同情,抑或也引起了自伤身世的悲怨。或许是,他自己后来也觉得,诗中的同情与感伤多于讽喻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具有了强烈同情与感伤色彩的《长恨歌》就不具有政治批判性。本意并非美化李杨而歌颂爱情的《长恨歌》,其爱情的动人表象掩盖了讽刺与讽喻的实质,这也更说明了采用“劝百讽一”作法之《长恨歌》具有非常特殊的艺术魅力。然而,即便是《长恨歌》也有“违背初衷”而同情多于批评之处,而让读者觉得具有“多重主题”,我们也仍然认为,《长恨歌》的第一主题是讽喻,而不是爱情。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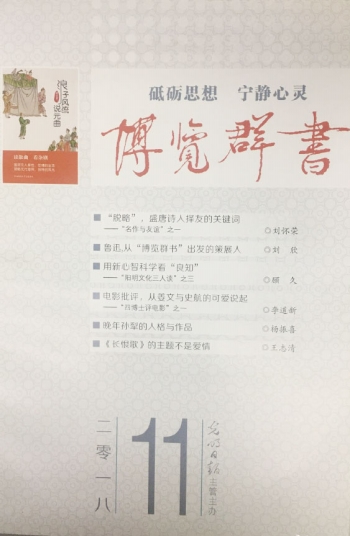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