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今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一下子推出梁归智先生的两本新书:《禅在红楼第几层》和《浪子风流说元曲》。我刚读了第二本,便忍不住要信笔涂鸦,想说说我的感受了。
这个感受需要从我的大学时代谈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中前期,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古代文学课分成四段,分别由四位老师主讲。讲到元明清文学时,梁归智老师出场了。梁老师是姚奠中先生的高足,姚先生又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这种学缘关系本身已让我们好奇;加上梁老师那时刚读完研究生不久,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直把元明清文学讲得风生水起,轻舞飞扬,这种功夫更是让我们叹服。记得1985年元旦,我曾自编一副对联,又亲自书写,把它贴在我们宿舍的门两边:“八条光棍八万根建安骨,四年岁月四十载楚骚风”,横披是“铜豌豆”。现在想来,那时敢把“铜豌豆”置于门楣之上,一方面说明我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梁老师对“浪子风流”的解读深入我心,它确实已是“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了。
铜豌豆,水晶球,浪子风流——那个时候的梁老师就是这样解读元曲的。他在这本书中交待,当年他曾写过一篇《浪子·隐逸·斗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84年9月4日)的文章,此文发表的时间也正是他给我们讲这门课的时候。于是,把最新思考作为讲课的逻辑框架,然后辅之于丰富的例证,再结合作品赏析之、阐述之,就成了他这门课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今我捧读这本新书,又恍如走进他三十多年前的课堂,真是令人好生感慨。
发完感慨,该说说梁老师的这本书了。
/贰/
虽然这本书的核心命意早已提出,但对它的解读却是崭新的。从中可以看出,那里面积淀着梁老师多年的研究心得,甚至隐藏着他自己的人生感悟。
在中国文学史中,学界对于元代文学的重视程度是远远比不上其他朝代的。这也难怪,因为元朝的存在时间本身就短(百年左右),元曲、元杂剧又不入中国文学的主流,于是对它的轻视乃至忽略好像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但梁老师却不这么看。像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部分那样,他在书中前言以“这是……时代”造句,一口气写了十四五个之多,以此说明这个时代的丰富、驳杂、宽纵、混乱,以及文人在这个时代的幸与不幸。由于科举被废,文人墨客已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晋升通道;又由于社会相对开放,禁忌较少,形而下的空间比较活跃,于是他们就收拾起精神,张扬开身体,过起了一种放纵自己的生活。在梁老师看来,关汉卿《不伏老》中的名句——“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就是元代时代精神“浪子风流”的真实写照:“多才多艺,玩文化,玩文学,玩人生。当然也可以从这里面寻找出潜伏的愤懑、悲哀、反讽……但其主调无疑是‘玩意识’,是一种以‘顽主’自居自傲的时代感。这或者能够让今天的读者联想到‘后现代’的种种‘嬉皮’‘雅皮’行为。”(P8)正是借助于这种时代精神的观照,梁老师深入到了俗文学的世界中,同时也深入到浪子与浪女、铜豌豆和辣妹子的精神世界中,完成了对他们的一次重新打量。
这种打量和打量方式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例如,为了把“上花台做子弟”(此谓元朝男人的理想)打量清楚,梁老师借助了“新感性”;为了把元朝的时代语境说得明白,他借用了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为了把浪子风流的革命性与颠覆性分析透彻,他借鉴了“酷儿理论”和“性政治”。这样一来,当今的西方理论就成了梁老师手中的解剖刀。这把刀所到之处,不但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还让我看到了作者庖丁解牛般的快感。
我想,当梁老师如此解读时,就既展示了他对西方当代理论的熟稔,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示范。古代文学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规矩”,我还是略知一二的。一种观点认为,用现在的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理论)去面对古人,弄不好就成了生硬切割,过度阐释,所以要慎之又慎。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当今的新潮学说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进入历史的理论武器,甚至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很显然,梁老师是认同第二种观点的。这其中的道理在于,虽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已是日新月异,但是人性与情感,以及被它们建构起来的文学之核,千百年来却变化甚微。这样,以今天的理论观照古代的文学也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而在我看来,关键还不是理论能不能使用的问题,而是能否用得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梁老师这本书的示范之处在于,他不但用了理论,而且还用得那么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仿佛为他量身定做一般。说实在话,每当我读到这些地方时,既觉得运用之妙,又让我这种号称是搞理论的人生出了许多羡慕嫉妒恨。
梁老师说:“浪子风流和隐逸情调是时代精神的两翼。浪子的前代模范是柳永,知名度最高的隐逸榜样就是陶渊明了。”(P51)这样,挖掘元代文人与陶渊明的关系,进而挖掘他们“中隐隐于市集”的隐逸情调,就成了这本书的另一主题。在这种挖掘中,唱颂“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的卢挚在玩隐逸;写过《双调·沉醉东风·渔夫》的白朴档次要高一些,把隐逸玩成了“上品”。而在“秋天的思索”中,马致远更是通过小令《天净沙》和套数《双调·夜行船》,把隐逸玩到了庄禅哲学的境界。当然,无论怎样玩,梁老师还是看到了元代文人露出的那条狐狸尾巴:他们固然也“采菊东篱下”了,却并未“悠然见南山”,而是悠然听见瓦舍勾栏里销魂荡魄之歌不绝于耳。“元散曲中不断出现对陶渊明的向往和歌颂,但大多数都难以深入陶诗的真境界,只是把陶渊明像个不倒翁似的你推过来我搡过去。”(P57)于是,在元代文人那里,尽管隐逸情调也是时代潮流,但也许终究敌不过世俗享乐对他们的诱惑。结果,他们假装隐逸几下之后,接着又开始浪子风流了。
在元代文人的隐逸之外,梁老师还有拓展性思考,因为他接着写到了当今时代梭罗的实践,苇岸的哀伤,赵鑫珊的希望,以此呼吁人们对隐逸文化多一份同情的理解。读到此处,我忽然意识到梁老师热衷于打捞隐逸,或许已注入了他自己的某种生命体验。因为在另一本书中他曾说过:“‘蓦然回首’自己的大半生,有点吃惊地发现了一个真相,自己一直没有清醒面对:一直在逃,一直想隐。”(《红莓与白桦:俄罗斯游学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330)至于为什么要逃和隐,我此前已有文章做过分析(参见《去俄罗斯走夷方》,《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5日),兹不赘述。这里我仅想指出的是,当梁老师自己也想隐的时候,他对元代文人隐逸情调的阐发、不满乃至一定程度的呵护,或许已是在“以我观物”了。
这本书中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斗士精神,主要是针对元杂剧的,也很有看头。但为了给我后面的谈论留出篇幅,这部分内容我就不再涉及了。
/叁/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这本书的文体风格。只要打开这本书读几页,我们马上就能意识到它与一般的学术著作并不相同。虽然此书的学术含量很高,启人深思,但它却并非让人一读头就大的高头讲章,而是融学术思考于娓娓道来之中,能让人获得一种阅读快感。为什么它有如此效果呢?答案其实就在《禅在红楼第几层》的“写作弁言”里。梁老师说:“我写的不是‘论文’而是‘论笔’,这当然是笔者的杜撰。习见的‘论文’以西方文化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为特征,自然有其合理锋利的一面,但也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文体的单一枯燥,让人望而生畏,而减少了流通性和影响力。”这里的交待,应该是他启用“论笔”的学术语境。那么,什么又是他所谓的“论笔”呢?梁老师紧接着也做了解释:
我杜撰的“论笔”,意思是提倡一种随笔文章其形而有论文之实的文体,或者说“做论文”要和“写文章”水乳交融。其特点是研究和写作都要突出“灵感”和“悟性”,“逻辑”是内在而非外在的,还要讲究行文措词的“笔法”,而不呆板地标榜所谓“学术规范”。
因为说到本根上,中华文化是艺术型感悟型文化,不是科学型逻辑型文化,太着相于表面的逻辑和“科学”,对中华文化孕育出的传统文本往往隔靴搔痒而难摘得其骊珠。(P5-6)
第一次听梁老师当面谈及“论笔”话题,我记得是2013年年初,那时他已把“论笔”写作经营了许多个年头。从他的讲述中我才大体清楚,他之所以要自造新词,自创新体,就是因为许多年来,我们已被“论文”和“论文体”彻底绑架了。“论文体”是西方科学主义和逻辑思辨的产物,虽然它自有其存在价值,且已是当今学界的主流文体,但久而久之,其问题也日渐突出——繁征琐引,三纸无驴,形式逻辑,名相纷列,崩人牙齿,难以下咽。既然“论文体”问题多多,梁老师便干脆弃之不用,而是用他发明的“论笔体”著书立说写文章了。
在我看来,《浪子风流说元曲》就是“论笔体”的典型文本。而细究起来,这种文体除讲究一般性的文学笔法外,它在行文表达方面还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感悟之思。当梁老师指出“中华文化是艺术型感悟型文化”时,我以为他是在强调师法古人,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古代的文论家想问题写文章不是黑格尔式的逻辑分析,而是更接近于诗人、艺术家的直觉感悟。于是,尽管他们把其思考上升到了理论言说的高度,却依然保留着鲜活的感性特征。梁老师研究了一辈子古代文学,对于古人的思维与表达自然了如指掌。这样,如何让充满灵性和悟性的思考进入到文章之中,显然已是他自觉的学术追求。而验之于《浪子风流说元曲》,这种感悟之思确实也比比皆是。
例如,身体性和精神性、物质性和灵魂性,是他描述元代文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对举性概念,可谓理论概括,但在具体展开的阐述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条感悟的草蛇灰线蜿蜒其中。他说《不伏老》把一个“浪子”刻画的活灵活现,《救风尘》则把一个“浪女”表现得惟妙惟肖,何以如此?因为那里面的浪子(女)风流都超越了“身体性”而达到了“精神性”。接着他进一步议论道:“人浪就有意气,就有股子冲劲,就敢闯能闹大胆抗争。元杂剧里的浪女们大多数都是辣妹子,敢爱敢恨,勇于追求幸福。”(P24)把人浪与冲劲、闯劲、意气风发联系起来,进而让浪女与辣妹子形成一种意象关联,我以为这就是感悟之思。这几句话一出场,一下子就让人明白了“浪”与人的生命元气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对“浪”形成负面联想,那就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其次是话语蒙太奇。我在前面说梁老师把当今西方理论拿来,活学活用,这是打量的视角或切入的角度。而在表达层面,他也会不断以今释古,古今对话,既让两者碰撞出火花,也增加阅读的趣味性。比如,他说“铜豌豆、水晶球是戏谑,但并不完全是反讽。正像王朔的‘顽主’们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并不是自我糟践,反而是自豪的宣言。”(P6)又比如,在描述了坏浪子的种种作派之后,他如此评论道:“衙内们大抵是一些文化素养差、艺术档次低的家伙,他们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温柔,只沉溺于肉欲和暴力的低级恣意享乐。沙龙里雅歌清唱,作赋吟诗,高谈阔论,歌厅里放的则是枕头加拳头的录像片。”(P113)
像这种表达,就既风趣幽默,也能把古人的生活、宣言等等迅速拉入当下现实,让它们在古今间的镜头切换之余,释放出更丰富的意义。这种话语蒙太奇可丰富表达,可增强理解,当然也给读者提出了一定要求:他必须对当下的文化掌故了然于心,否则就会不明就里。例如,当梁老师解释元代文人的“俗”时,忽然冒出这样一句:“很难说这种‘俗’好还是不好,王朔说好,张承志就说不好。”(P75)这个“梗”虽然也照应了前面的俗痞与崇高之争(P19),但只有对“躲避崇高”的王朔和倡导“清洁的精神”的张承志有更多了解,甚至熟悉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正反双方的观点,才能在这里发出会心一笑。
第三个特点,不妨称之为“作者闯入”。作者闯入本来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惯常使用的一种小说技法,意指作者中断了正在叙述的故事,现身说法,发议论,谈感受。一般性的著作论文往往通篇客观论述,作者是不宜出场的。但假如作者忍不住站了出来,中断了正常的论说,讲述开了自己的经历或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作者闯入。
在《浪子风流说元曲》中,我就看到了梁老师的“闯入”。比如,当他比较了一番元曲之俗和当今的俗文学大潮之后,忽然有了如下感慨:“忍不住做这种比较,就笔者个人而言,情绪上是有一点迷惘和感伤的。赵盼儿或谭记儿,似乎比今天的歌厅小姐或‘上海宝贝’更可爱,好像也更‘有文化’。元曲的情爱世界虽然染上了一点后现代色彩,但比起真正的现代、后现代之情欲分裂的畸恋畸爱来,却更健康、更美丽、更有魅力。”(P31)又如,当他对《赵氏孤儿》的论述告一段落时,忽然插入了“想起当年读雨果《九三年》时的激动”,接着便是一番别开生面的反思(P109),这一处也是作者闯入。
作者闯入的文字进入正儿八经的论述之中,大概可以算作游离之笔,但这种游离又有特殊的美学功能。因为它一方面稀释了论述的坚硬,另一方面又拓展了表达的空间,同时还因“暴露”了自己的情感或隐私,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可谓身兼数任。所以,要想把文章写成“论笔”,我以为这种笔法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梁老师身体力行“论笔”和“论笔体”,我可以说是举双手赞成。因为近年来我也在撰文呼吁,希望把“随笔体”融入到论文写作中,让文章在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同时也具有某种文学性。如今,梁老师又亮出“论笔体”的旗号,更是让我感到振奋,很受鼓舞。于是我既借用他之“论笔”,对译阿多诺所谓的Essay,又把自己新书《赵树理的幽灵》中的一组文章称为“论笔”。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已在心摹手追,向梁老师学习。我想,如果我们的学人能像梁老师那样,把著作论文写成锦绣文章,那么,学界很可能就会是一番不一样的气象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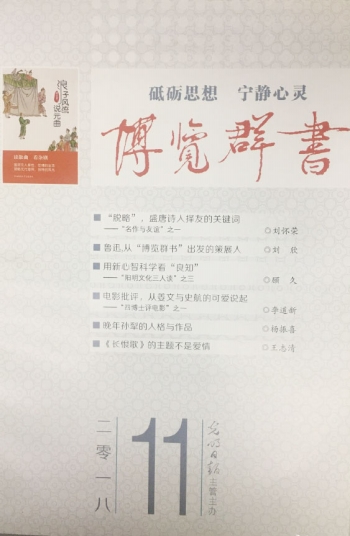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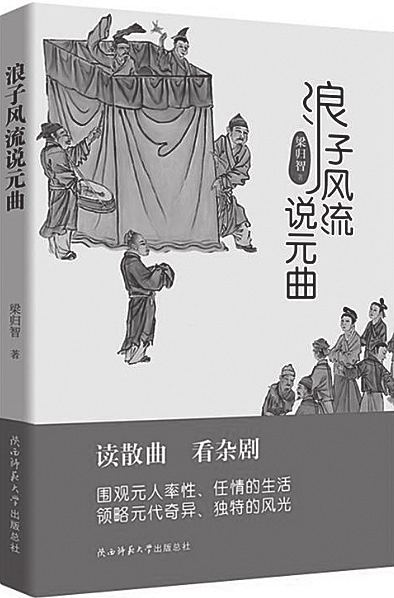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