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继《江南三部曲》后,凭借着《望春风》再次回归乡村,作为对乡村的一次庄重的告别。“即便中国的乡村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对我来说,是彻彻底底地结束了”,“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望春风》是小说中人物赵泊瑜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乡往事,故事中穿插了几十个人物交错复杂的命运。从1958年至2007年,时光荏苒,人生浮沉,从属于老一辈们的世界逐渐转变为“我”们的时代,整个村庄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发生结构巨变,打破了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间秩序,最终沦为一片废墟。随着城市现代化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与乡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乡村在城市快速发展的碾压与吞噬下,正在逐渐凋敝,面临着消失的危机。
“我”童年时的儒里赵村:古风犹存
儒里赵村是一个风景如画,并有着显赫历史的江南乡村,充满着自然清新的乡野气息和纯净质朴的人文环境。儒里赵村一直保持着“儒”的传统:村里的长者赵孟舒自幼学琴,琴艺精湛,声名远扬;妓女王曼卿也是一个精通古琴的才女,与赵孟舒互为知音;“老菩萨”唐文宽擅长说书,甚至还会说标准流畅的英语;“刀笔”赵锡光替人做合同、写状纸,还教小孩子念书识字;他的夫人冯金宝也是读书人,夫妻俩连吃饭也要讲究规矩礼仪。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使传统乡村充满了诗情画意、温顺祥和,他们有着更多的文化知识、较高的精神素养、更丰富的阅历和更广阔的视野,他们在乡村里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和教化平民百姓的责任,同时参与乡村的教育事业和地方管理,他们是整个传统乡村的引领者,也是乡村的灵魂。
“我”的父亲赵云仙是一个算命先生,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人面桃花》中张季元的影子,他和张季元一样,机智聪明,并且推理能力极强,他能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大胆的推测,正确算出农户家的孩子是在前年掉入茅坑淹死的,而且在预知生死、推测命运的大事上料事如神。小说中父亲的出场,使整部作品增添了悬疑色彩,尽管父亲在前半部分就已经离开人世,但直至小说结束,父亲仿佛始终存在于读者的视野中,陪伴着“我”成长。时间验证了父亲的预言句句成真,他选择了结生命的便通庵,是整个儒里赵村唯一幸存的地方,而“我”也将兜兜转转,仿佛有一双命运的手将“我”一步步推向便通庵,便通庵是起点,也是终点,人生和命运在此处合拢为圆。
“我”中年时的故乡:似乡非乡
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农村展开,给乡村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秩序。土改工作队打破了传统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带入了等级制度与阶级,村民的命运随之发生了颠覆,例如曾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赵德正当上了农会主任,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指导员和教导员;章珠从一个身份卑贱的童养媳变成了妇女主任,进城当了官太太。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如此幸运,赵孟舒在这一场土改中栽了跟头,他被扣上地主的帽子,在批斗会上丢人现眼,倍感羞耻、侮辱与不公的他选择服毒自尽。1958年,党中央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了严重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广泛开展,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村民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灾难。村民先后两次制造了拥有充足存粮的假象骗过了检查组的抽查,乡村里不再是自然传统、简单朴素的风气,更多的是欺骗、虚荣、浮夸的作风和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作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的梅芳,满口都是“共产”风,“冒险主义”“资产阶级盲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错误的政治思想像一颗毒瘤深深埋入百姓的心里,毒害了传统朴实的村民,自然淳朴的儒里赵村变得似乡非乡。
20世纪80年代,城市现代化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发展缓慢的乡村与城市产生巨大差距。村民羡慕并渴望拥有城里人高品质的生活,他们学习城市建设自己的乡村。为了扩大乡村的教育规模,提高村民的文化程度,他们将传统的私塾改为正规的儒里小学。村民们还运用乡村的地理条件和优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财富,他们计划推平磨笄山,以获得更多的粮食,既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也能解决饥荒问题。同时,往返于城乡的村民在两者之间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不断地把现代化的思想和科技引入乡村,例如丝袜、肥皂、电视机、收音机、大屏幕的彩色电影……不仅拓宽了村民的视野,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乡村的村民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方式,由重农变为重商,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商业的桥梁。富有创新精神的赵礼平将传统的配种方式与现代科技结合,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因此成为农业技术员,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越来越富裕的他不断拓展业务,变成了工厂老板,又成为朱方集团的董事长,他的势力从儒里赵村、朱方镇,一直蔓延到省城、北京,他的业务甚至拓展到深圳、珠海、香港,金钱为他带来了荣誉、权力、地位、美女,仿佛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难题。村民们也秉承着“金钱至上”的原则,纷纷投入了商业的浪潮中,乡村里几乎一半的土地都荒废了,每个人都梦想着一夜发家:赵宝明办了个模具厂;赵宝亮办了家五金电配厂;小武松和银娣开了个酱菜厂;王曼卿和柏生合伙办起了养鸭场;唐文宽做起了补习英语的生意。在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下,商业观和金钱观深深影响了村民,淳朴敦厚、老实善良的传统村民向商人转变,也使传统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我”年老后回归的故乡:沦为废墟
政府和开发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纷纷把目标移到了农村大片荒芜的土地上,他们逼迫村民们接受拆迁,然而由于政府的巨额负债和赵礼平资金链的断裂,重建的工作暂时停了下来,儒里赵村彻底沦为了废墟,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产生陌生感:阁楼布满了发霉的痕迹;羊圈里长出了一片野生的向日葵;红头聋子的家倒在猪圈和柴屋里;赵家宗祠被夷为平地;遗落的麦粒在大晒场上发芽,形成了一片稀疏的麦地;茅草和蒿莱遮住了乱砖碎瓦,野生的南瓜藤、野菊、牵牛和蒲公英爬满了残垣断壁;池塘中的水长满芙蕖和萍藻;果树已经硕果累累却无人采摘;只有便通庵因远离村庄得以保留。窑头赵村也没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存, “我”和父亲看到狐狸的乱坟岗上立着“韩泰轮胎”的广告牌;半塘村变成了墓园,当年春琴手摇纺车的地方耸立着“李阿全”的墓碑……随处可见的只是大片的工业园区和一排排居民楼群。
90年代,传统乡村逐渐在科技、信息、工业、商业等领域远远落后于城市,并被打上了“贫穷”“落后”“封建”“愚昧”的烙印。乡村和城市本是地理学上的概念,却被划分为传统落后和先进文明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城市像一张血盆大口,不断吸引着乡村里有能力的年轻人,一步步吞噬着残缺凄切的土地。贾平凹在《极花》中不仅展示出野蛮的乡村男性强暴胡蝶的血腥场面,同时也展现了乡村的原始风貌,邻里的团结和睦,以及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照顾;电影《盲山》中,导演在郁郁葱葱、风景宜人的崇山峻岭与黑暗、孤独、暴力的场面之间无缝切换,给予观影者双重矛盾的心理冲击。他们想要表达的不仅是农村拐卖妇女这个恶劣的社会问题,还有其背后更为严峻的城乡问题。在《望春风》中,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与这座喧嚣热闹、灯红酒绿的城市格格不入,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透出城里人厌恶的“土”气,农村人若是不小心惹恼了城里人,便会不停地被骂“乡巴佬”。传统的农村人无法彻底改变血液中流淌的乡味和与生俱来的风俗习惯,他们天生是属于大自然的。城市不仅吸引着村民,甚至贪婪地想把乡村的一切都吞噬,他们将风景秀丽的村庄变成了肮脏泥泞的工业园,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以及几千年来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乡村彻底消逝了。
格非有着浓郁的“归乡情结”。《人面桃花》中秀米被绑架到花家舍,远渡日本后又再次归乡,在自己的家乡试验一场桃花源梦;《山河入梦》中姚佩佩失手杀害了对她施暴的高管,从普济镇逃亡后竟然又回到了普济镇;《春尽江南》中庞家玉在病重时希望丈夫能把她的骨灰埋在家门口的石榴树下,表现出强烈的对故乡的怀念,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庞家玉用着年轻时的名字“秀蓉”和丈夫通话交流,意味深长地代表着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回归。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故乡怀有不可替代的情感,就如同《望春风》中的“我”从未把邗桥的公寓当作永久的栖息之地;章珠每天都在信纸上吐露对我的思念和对家乡的眷恋,她希望死后能够把她的骨灰撒到扬子江中,她便能随着水流回归她的故乡。命运引领着“我”归乡,最后,“我”和春琴在唯一幸存的便通庵安度晚年,远离了所有现代化的元素,回归到最初的精神家园。格非三次写道“我朝东边望了望,我朝南边望了望,我朝西边望了望,我朝北边望了望”,表明了作者希望现代人的眼光不仅要向前看,也要向后回望历史,不能一味追求城市现代化、工业化和经济利益的快速发展而放弃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毁灭了建立在乡村伦理基础上的中国乡村社会。格非所认为的“归乡”并不是回归到野蛮落后、脱离现代的原始之地,也不是反对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发展而盲目地为愚昧落后的乡村歌功颂德,他所希望回归的是人类最初的精神家园,是每个人的“根”。尽管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着他们曾经踏过的脚印,镌刻着时间划过的痕迹。
给予人们未知的希望
《望春风》是格非对乡村的一次告别,他匆匆记录下中国最后的乡村,又在文章的结尾处给予人们未知的希望——“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所谓“春风吹又生”,春风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传递希望的媒介。与《江南三部曲》的凄凉结局不同,《望春风》用真情的温暖融化了基调的悲凉,在绝境中给予人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可是乡村是否还能存在?城乡关系是否能够改善?现代文明如何进入传统乡村,才能使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相辅相成?这不仅是城市对乡村的反思,也是现代性的反思。现代人不能忘记历史和传统,中国的土地上更不能没有乡村。格非指出重建乡村的艰巨任务,本质上并不是让老一辈回归故乡,而是要鼓励并号召有能力的年轻人回归乡村、建设乡村、繁衍后代。发展城市的同时不能忽略和遗忘乡村的建设,更不能损害乡村的发展前景,另外乡村也要找寻合适的出路,大力发展乡村优势项目,例如开发旅游业,办农业生产基地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将衰败的乡村变为改造中的乡村,将乡村一脉延续。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余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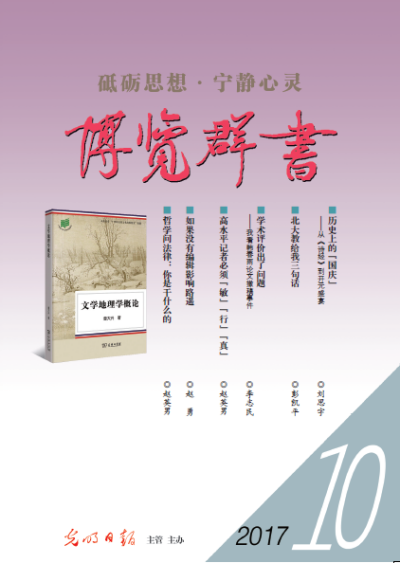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