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地图上,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地标式建筑,这里居住过两个“地标式”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当周氏兄弟如日中天的时候,大宅院里出入过许多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沈雁冰、郁达夫、梁实秋等等,毛泽东也曾慕名来访。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这里是京派文人们雅集之所。周作人被捕入狱后,八道湾十一号被部分占用,1949年后沦为大杂院。到了新时期,又重新吸引了众多的关注。我本人于1990年代初在江绍原之女江小蕙的带领下,进院参观,同行的有李大钊的一个后代——好像是他的外孙女。我还去了院内做过周家女佣的白发老人的家小坐,听她诉说自己眼中的周作人。1996年,八道湾胡同面临被拆毁的危险,关键之时,鲁迅的声望发挥了作用,使得宅院幸免于拆。近年来,随着金融街的扩《八道湾十一号》 黄乔生著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建,第三十五中学高中部搬迁至此,八道湾十一号被作为校内文物保留了下来。然而,旧有胡同的肌理与风貌消失了,八道湾十一号终究成了一座“孤岛”,现代大都市中一处古色古香的盆景。
值得高兴的是,黄乔生推出专著《八道湾十一号》。该书提供了周氏兄弟故宅沧桑和人事关系的完整“档案”,并把它与现代的历史风云联系起来,揭示了这一文化地标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精神内涵。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雅俗共赏的好书,从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更新了对八道湾十一号和周氏三兄弟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充实了周氏兄弟的基础研究。孙郁曾出版过一本《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对一个个曾进出过八道湾十一号的周作人的朋友进行勾勒,探讨了这一文人群体的精神特征。《八道湾十一号》与孙著可谓珠联璧合,弥补了学院派文学史研究的不足,评介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没有的人物,拓展了研究的领域。黄乔生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供职,孙郁也曾经在这个单位工作过,他们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相关的文献、实物和人员,突破单纯文献研究的局限。从《八道湾十一号》后记中知道,作者不仅做过广泛的调查,还参与了周氏兄弟故居的保护工作,出谋划策,如今的“周氏兄弟旧居”的名称就来自他的提议。
黄乔生出版过一本《渡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又花五年时间写作《八道湾十一号》,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与相关研究相比,《八道湾十一号》提供了更全面、更翔实的材料,特别是首次引入了新近出现的日文资料。当然,光有材料是不够的,作者还表现出了公允、求实的态度。他不回避敏感的材料,如引入周丰一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对兄弟失和原因的解释,而且处理得很好。黄乔生尽量避免成见的束缚,不是一谈到周氏兄弟就“褒鲁贬周”,而是用材料说话,并进行合情合理的分析。只有做到了以上两点,他才可能把周氏兄弟关系研究推进一步。
在八道湾十一号的长篇故事里,鲁迅、周作人及其两房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其关键节点是1923年兄弟失和。兄弟怡怡,成为参商,这对两人的人生道路和创作,进而对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务事”延伸到了公共领域。关于兄弟失和的真正原因,一直没有直接、确凿的证据,然而人们总是习惯把价值的天平倾向于鲁迅一边,对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大加指责。此一话题关系着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至今仍具有较大的敏感性。这对研究者是一个考验,对本书作者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而黄乔生的态度是谨慎的,他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这一点比大多数相关研究者做得要好,不过仍有可以商榷之处。
这对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为什么各奔东西?最通行的说法有两个:一是鲁迅与弟妇羽太信子间的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二是经济的原因。持后一观点的人往往说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因为有鲁迅的制约,感到花钱不痛快,于是造谣说大伯子对其“不敬”。就是说,羽太信子离间兄弟关系,以达到分家的目的。此说的证人最多,最安全保险,也似乎最能保全当事人的体面。黄乔生深知问题的复杂性,说失和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但还是强调:“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值得考虑。”并据此进行了推测。只是,此说的疑点实在不少。分家的方式多种多样,这种方式显得过于奇葩,杀伤力也太大。事后,鲁迅受到沉重的打击不说,周作人始终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认为过去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另外一个当事人羽太信子夹在两兄弟之间,也会深受伤害,然而她被指为一个“恶人”,成了一个任人猜度的无言者。周作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一个容易听信别人、容易冲动的人。当听到关于哥哥的说法后,他会调动自己的记忆——过去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从而做出判断。鲁迅小说《弟兄》是以周作人的一次生病经历为素材的,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复辟前后一》中写道:“在我生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要收养你的家小了。后来在小说《弟兄》末尾说做了一个恶梦,虐待孤儿,也是同一意思,前后相差八年了,却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解,或者须求之弗洛伊德的学说吧。”这话里是有强烈的暗示的。我注意到一则材料。《鲁迅收藏的书信三十六封》(《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收有一篇《羽太重久致鲁迅》,作于1925年10月7日。羽太重久为周作人的妻弟,此信是对鲁迅8月26日信的回复,其中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还谈到替鲁迅在日本购书。看来,在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对羽太家仍有资助,这是不合常理的,颇使人感到意外,需要进行研究和解释。
更为关键的是证人证言的可靠性问题。黄乔生注重用材料说话,有的地方引述别人的观点而不予置评。可是,在没有别的材料参照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把“一家之言”当作可信的权威解释和评价。材料是特定的人留下的,难免有偏向。作者在谈到其中的某一问题时,多次引用俞芳、许寿裳、许广平、周建人、唐弢等人的言说,而这些人是亲近鲁迅一边的。他们的文章讲述的是“家务事”,作者有着强烈的倾向性。作者在引用某人的话时,如果能点出他们与鲁迅、周作人的亲疏关系和说话的历史语境、个人语境,可能会更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
俞芳、许寿裳、许广平、周建人、唐弢等人的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研究者和公众对周氏兄弟关系的认识和评价。俞芳写过《太师母谈鲁迅兄弟》《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我所知道的芳子》《谈谈周作人》等多篇谈论兄弟分手的文章。可文中所述大都非亲历,而是间接听来的。俞芳和姐姐俞芬、妹妹俞藻是鲁迅居住北京西四砖塔胡同时的邻居,那时作者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俞芳与鲁迅一家关系亲密,而憎恶周作人、羽太信子。她在《谈谈周作人》说:“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从家庭这个角度来看,信子和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理由是她们在北京结识了各种日本朋友,“有好人也有特务”,日后周作人“正是日本特务们物色的汉奸对象”。这只能说纯粹是想象了。许寿裳与周氏兄弟都是老朋友,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黄乔生在引述许寿裳的话之后,指出:“许寿裳的文章是在周作人因投敌叛国被判刑后写的。”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到说话人在周氏兄弟之间是有偏向的。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做出了较为激烈的回应:“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作为周氏三兄弟之一的周建人,其说话的分量自然会更重。他在1983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鲁迅与周作人》,在他的描述中,周作人是一个“意志薄弱者”、八道湾十一号的“唯一臣民”、“逆来顺受”的“沉睡中的奴隶”。文章写道:“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1932年11月20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止庵指出,这番话常被人引用,甚至据此立论。然而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还有后文,即周建人以“……”替代的:“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外事”与“废名”之间原有逗号,本来是一句完整的话。“启孟真昏!”未必是由“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演义而成,但至少没有讲明鲁迅是在何等情况下发此议论。忽略语境,特殊判断就会被看作一般判断。”周建人在文末记述了他称之为“永诀”的与周作人的一次见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意外相遇。周作人“颇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又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周建人写道:“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这一切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这个场景颇具戏剧性,在新时代的机构里邂逅,一个神情黯然地悔恨,一个表现出胜利者的冷傲。这让我想到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的“诀别”。那一次,林道静行进在游行队伍里,而余永泽冷漠地站在邮政总局高高的台阶上,此时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阶级分野。正如黄乔生书中所言:“按周作人的性格,只会把这一切默默忍受。迄今没有发现他在解放后曾向弟弟求助的资料。正相反,他对建人满怀怨恨和蔑视。”周作人连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的态度都是平起平坐,他到底有多大可能在一向不大瞧得起的弟弟面前低三下四呢?
人情总是容易偏听偏信,以至偏袒,还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凭空编造。唐弢是资深的文学史家,他的话总该靠谱了。然而,也不尽然。唐弢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说,1950年,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等,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辩解信,唐弢从郑振铎处得见此信。唐文写道:“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人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个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文化汉奸嘛”几句话带着霸气,简直非毛泽东而不能言之,唐弢本人又是新文学史家,许多人深信不疑,流传甚广。后来,倪墨炎在《晚年周作人》(之四)(《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8期)中细加辩驳,得出结论:“所谓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要‘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云云的故事,是唐弢凭想象虚构的。由于他不熟悉政府机关的办事程序,因而想象错了,他所虚构的故事也就因种种破绽而不能成立。”所谓毛泽东的“批示”也经不起推敲,属于子虚乌有。上述“主要是从谎言的破绽中指出谎言的不可信”,还有可以“证实谎言的真凭实据”,这就是收在《胡乔木书信集》中的1950年2月24日致毛泽东信。信中说,周作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胡的意见是,“他应该彻底认错”,“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照办。”从此信可知,周在1949年年底或1950年年初给周恩来写信,由于得不到回信,他大约在1950年2月上旬又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接着,2月18日,又给周扬写信,并附去给毛泽东的信的抄件。周作人直接给毛泽东写的信,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他给周扬的信及附信,也由周扬转给了胡乔木,“胡乔木拟具上报毛泽东的处理意见,事先是和周扬商量过的,所以乔木说‘周扬也同此意’” 。
以上针对几篇影响较大的回忆录提出一些质疑,绝非是要肯定鲁迅有何过失,而主要是想通过回忆录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个人立场对真实性的制约,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研究者面对回忆性史料,需要搞清楚说话人的立场。具体一点说,应该考察他与当事人的关系,明确说话时的历史语境和个人语境,把他的话语置于所有相关材料中进行对照、甄别,力求找出佐证。可疑的材料或孤证只能姑备一说,不可作为“信史”。另外,也要防止道德评价所导致的误区和偏见,不能因为鲁迅是伟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什么都是后者的错,甚至往他身上泼污水。俗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周氏兄弟失和的问题,在掌握确凿的证据前,最好的态度是保持最大程度上的审慎。否则,哪怕说得天花乱坠,也徒劳无益,甚至露出自己的马脚来。
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有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盲艺人要说的是东汉蔡邕的故事。蔡邕曾官至左中郎将,传说他考中了状元,因为贪图富贵,抛弃了在老家忍饥挨饿的父母妻小,当了牛丞相的乘龙快婿,后来被暴雷震死。而那个住在历史上的蔡中郎并无其事。总有人喜欢根据自己的兴趣涂抹历史,臧否人物,甚至不惜虚构。(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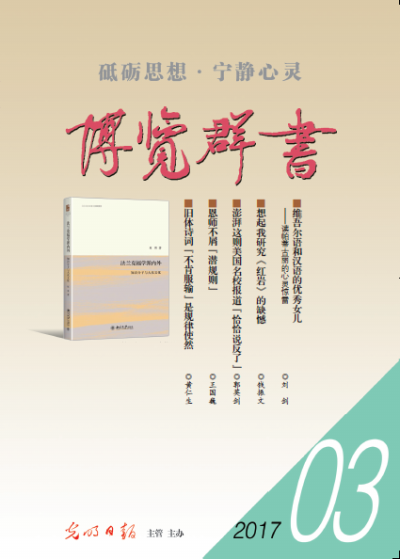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