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的什刹海微波荡漾,在它的西侧有个院落里铺满了黄色的银杏叶,这对于深秋的北京来讲更有一番风味在其中,这就是坐落于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纪念馆。在北京众多古建筑中,郭沫若纪念馆所在四合院的历史并不算是特别长,仅仅不足百年。无论它最初由恭王府地产一部分到乐氏达仁堂私宅的转换,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蒙古大使馆到宋庆龄寓所的更迭,最终却是因郭沫若晚年在此居住而成为现今的状貌。
走进郭沫若纪念馆立刻会被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吸引,一尊在银杏树下郭沫若的铜像会给你带来无限的遐思,一面郭沫若书法的墙壁会给你带来艺术的感染,一本本泛黄的郭沫若作品会给你带来文学的感悟,一张张历史的图片也会带给你长久的回忆,处处都在告诉来此的人这里曾经是郭沫若的居所。
现在的前海西街18号原为中医世家乐氏达仁堂私宅的一部分,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来先后做过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寓所。1963年11月,郭沫若由北京西四大院5号迁入,至1978年6月12日病故,他在这里度过了晚年,这15年里他有过欢乐,也有过悲伤,有着辉煌,也有着低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最后15年的郭沫若留给世人的更多是付诸报刊版面上以国家领导人面目示人的形象,而他作为一名普通人的存在被我们忽略了,因此现在多数人更愿意谈论的是郭沫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混乱时刻所做出的文化和人生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言行,而忽视了他作为一名父亲、一名丈夫和一名普通文化人所呈现出的不同社会角色的样态。进而也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单一化、平面化和绝对化,而忽视了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
前海西街18号
一个被政治空间所挤压的郭沫若
前海西街18号是一个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能够入住其中也是彰显出郭沫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搬进这所院子之前,郭沫若不是没有犹豫过。据现存资料记载,起初郭沫若自己并不愿来此居住,因为他觉得院子太大了,住宅条件太好了,在他心中自己不应享有如此高的待遇,最终周恩来总理出面劝说,表明这座宅子并非简单供郭沫若私人居住,也是考虑他作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科学院院长办公和接待国内外友人的需要才分配给他使用的。如此郭沫若才改变初衷,同意搬来居住。这也许是个比较合理的理由,但我更愿意相信郭沫若的犹豫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如此,他何尝不知如果搬入这所院子之后便会注定,他行将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形象、一个社会文化代表而存在,这必将与过去的那个充斥着个性自由呼喊、,天马行空想象的郭沫若告别。
事实情况也印证了郭沫若的这种担心,虽然这所院落宽敞精致,但在这里真正属于郭沫若个人思考和活动的空间却寥寥无几,甚至有些小得可怜。现在按照郭沫若生前的原貌保存了下来的原状展厅便清晰地印证了这些。透过展厅的玻璃窗你会发现会客室、办公室兼书房、卧室被分隔得清晰明确,在这明晰的分隔中郭沫若个人的空间其实已经被压缩得所剩无几了。从空间的维度上来看,从会客室到办公室兼书房再到卧室的面积空间是逐步缩小的,单就完全属于个人空间的卧室来讲,这里的布置相对于前两者已经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一张棕床、一张单人沙发、一套衣柜,一整套带木盒的《二十四史》,单就这几件简单的物品已经让本来就已狭小的卧室显得更加局促了。在这里唯一能够体现出郭沫若个人性情的便是这套《二十四史》,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每当处理完各种繁杂的政务和公文后,一天归于平静的时候,郭沫若自己一人安静地躺在床上顺手拿起《二十四史》中的一本认真研读的场景,再无喧嚣的吵闹,再无无绪的争斗,而是进入自我沉思的空间,但这属于自我的空间又是那么的狭小和短暂。
相对于个人空间的狭小,作为会客室和办公室的公共空间却是非常宽大。这个会客厅是郭沫若用来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面积大约有卧室面积的三倍还要大些。因为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所以他要经常会见来自各方的不同客人。马蹄形摆置的沙发占据了这间会客厅绝大多数的空间,还有靠墙角摆放的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是郭沫若接待友人时习惯的坐椅,最尊贵的客人在他左手的位置上。沙发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的是傅抱石专为郭沫若“量墙定作”的巨幅山水画《拟九龙渊诗意》,描绘的是郭沫若笔下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美景。总之,这件会客厅中摆设的物品都追求着“大”的原则。细看一下,这里所有的摆设和陈列其实与其他人的会客厅别无二致,更多的是为了待客之道,属于自己的空间几乎没有。
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略显奢侈的大房间就是郭沫若的书房了,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办公室。屋内西侧一排高大的书柜倚墙而立,满满排列其上的中外文书籍暗示了主人贯通古今中西的学识。书房窗台上满布的一堆堆科学院科学考察报告、国情社会调查资料、待批阅的各类文件,诉说着主人公务的繁忙。
正是如此,作为一位文化巨匠,郭沫若寓所中这块写作空间显现出“书房”与“办公室”的双重特性,这恰恰是这一时期郭沫若社会身份的反映。从新中国诞生时起,郭沫若就不再仅仅是一位文坛斗士,此时的他更多了一重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迁入前海西街18号更是对他这一身份的认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轨迹,他们主动压缩了自我写作和思考的空间,真诚地歌颂新中国的伟业和美好前景。
前海西街18号
一个青春诗性依旧的郭沫若
如果说郭沫若纪念馆里有什么样的特殊景观,我觉得放置在草地中的一对石狮子应是其一,这也是郭沫若纪念馆内往往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重要物件。在一进郭沫若纪念馆大门的右手边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放置着一对威武的石狮子。你也许非常惊讶,为什么这对石狮子放在了草地上,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习俗,石狮子应该是放置在住宅大门两侧,起到震慑的作用,并凸显出宅子主人的威严。但是在郭沫若的心目中,石狮子也应该是一个动物,既然是动物那就应该把它们放置在自然之中,去恢复动物原有的本性,这样才能让它们在本真的状态中去生活,由此便折射出郭沫若内心中本有的童心思维和他对青春诗性的向往与追求。
青春和童趣何尝不是郭沫若此时的向往呢?因为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郭沫若只能将这种向往深深地埋在内心。《英诗译稿》的翻译便是在此种境遇中产生的,也是郭沫若晚年隐曲心境最典型的体现。《英诗译稿》是郭沫若翻译的最后一部诗歌作品,也是被研究者们所忽视的一部译作。在郭沫若翻译作品中,《英诗译稿》无论是翻译的时间、方式还是内容等方面都显示了非常多的独特性。这部诗歌译作和之前所翻译的作品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郭沫若在《英诗译稿》中所选取的诗歌都是“英美文学中平易,有趣的,短的抒情诗,是早有定评的世界著名的部分诗人的佳作”(《英诗译稿·序》,成仿吾)。因此《英诗译稿》中所译的诗歌几乎都是对春天的歌颂和向往,以及对人类原始生命活力的追寻和灵魂的拷问式的诗歌,如“青春的热情尚未衰逝,愉悦的流泉但觉迟迟,有如一道草原中的绿溪,静悄悄地蜿蜒着流泻。……/当快感失去了花时和吸引,生命本身有如一个空瓶,当我快要临到死境,为什么退潮更加猛进”的诗句。(妥默司·康沫尔《生命之川》,《英诗译稿》)这何尝不是久经情绪压抑渴望自由生活的郭沫若的典型心声呢?
《英诗译稿》在郭沫若生前并没有出版,就内容而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没有出版的可能,它成了郭沫若为数不多的一部生前已经完成,但却没有出版的著作。如果从翻译的方式、心境和作品的选择来看,其实郭沫若翻译这部作品的初衷也许本就不是为了出版而译的。郭沫若之前所翻译的作品大多是有目的性的,或为学习而译,或为生活而译,但是《英诗译稿》可以说是为内心而译,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到《英诗译稿》中诗歌的翻译“几乎都是留在原文空白处的手迹”(《郭沫若画传》,蔡震著),现在在1981年版的《英诗译稿》的插图中清晰地看到郭沫若译此诗歌的手稿形式,在原诗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汉语译文,时而涂改,时而增删。这种随感式翻译的方法更加凸显了郭沫若此时的心境,那就是渴望创作的冲动,渴望情感的抒发,渴望青春的重现。这何尝不是一次再创作呢?正如译稿中所译到“我的灵魂是阳春,踊跃狂饮爱之醇;万事万物皆有情,渴望,缠绵理不清”。(《灵魂》,约翰·格斯瓦西,《英诗译稿》),这不正是“五四女神”时期诗歌创作中对青春的颂扬,对生命的赞叹重现吗?即使是已年迈的郭沫若,内心中永恒的青春激情也不自觉地流露而出。
毕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都历经了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洗礼,对真与美的追求已经内化为他们灵魂的晶体,即使在恶劣的外界环境挤压下,一旦有了可以奔突的缝隙,这些晶体便会喷发而出,这也是如郭沫若、老舍等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依然有着经典作品存世的缘由吧。
前海西街18号
一个复杂灵魂存在的郭沫若
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郭沫若当然也并不例外,复杂性伴随着他一生的选择,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晚年岁月中的复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前海西街18号居住的15年中,他既有过挥斥方遒的豪迈情怀,也有过内心彷徨的低回苦闷,既有过与友人诗词唱酬的文情雅趣,也有过痛失爱子的悲哀无助。
郭沫若纪念馆内悬挂了很多书画作品,有傅抱石赠送的巨幅山水画《拟九龙渊诗意》,也有郭沫若题字、傅抱石画石、郁风画花、许麟庐画鹰合作完成的作品。但在众多书画作品中有一幅最为独特,这就是悬挂在郭沫若书房西墙的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这幅作品原为郭沫若专为井冈山修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请毛泽东书写的。这幅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现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上所刻写该作品中的“鉋”改为了“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65年7月1日郭沫若到毛主席旧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黄洋界哨口等处参观,适逢该地正在修建纪念碑,于是郭沫若便答应了请毛泽东手书《西江月·井冈山》后镌刻在上,于是便有了这幅字的由来。郭沫若得到这幅作品之后,第一时间便发现了“鉋”和“炮”的差异,并请毛泽东将此字修改了过来。
此后郭沫若还专门给井冈山负责同志就这幅字写过一封信,信中主要强调:
请照碑式勾勒,并且适当放大为荷。
如以主席原式,则当成横披形,已建立碑又须改建。如何之处,请酌量处理,寄件收到后,望回一信。
如果从郭沫若一贯的性情以及他作为书法家的禀赋来讲,其实将“鉋”写为“炮”也无可厚非,但是郭沫若还是坚持让毛泽东将“鉋”改为了“炮”。通过这一字修改的事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郭沫若此时非常复杂的情感,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沫若晚年对于毛泽东亦友亦神的复杂情感。毛泽东作为自己诗词唱和的多年挚友,郭沫若是真诚相待的,而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郭沫若也是真心崇拜的,按照人的基本情感来看,挚友和领袖的关系是很难兼容的,甚至来讲是矛盾存在的,正是这种矛盾性形成了郭沫若一生中最复杂的存在,但也是真实的存在。1966年5月,“文革”已经开始,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郭沫若不会看不到这一切,也不会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这种时局的变化是他凭一人之力所不能左右的,也是改变不了的。郭沫若晚年在如此复杂情感支配下的存在,这何尝不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情感的集中体现呢?
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郭沫若书房书桌的案头摆放着他誊抄的两个爱子的日记本,这更是他在耄耋之年复杂心理的呈现。即使是再谨慎地处事,郭沫若在“文革”之初也还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1967年4月,郭沫若在部队服役的年仅23岁的儿子郭民英在苦闷中辞世,1968年4月,才华出众的儿子郭世英也惨遭造反派非法绑架直至死亡,也仅26岁。这样的丧子之痛,对于他是多么大的精神打击啊!可以想象每天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后,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满含热泪抄录已经逝去亲人日记的悲情场景。他每天用工整的小楷字体一页一页地抄下来,共抄录了整整8本,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在这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中,任何的努力都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任何的挣扎最终都会被无情地泯灭。这种无声的抗战更加凸显了郭沫若此时复杂内心的存在。
由此可见,晚年的郭沫若是复杂的,但是我们对他的认知却是简单的。在单一对错判断的支配下,晚年的郭沫若留给世人更多的叹息和不解,而在这样的判断中也忽略了借助对晚年郭沫若复杂性的学理性分析,去探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展道路的宏观考究。其实郭沫若正如同一枚标本,通过他复杂性存在的解剖,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便会清晰可见。
前海西街18号的秋天依旧美丽如画,落满一地的银杏叶将这个院落装点得格外具有诗意。那尊银杏树下的郭沫若雕像一直注视着远方,他仿佛是在思考,又仿佛是在述说,思考着曾经一段过往历史的现场,诉说着一段青春永恒的追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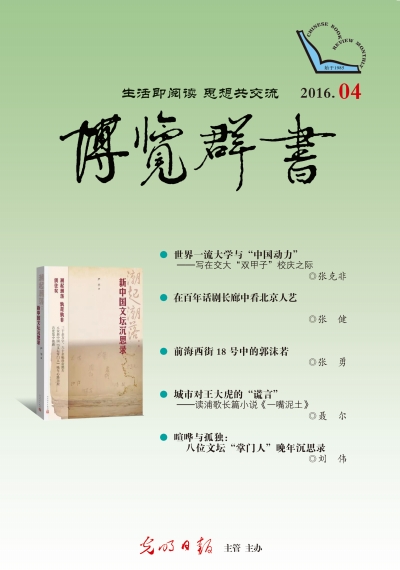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