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秋,郭沫若创作了第一篇白话新诗《死的诱惑》,从此后他正式登上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他以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创作出了《女神》等名篇佳作,树立了革新中国的“凤凰涅槃”精神,他以“借古喻今、借古讽今”的创作思想,赋予了屈原等中华历史名人崭新的时代意义,表达出了强烈的革新精神。他还在历史、考古、翻译、书法等领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学者以及政治家,郭沫若的各种成就早已见惯于世。近年来,随着译介学在中国的发展,郭沫若的翻译成就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屡开风气之先,却未必众人皆知。事实上,郭沫若在诗歌翻译领域中保持着数个“第一”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翻译大家。
··Ⅰ··
郭沫若是第一个将泰戈尔诗歌翻译成集的中国人。
1917年,郭沫若辑成《泰戈尔诗选》汉英对照本,此选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诗歌汉译集。我们今天普遍认为,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为泰戈尔翻译第一人,但他到1922年10月才出版《飞鸟集》,迟至1923年9月才又推出《新月集》。相较而言,郭沫若的译诗集比之至少早了五年。
1915年前后,郭沫若开始接触泰戈尔诗歌。郭沫若1936年在和蒲风谈诗时说:“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当民国四年左右即已看过他的东西,而且什么作品都看:如像Crescent moon(《新月》),Gardener(《园丁集·恋歌》),Gitanjali(《颂歌》),The Gifts of Lover(《爱人的赠品》),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伽彼诗一百首》),The King of Black Chamber(《暗室王》——剧本)都已读过。”郭沫若在1915年前后大量阅读了泰戈尔的诗歌,算是较早接触泰戈尔的中国人,但却难以断定他是所谓的“最先”或“第一个”。因为早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四首,陈自拟题目为《赞歌》,由此拉开了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1917年,郭沫若迫于生计开始翻译泰戈尔诗歌。我们往往从时代需要和民族情结等角度出发,去考证诗人的翻译动因,但其实很多翻译源于非常私人化和世俗化的目的。郭沫若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便是因为经济的短缺:“在民六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可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就连泰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便碰了钉子。”郭沫若说是“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表明其中很多译诗是在1917年前完成的,而其所说的当时国内还没有人知道泰戈尔明显有误。泰戈尔1913年因《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诗人,其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迅速跃升,随后有很多中国人开始阅读并翻译这位印度诗人的作品。不管郭沫若是否在1917年印刷出版了泰戈尔的译诗集,不管他是否最早走近泰戈尔的中国人,但其作为早期中国泰戈尔译介先行者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喜爱和崇拜之情不仅溢于言表,流于翻译,而且还体现在诗歌创作中。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坠入泰戈尔诗歌艺术境界中难以自拔,他曾回忆说:“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突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指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等——引者)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淡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郭沫若名诗《凤凰涅槃》受泰戈尔诗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他创作《岸上》时直接引用了《吉檀迦利》中的四行诗;而且其名作《天上的街市》也与泰戈尔戏剧《春之循环》中的一首诗歌相似。通过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郭沫若所受的影响和启示是深刻的,他回忆自己作诗经历时总是这样说:“我短短的作诗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在此不妨逆流而动,做如下设想和推断:如若郭沫若当年具有出版的资本和门径,且国人当时对泰氏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中国的泰戈尔翻译历史将会是另一种面貌。
··Ⅱ··
郭沫若是第一个完整翻译并出版《鲁拜集》的中国译者。
鲁拜诗在中国的翻译开始于五四初期。胡适1919年2月28日翻译了两首鲁拜诗,收在我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中,他于是成为第一位翻译莪默伽亚墨作品的中国诗人。1924年11月,徐志摩重译了这首诗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也是中国现代译诗史上首次就一首诗的翻译出现多个译本的现象。徐志摩之所以会重译鲁拜诗,原因并不在于他怀疑胡适的翻译能力,而在于他对诗歌翻译的独特理解,即诗歌翻译只是翻译原诗的内容,至于译诗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则因人而异,同一首诗歌的不同译本反映的并不是译者能力的高低之别,仅仅是译者艺术风格的个性化差异。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新月派”诗人朱湘选译了《鲁拜集》的部分篇章,据罗念生整理的《朱湘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介绍,朱湘从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中选译了其中的第59-73首,共计15首鲁拜诗。朱湘的译诗严格遵守“鲁拜诗体”的形式要求,第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可以相对自由而不押韵,是五四前后中国现代译诗中形式感最强的译作,体现出了这位新格律体诗人在诗歌翻译方面的形式自觉意识。
郭沫若译文的出现标志着《鲁拜集》的翻译开始走向成熟。郭沫若于1922年完整地译出了《鲁拜集》中的101首诗,以《莪默伽亚墨的诗》为名发表在1922年10月的《创造季刊》上,他根据的版本是英国人菲茨杰拉德英译的《鲁拜集》第四版。1924年,郭沫若以《鲁拜集》为名,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单行本。闻一多读了郭沫若翻译的鲁拜诗之后写了《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发表在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上,该文肯定了菲茨杰拉德的译诗因为语言具有诗性而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同理,他希望中国的译者在译诗语言上同样应该符合中国诗歌的审美特质,以保证译文的文学性。
《鲁拜集》不仅是全世界翻译版本最多的诗集,而且也是翻译持续时间最长的作品。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有诗人在翻译这部不朽的古波斯作品。但无可否认,郭译《鲁拜集》既是我国现代翻译史上第一本完整的译诗集,也是第一本以新诗形式译出的诗集,更是中国众多《鲁拜集》译本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本集子。
··Ⅲ··
郭沫若是第一个出版雪莱诗歌汉译集的译者。
在西潮涌动的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译介西书的繁盛局面,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在翻译领域彰显出鲜明的特色。
作为创造社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对雪莱的诗歌情有独钟。我们将创造社刊物发表的译诗统计如下:郭沫若和张闻天翻译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103首诗歌;郭沫若和成仿吾翻译了英国诗人雪莱和葛雷的10首诗歌;郭沫若翻译了德国诗人歌德的3首诗歌;穆木天翻译了法国诗人Alfred de Vigny和维勒得拉克的3首诗歌;N.C翻译了日本诗人上野壮夫和森山启的2首诗歌;穆木天翻译了比利时诗人万雪白的2首诗歌;此外还有郭沫若翻译的1首没有注明国别的诗歌。单从数量上看,除去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100首短诗外,就算雪莱的9首诗歌作品居多了,明显地表现出对雪莱的偏爱。
1926年3月,郭沫若翻译的《雪莱诗选》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雪莱诗选》不仅是郭沫若翻译文学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最早的雪莱诗歌汉译集,郭沫若连同雪莱一起被文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部划时代的译作除书前的《小序》和书尾的《雪莱年谱》外,包括《西风歌》《欢乐的精灵》《拿波里湾畔书怀》《招“不幸”辞》《转徙》《死》《云鸟曲》和《哀歌》等8首诗歌,基本上是郭沫若当年发表在各刊物上的译诗合集。
上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他与雪莱的情感灵犀让人叹服。1923年,郭沫若翻译雪莱诗歌后写下了如下感言:“男女结婚是先要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若不是郭沫若对雪莱诗歌的强烈认同,便不会有如此“浓情蜜意”的译后感。
如果说郭沫若翻译泰戈尔诗集是为了渡过经济难关,出于现实生活的压迫所致,那他翻译雪莱的诗歌则是超于现世的审美需求,也正是二人精神和情感的契合成就了《雪莱诗选》,成就了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的第一部雪莱诗歌汉译集。
除以上论述的内容外,郭沫若还在日语文学、德语文学和俄语文学翻译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有些译作至今依然无可取代。从翻译的角度去审视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我们自然会看到他鲜为人知的文学面貌,也易于从时代语境出发去探视特殊时代的文学风气和思想动态。总之,郭沫若的翻译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翻译了如此众多的经典文学作品,更体现在他与同辈学人们开创的优秀翻译传统,后者也算是郭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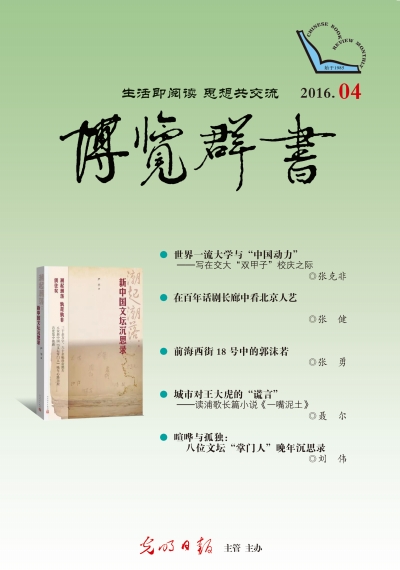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