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初,暑假刚刚开始,第四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沸腾举办。作为“书香江苏形象大使”之一,我与南京大学知名校友、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叶兆言先生等有了一次夜步金鸡湖北岸的经历。回到南京后,江苏城市频道踪迹而至,请我向观众推荐一部好书,我脱口举荐的就是他的《陈年旧事》(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陈年旧事》仅有11万字,但视野颇宽,涉及陈三立、李瑞清、蔡元培、孙立人、林虎、陈绍宽等48位以上的民国早期闻人、要员、名士,可以使读者略窥这些活动于文化、教育、学术、政治、军事各界的人物,究竟是如何随缘率性地为人处世,或治学做事的。作者在自序中说:“我是个喜欢动笔的人,写什么都觉得津津有味,都能自得其乐”,因此在往日所写《陈旧人物》(上海书店2007年版)似乎还能受到读者欢迎的五六年之后,又写作了这本《陈年旧事》。
他说,所谓“陈旧人物”,既表示书中所及人物之“陈”与“旧”,也试图“陈列”并“陈述”下那些似乎“老掉牙”的近现代文坛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林琴南、严复、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齐白石、张大千、吕叔湘、苏青、张爱玲等,书中诸如“林译小说以情动人,严译著作以理服人……就思想启迪而言,严译要比林译更有意义。林译和严译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绝唱,是桐城派古文喘的最后一口气”之类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学识与见识。作为《陈旧人物》续集的《陈年旧事》,“以人叙事,以事论人”,显然承袭并发扬了这种风格。但其取材已不再局限于文化界人士,诸如“从为党国效劳的角度看,桂永清只是(军人)楷模,杜聿明则是不折不扣的(战地)劳模”之类的言论,也多有放谈。
纵览全书,民国名士的掌故、闻人的轶事、要员的事功,显然是作者的关注点,也是读者的看点所在。诚然,以作者博闻强记的腹笥,出之以人物比较的思路,亦庄亦谐的文笔,该书可谓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兼具,但我在此种可读性之外,独独致敬于其文章的耐读性。
他把柳诒徵(1880-1956年)视若“旧式文人标本”加以分析,指出柳氏大鲁迅一岁,“都是少年丧父,都是在母亲影响下成才……(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容易让人早熟,更容易让人发愤”,可谓只眼别具,耐人寻味。他进而指出鲁、柳之间的根本不同在于,“一个是新文化激进代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另一个是旧文化保守典型,永远留守时代末端”,并分析道,“五四”以来的“新派历史学家,做学问在于敢于疑古,理论立足点是科学和实事求是。柳诒徵是‘信古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反对疑古,对古代经典有十分坚定的信仰,有宗教般的热情……他们相信古代圣人总是不会错。往好里说,这种态度是从一而终,往不好里说,尽管传统功力深厚,但难免抱残守缺”(《柳诒徵:旧式文人标本》),又是泾清渭浊,是非分明。
他论胡适(1891-1962年),特地从其被国人呼为“胡博士”,而实际上当年以学农科名义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官费留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859—1952年),其实并没有申请什么学位的“旧闻”说起,旨在说明他的学问与其为人和书法一样明朗而浅白,似乎无甚“文化含量”,但“胡适无疑是20世纪最有文化的人,他的一些想法,在今天越来越有意义。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学问……容忍比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容忍‘异己’,才可能会有真正的自由”,从而认为“自由和容忍让胡适变得博大”,“他投身政治,涉足官场,都不成功……是政治和官场对不起他”(《胡适:别看学位,看学问》),也可谓琵琶反弹,别有怀抱。
他评价杨宪益(1915—2009年)是“最令人称道的富二代”,留英六年,娶得英国美人归,而其人生“最优美的乐章”,却发生在夫妇二人共度自1937年抗战始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患难期,“他们十分恩爱地一起度过了60年,经历各种风雨,见证时代变迁,‘文革’中一起坐牢受难。他们的儿子饱受迫害,最终因为精神失常而自焚”,“他晚年的种种行为,尤其值得后人称赞。”作者最后检讨说:“我自小受阶级斗争教育长大,记忆中,总觉得穷人就是好,富人一定很坏。渐渐书读多了,才明白,穷人和富人都有好有坏,没必然联系。用‘好人’来评价杨宪益有些苍白,也无力,然而又是地道的大实话,绝对担当得起”(《杨宪益:最令人称道的富二代》),可谓论世知人,意味深长。
综上可见,作者的人物随笔,善于细察微枝,关注末叶,敢于从前因后果中寻绎事理和物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见识,或澄水清流,或拨云去霾,从而以发人深省的文字,来增广读者的历史知识和社会见闻。而所谓“耐读性”,则贵在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精神”地阐隐发微,贵在随机发表有感而发的个人新见,贵在行文中的微言大义,并以画龙而点睛的手法,让读者尽享开卷有益、读书得间,乃至掩册成思的接受快感。
作为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硕士,作者对于南京尤其是校史人物,特别是曾在其母系执教的老教授故事,情有独钟。他在《陈三立:虎子无犬父》一文中说:“1903年,散原老人曾担任过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总教习,又称总稽查。三江师范后来改名两江师范,又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再改名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最后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因此,说起南大的老校长,似乎不该忘了提一提这位散原老人。”但作者言论的精彩,其实不在此开卷第一文中。且以浏览所及,撷取数段文字如下:
李瑞清成了清道人,客居上海,卖字为生。散原老人不当官,诗越写越好。清道人辞了官,字也越写越好。他们晚年都成了普通老百姓,没有大富大贵,名声却越来越响亮。作为地道的中国文人,被迫离开仕途,脱离官场的轨迹,实属人生之不幸,然而对于诗歌和书法史,又是不幸中的大幸。(《李瑞清:一代非著名书法大师》)
20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有一大帮名教授,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是汪东先生。我一直觉得好奇,想不明白他何德何能,凭什么来驾驭手下的那些教授……年代隔得太久,我也弄不太明白汪东的学问水平,反正那年头,即使一个没学问的人,跟今天有学问的相比,仍然非常有学问。(《汪东:革命、当官、学问、书画都不误》)
听过胡小石课的人,都说他讲得精彩,形象并且生动,古风犹存,没有多少理论的枯燥,听过一遍就不会再忘。不仅擅讲唐诗,讲楚辞,讲诗经,讲文字学,讲书法史,讲佛典道藏,无不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胡小石:“不务正业”的国学大师》)
汪(辟疆)对清诗评价相当高,认为是清文学史中的高峰,而水平最高的又是晚清诗,其成就远在宋诗之上。一个老先生不薄今厚古,很容易受到年轻人欢迎。汪辟疆写《光宣诗坛点将录》时,被点到的一些诗人还健在,成了大名士,有的身居要位,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文学风气正处于剧变,“五四新文化”才是当时最强最大的文化潮流,他的研究注定不可能变成显学。(《汪辟疆:给别人排名,自己却被忘了》)
陈中凡一生都信仰“三书”和“三不”。所谓“三书”,就是前面说过的读书、教书、著书。所谓“三不”,是不做官、不纳妾、不抽烟。这是他参加蔡元培创立的“进德会”时的承诺,后来又发展为“新三不”,即不做官、不入党、不接受任何人的津贴……太太识字不多,是个半文盲,这丝毫不妨碍婚姻圆满。夫妻双双长寿,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陈太太活到九十三岁,她过世仅几个月,陈先生便也告别了这个世界。
(《陈中凡:文人的“三书”和“三不”》)
从《陈旧人物》到《陈年旧事》,积篇成书,显然非数年而能功成,因此,日积月累的读书,设身处地的思考,风晨雨夕的动笔,乃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任何一个作家乃至学者在笔墨上取得成功的秘诀,岂有他哉?
正如他说:“通常我们喜欢说书香门第,说贫寒子弟,都是为了解释一种结果,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功名呢,因为他能够刻苦读书。书香门第,家境贫寒,都是正面形象,都是成才原因。”(《李瑞清:一代非著名书法大师》)他曾表示:“我是个喜欢读闲书的人,乱七八糟的书看多了,对胡适的认识就有变化”(《胡适:别看学位,看学问》);他指出:“王伯沆批《红楼梦》,前后共批了20次,历时24年,共批了一万两千多条,见解独到,完全可以与金圣叹批《水浒》相媲美。因为这本书,我终于明白,当年(自己)不喜欢《红楼梦》,既和年龄有关,也跟学识有关,当然更与自己读得不认真不无关系。一本书随便翻一下,与静下心来仔细品读,完全两回事。”(《王伯沆:活在民国的六朝人物》)
“我喜欢胡(小石)的书法,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精神,正是我在创作中想努力表现的。我的很多小说,都沐浴在这幅字(胡先生所书长卷片段——引用者注)的光辉照耀下,感到困惑的时候,写不下去,就会回过头去,看一看那字,看一看潇洒流动的线条。”(《胡小石:“不务正业”的国学大师》)由叶先生的这些文字,可知其读书、写作生活之一斑。
在《陈年旧事》中,民国的知识女性虽然不是作者的关注重点,但也不是毫无涉及。他介绍蔡元培长女蔡威廉(1904—1939年),是中国有数的几位最早向西方学习油画的女画家,为她因“产褥热”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蔡威廉:艺术家活得长很重要》);他推介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曾昭燏(1909—1964年),她与族曾祖曾国藩相差99年,彼此所处时代完全不同,但“良好的家教遗风还在”(《曾昭燏:曾国藩家族里的考古学姑娘》)。在《沈祖棻:斜阳里的春愁》的篇末,他似有无限感慨地写道:“天还是那天,地还是那地,文化已不是那文化……失望总是难免,无可奈何花落去,旧渐渐远逝,新却没有就来。”——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他为才女“沈斜阳”在当代的不可复见所发表的感想,但也不妨理解为,作者是为旧学旧文化旧风尚所凝结的“民国范儿”所唱的一支挽歌。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叶兆言在该书自序中特意引用这一唐诗名句,应该寄托着他一番浓厚得不易化开的怀旧情愫,而借故讽今以为镜鉴,或正是作者持续踪迹和追思民国人物命运的终极关怀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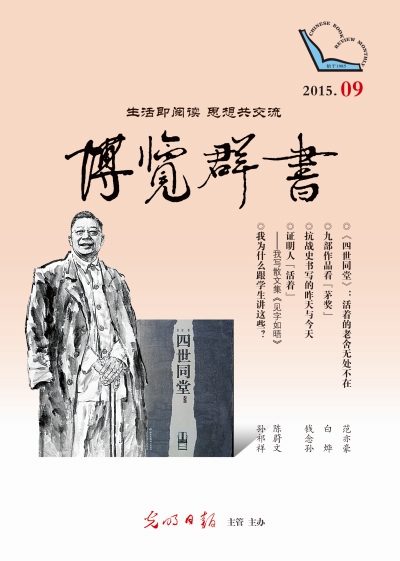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