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还有两天的时间,我收到了一些郝景芳的小说稿,都是中短篇。
这位科幻作家的作品以前没有阅读过,虽然在网上见过她的书《回到卡戎》《流浪玛厄斯》,知道她是《科幻世界》的作者,新概念作文出身,又在清华大学读过物理学和经济学博士,好友刘慈欣向我介绍过她,也推荐过她的作品。
随意浏览这些小说稿却很快让我正经起来,我打算写点阅读札记,代表我初读郝景芳的印象。然而直到飞机起飞,终究只字未动。基于我脑海里对于郝景芳小说的捉摸初具轮廓,我继续乐观的估计,评论可以拔地而起,所以云上才是写它的好时候。想到这里,我评论的题目就有了:《云上读郝景芳》!
并无疑问,幻想小说是人类小说的嫡传宗嗣,正如幻想是人类生而本有的灵智。换句话说,小说没有不幻想的,虚构就是幻想最低调的体现;而虚构,也就是小说艺术的核心基因和核心问题。
客观省视一干伟大的小说,其实都有面向神话、寓言和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图腾”或者“心灵考古学”致敬的意思,无非有的是通过对前辈文本的直接模仿,有的是通过戏仿、映射、象征、变形来完成。从这个意思上,郝景芳的这种尝试及其坚持同样是古老的、主流的——我现在判断一种小说是否主流,已经不爱从当下固定的一个潮流、一个圈子的观点来想见,而宁愿重新考量其在整个文学传统中的位置和它在未来趋势中的可能性。——摆脱了时髦和圈子化的训导,便于让人回归常识,依傍自己作出更为真实的判别。
事实上,幻想小说并非是站在狭义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对立面存在的,它比现实主义小说更古老,并时刻在成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补充。郝景芳式的幻想小说,在我看来,就是(当下)现实主义的重要的补充,更准确的说,她延伸了我们的现实思考——文学的、哲学的和美学的。
一个总的观点是,郝景芳的这组作品就是一种有趣的新寓言小说。无论篇幅上的“长枪”或者“短炮”,每每都有一个隐喻的中心,在寄寓我们的共同处境即“存在”的模式。作为寓言,短小精悍甚至就是一个特征,传统的寓言便如此,比如《伊索寓言》。这也可以局部用来说明郝景芳这里的半数作品为什么那么短。
比如《从前有一个小孩》,短不及千字,大意却非常明晰。它以拟人之法说明我们与“羞怯”这一人性特质如何的“始乱终弃”,以此悼念某种人性原始美德之不可得,即其失去的惆怅伤感。——“从前有一个小孩,从小有个玩伴叫羞怯。羞怯长得柔柔小小,总是被他揣在口袋里。没人的时候,它露出头来陪他一起看世界,有人的时候,他就把它塞回口袋。他不喜欢让别人看见它。”——小说就是这样开始交待“羞怯”的孱弱性格,却也同步印证其珍贵,即所谓“且行且珍惜”的原委。小说为了生动说理,形象地设计出一组与那个“小孩”(比喻人类)成长及其羞怯失踪的语词形象,他们是:“恭维”、“嘲笑”、“胆大包天”和“谦虚”,作者依靠对这些词义(性格)特点与消长关系的准确把握演绎出一场人生历程上的三幕剧。
与古老的寓言相同,作者出手成篇的字里行间,赋予了短篇一种童话般的气质。换言之,一些卡通模样的形象也将从读者的阅读中油然而生。郝的小说具有此类视觉的生成性,这也是我在其他合适的地方需再次阐述的另一重点。
当然,郝景芳的“新寓言”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寓言的仿拟,富有现代感的意识和文字洗礼让她从中超越出来,一点点重现她“寓言”式表达的新质。《我的时间》是递进一步的做法,同样不长,不及千字,但故事和人物的设置不至于《从前有个小孩》那么抽象、扁平,更显游刃有余的虚构之力。——“我偷时间为生。我把时间和别的东西打包卖出去,赚取银子。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因此我只能偷一些。”——奇幻的开头调动了阅读的乐趣,成功地为这个短篇奠定了故事的奇妙可能,以及“偷时间”这个概念所意味着的一切寓意谱系——所有关于“时间”的哲学、物理学和文学文献都整装待发,于瞬间集结,开启了阅读者广阔的知识背景。虽然,下文并不一定运用到所有的人类关于“时间”论述和想像的文本,但“偷时间”这个开始就使“此刻”具有拥抱“存在”的契机,这同样说明郝的小说何以是“寓言”小说的原因。
这个小说颇为有趣地推动着“我”偷取时间在人间买卖的成功勾当,缩影了人的一天、人的工作和生活原理及其伦理解释,但将它建构出荒诞感的卖时间和赚时间,形成其强烈的寓言效果。而后那个“一见面就知道我是谁”(而常态中的人们对我毫无察觉)的“女孩”,与“我”展开了富有悬疑的对手戏,使得小说更像小说,丰富了寓言的现代感和文体变异。当我最终成为用每天的谎话赚取她提供的百分之一千的利润回报终于获得了无限时间的囚犯时,我彻底意识到败给了她,因为她其实是个买卖灵魂的人。——作者由此提示我们,时间固然奇妙,但对于人类而言灵魂却比之更为贵重易失。这和她的《从前有一个小孩》一样,证明着郝景芳的人文主义立场,也可以说她写的小说依然保持着对人类基本价值和美德的守护,反之以强烈的寓言感向现实中人性的异化和底线的沉沦报以结实的批判。
怎样使小说更成为小说,而不至于被人诟病为未能成势的“散文”,我想,应该是郝景芳要力图突破和值得思考的文体问题。换句话说,既不失其“新寓言”的立场和特色,又吻合或者说发展出自己的小说厚度,是郝氏小说的当务之急。《阿米和阿豆的故事》是一个升级版,企图弥补这种争议。
我个人很喜欢《阿米和阿豆的故事》,认为这越来越接近于“无痕迹”又富有现代小说滋味。这个小说呈现出向卡夫卡之后的文学传统,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卡尔维诺致敬的意味,又嵌入了准中国语境,其隐喻和反讽的肌理正在向深度之维和现实世界种植。阿米和阿豆是如此“二货”的一对同胞兄弟——“他们生下来就只懂快乐,不懂忧愁。造物主没有赋予他们疼痛与忧愁的能力。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生来就是要挖墙的。从一边,到另一边。他们很喜欢挖墙,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唱:我是一个挖墙工,挖墙本领强;我要把那伟大墙,挖得很漂亮。”——“挖墙工”,这又是一个与“偷时间”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新词和新概念,此后所有关于这对快乐的二货挖墙工兄弟的故事都呈现着狂欢化叙事的调子,成为具有庞固古埃(拉伯雷《巨人传》)气质的形象,他们的所谓“劳动”和这种劳动的冲动激情、他们与警察的遭遇、他们最终的死亡,就是一种底层“二货青年”的可能性命运的写照。
在关于“挖墙”这件事情,郝景芳写得非常到位、传神:
阿米和阿豆知道,被警察抓住是会杀的。他们有很多兄弟就被抓住了。
“不行,我就要抓住你们。”小警察又说了一遍,但还是没有动,“你们挖墙是有阴谋吗?”
“不是啊。”阿豆说,“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阿米和阿豆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曾经看到过很多很好看的东西,有些他们都说不上是什么。每次把墙凿穿之后,待洞口的亮光透进来,哪怕还没出去,心里就一阵激动。他们心中没有词汇或合适的记忆来描述那种感觉。就是期待着发生什么,期待着,紧张着。
他们从洞口滑出去,沿着隧道通路滑出最后的圆圆的亮光。然后他们会惊叹地叫起来,无论看到什么。他们看到过大海,绯红色朝霞染过的天空和海面,翻滚在脚下,变幻各色光芒。他们掉进云层里,被颠得上来下去,能感觉云的撩逗,惹人发痒。他们有时候被夹杂着带到音乐隆隆的巨大房间,鼓点敲得他们心脏狂跳,周围人亢奋地扭来扭去跳舞,用屁股把他们撞来撞去。落入战场的时候,他们会满身泥土,卡车沿飞奔的小巷向远处射击。有时候他们哪儿也不去,就飞在天空中,在气流中波动,俯瞰下面漂浮的一行行巨大的字。那些画面中时常有错,他们见到了就想去改过来,有的地方能改,有的不能改。
……
挖墙工阿米与阿豆所谓的“随便看看”“有些他们都说不上是什么”等等等等,谁说不是“屁民精神”的传神写照?那种“挖墙”出去看看的“无目的论”具有非凡的现实主义根据。而“有什么好看的?”也就是为什么要挖墙出去看看,其本身所具备的自由精神尺度何尝不是美好的!只不过对于“二货”阿米、阿豆而言,冒险、猎奇、刺激、娱乐精神——“屁民爽点”——比冒犯和严肃精神更为重要,也因此,他们的死亡则更富黑色幽默与喜剧中小人物的尘埃般的悲怆。
不可否认,《阿米和阿豆的故事》语言也更加棒,令我想到当下另一些才气作家,比如马伯庸的短篇小说(详见马的短篇集《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可以说丰富了我们的作家序列和语言路径,他们在进一步综融经典文学语言、当代严肃小说语言和网络语言方面作出了独特和重要的尝试。这也是我只能在另一个合适的时间中想继续探讨的话题,兹不赘述。
这里最后想再说一篇的是《最后一个勇敢的人》。这肯定是郝景芳这组小说中最成熟的一篇,即不失其“新寓言”性而浑然让读者忘了寓言不寓言的一篇。可以让人浑然忘却其寓言的追求,是因为作者把“寓言”种植得更深了,沉淀在根部,扎稳于大地;此外,则是篇幅、叙事能力、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获得了发展,具有了根深叶茂、内外兼修得神形;而这篇,也就是“科幻作家”的“当行本色”所在,当然,一个固定名词有时候貌似准确却又恰恰不准确,如果作家的外延远远大于固定名词的一般认知,而作家又有野心地在综融几种传统的话。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克隆人普及的世界中,“自我”确认的哲学或者说人类学发展出现的挑战。在小说中,郝景芳赋予了它“独立个体主义”的概念,以克隆人的角度最终立论——仿佛一部新的《人权宣言》——
“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用大世界来判断,应该用小世界判断。”如果说这种来自克隆人的人权和自我认知似乎也不过是人类个体独立精神的拷贝的话,那么当老年的仓库保管员潘诺34号重申一个人的无数世代克隆意味着“我们都像一本书的拷贝,书才是意义。克隆体越多,你的世界越大。你可以经历永生永世”,则再次强调了克隆并不是目的,即便一种基因的克隆在这世上被剿杀,其关键之处仍然是尊重人类普遍的自由精神和人性觉醒,让人性不丢失是人(哪怕是克隆人)的终极使命,而不是技术的、专制的和其他的。所以,郝的人文主义情怀在科幻的克隆世界再次顽强自证,这一点,无疑是郝景芳小说的“正能量”和价值观。
当然,这么阐述会显得有点无趣,因为小说本身十分好看、可读,有科幻、有悬疑,类似美国式的优秀科幻电影,本身的影像感、即视感让我觉得这就是个不错的科幻电影的改编对象。对于这样的小说,剧透会被人鄙视,所以不在本文之中,看官自己上网搜去。
郝景芳整体上是特异的,于当下“左”或“右”的习见的小说脉络而言。我非常看好这样的小说,认为这就是我在期待和发现中的“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可能”,我甚至相信,这也是一种国际化视野下的期待。就目前郝景芳提供的作品来看,多少还不够数量和力量来做更强有力的证明,所以如果可以,请她考虑我们的感受,多多思考这中间的发展和问题。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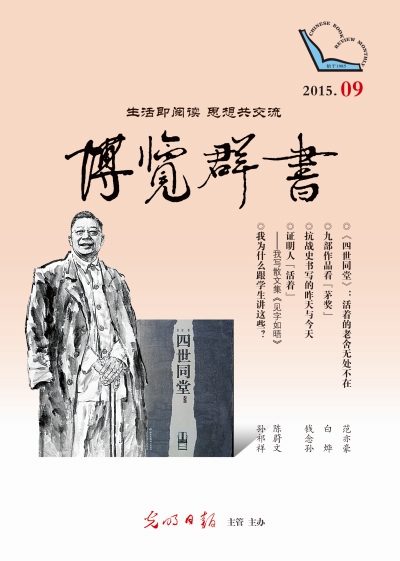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