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新中国工业摇篮的“老工业基地”,在时代变革中发生了巨变,昔日辉煌不再,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相对薄弱,投身工业题材创作的积极性和投身的优秀作者都非常缺少,甚至处于失语的状态。“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变迁给新世纪都市文学创作究竟带来些什么?当下作家在现代化工业文明进程势不可挡的今天,如何重新找寻都市文学创作的新的生长点,并以何种角度再现“老工业基地”的美丽梦想?
评论家:工业仍为宝贵的文学资源
“老工业基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曾缺少激情和想象。以都市文学创作的维度,追寻“老工业基地”诞生、发展、变迁的历史踪迹,是将书写现实与历史感结合在一起,思考的是新中国工业的兴衰荣辱,透过一个民族的工业文化在这片黑土地的发展历史,看到中国历史顽强的生命意志,也看到大批产业工人为生存与发展而斗争的壮烈与悲凉。《芒种》主编张啟智提出,迄今为止的工业题材作品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对“老工业基地”作出文学和哲学深度的生活体察、细致审视和现实思考、文化批判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面对今天社会的特殊的历史现实,为何中国作家对工业革命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深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指出,作家的生活基地都在豪宅里,要人中间没有作家,也缺乏深入基层的能力,所以能和这块土地相称的作品不多。评论家陈福民提出,今天谈论老工业基地,有很多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复杂的情感记忆,不是说要痛下决心割舍这些,而是应该看清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原来的历史记忆承载的文明记忆与现在的关联,关注文明的差异性和渐变性,这是很多作家缺乏的,我们很难从老的机器文明中发现新的东西,这是需要值得研究的。
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催生了新时期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改革文学”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现代化工业进程给“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给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都给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元素。
如何深化、丰富我们的都市文学,文学研究者贺绍俊提出两点:一是应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我们进入工业题材的文学资源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先进的阶级立场,才能进入到本质性的认识并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应该有一种城市立场,城市中承载着一种都市精神,如何以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文学资源去开拓都市文学写作,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从沈阳到辽宁,再到整个东北,真是工业题材的摇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从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起,可以看到工业基地和工业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比如邓刚的《阵痛》、肖克凡的《机器》,通过工厂的转型,写出了社会的演变。工业基地也是文学的沃土,希望作家们在这个领域深入进去,创作出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工业题材之作。
对“老工业基地”重大历史变迁的文学书写,需要放到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考察,放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发展态势中审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这些年工业题材的都市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辽宁、沈阳等地涌现了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是远远不够。现在谈到老工业基地的时候,作家们还是比较习惯于按照历史,带着一点历史悲情。尤其是涉及作家个人经验,这种历史的悲情和个人的感伤联系起来了,这都是有道理。“但我也同时觉得,应该注意到,历史就在痛苦的蜕变中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表现工业题材的时候,应该尽量全面看待、掌握它,这对于工业题材、都市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很重要的。”
作家:工业题材已离时代远去
20世纪80年代末,天津作家肖克凡的小说《黑砂》和《最后一个工人》被改编成话剧上演时的轰动和好评似乎恍若隔世。时光流淌到2012年,有人将他的工业题材小说推荐给影视公司时,专家论证的结论却是“工人阶级不存在了,拍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有谁看啊!”这样的结论令肖克凡受到震动:工人阶级竟然不存在了。难道真的都变成工薪阶层了吗?
在工厂待过25年的作家蒋子龙,曾经写出《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等一系列掷地有声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他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已经不复存在。在他看来,当年所谓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像“天津重机”一样淡出公众视野,应该重新考量和界定。
蒋子龙觉得,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题材”概念是指关注经济核心、经济脊梁的作品;还有一种泛工业题材,当下很多作品都掺合一点工业内容。工业品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身边,比如有人做心脏搭桥手术,他的心脏是半工业心脏;写灯红酒绿的作品,也是在工业氛围中。现在,恐怕工人的身份也变得多重。农民工是工人吗?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并非完全具备工人的本质。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也最缺乏工人形象,缺乏能够触及工人的“魂”的作品。
“现在一切核心的核心都是GDP,”蒋子龙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太潦草了,缺乏核心工业,核心技术完全轻而易举从国外购买代替了。好的工业工人凤毛麟角,原来一个强大的技术队伍都涣散了,而且没有再培养。他特别希望像农村调查一样,搞一次工业调查,多跑几个像造船厂、机床厂这样有代表性的行业,对中国目前的工业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以我在生活中了解到的现象和部分调查,到处都是粗制滥造。”蒋子龙说,就目前的多数状况,他对中国工业题材的创作不太乐观。不过,他去过太原重型机器厂参观之后非常激动。他对太原重机厂总经理说,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脊梁。蒋子龙说,自己还要写一部关注工业的作品,就写天津工业最好的时候。他希望用作品证明工业振兴的源头和力量。
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煤矿工人的刘庆邦看到,煤矿产业的手段在发生变化,手工变成机械化产业,木头支护变成钢铁的综合支护,这些不是他着重关注的,他更关注人的心理变化。他常常一个人深入到煤矿,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没有任何应酬,一杆子扎到底。有一次他去河北的一家小煤矿,发现那里还用骡子拉煤;他偶尔走走“关系”,通过朋友介绍深入到国营煤矿,住在矿工宿舍里,和矿工一起排队买饭。靠着这种扎扎实实的“接地气”,虽然离开一线,刘庆邦仍能准确地把握到现代矿工的心理变化。刘庆邦说,矿工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70%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希望写一部矿工群像的生活,写矿工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为此,他深入到郑州煤业(集团)公司,这里的大平煤矿曾在2004年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刘庆邦陆续采访了矿难后职工家属,关注他们怎么战胜伤痛,面对生活。
“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从农村到煤矿,从农民到工人有很大转变。刘庆邦说,矿工是特殊的生态群体,作业环境和任何行业都不同,看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狭小、黑暗的环境中,只有矿灯一点微弱的光亮。他们饱受水、火、瓦斯等灾害的威胁,但是,他们在黑暗中维护着中国的光明。”
现今有不少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只是文学界将它归为“打工文学”。肖克凡分析,如此归类的原因,是我们将如今在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称为“农民工”。“当年我16岁进厂学徒时,很多工人师傅也是进城做工的,他们的家庭都在农村,每逢春节享受‘探亲假’回农村家里团聚。那时候他们都是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今天却都叫农民工。”
“现在提倡市场化,假若市场不需要工业题材作品,它就很难振兴。如今市场需要娱乐,所以娱乐作品不用我们振兴它就欢蹦乱跳了。”肖克凡说,从普世意义讲,工业题材也是文学范畴,普通劳动者不应当被社会瞧不起,这个社会不是只有白领,还有蓝领大量存在。然而,由于蓝领生活缺乏华丽风光,不好吸引眼球,久而久之就愈来愈少了。所以,肖克凡说:“如果必须要我提个建议,这可能与文学无关,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适度尊重普通劳动者,不要放弃劳动光荣这个价值观。”
一个写作者没有忧患意识,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李铁说,这种意识注定了他的悲剧情怀,没有办法,工人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而只有悲剧才更有震撼力,才更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写工业题材的创作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家也参与进来。”李铁认为,工业题材处于边缘状态,有作家的责任,也有出版者的责任,通常认为这类题材的小说没有商业卖点,出版社不愿出这类书籍,连出版都困难,作家在写这类题材时也就会持迟疑和谨慎的态度了。恶性循环,工业题材的作品就越来越少。“我从来不认为有工厂元素存在的小说艺术质量会容易低,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元素更适合写出高艺术水准的小说。与众多的见解相左,我还认为以工厂为背景的小说更容易是现代性的,或先锋性的,如果把工厂里的一些生产片段或工人的生活片段写出来,不人为地强加故事,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想象其中会发生的故事,这就会是一篇或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对于如何才能振兴工业题材的文学书写,李铁提出,首先应该重视,出版和评奖都不应歧视这类题材;第二就是作者本身要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当代人都面临两个不同的窘境,一个是生存的困境,一个是精神的困境。一个写作者要从文学的角度正视这种状况的存在。我们的所谓“工业题材”写作不能只面对那些所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精神上的问题才是文学的问题,用文学的叙事来呈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所在,才是作家的责任。写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生活经验之上的,不了解当代工人的生活,只熟悉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老总们是写不好“工业题材”的。
振兴任何题材的文学书写都需要一个前提,作家曹征路认为,那就是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文化艺术积累,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传统,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这些东西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一点都不输给其他民族。中国有13亿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普通劳动者,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去为他们服务,而是去满足少数精英的趣味,去追求“与世界接轨”,这种艺术有什么前途?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曹征路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央电视台久违地喊出了“工人伟大劳动光荣”,青歌赛上奏起了交响乐《红旗颂》。是春江水暖?还是临阵磨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主流媒体这种改变还是令人恍如隔世感慨万千。他说:“一位远方的朋友告诉我,只有精神强大的民族,才能产生伟大的交响乐。我深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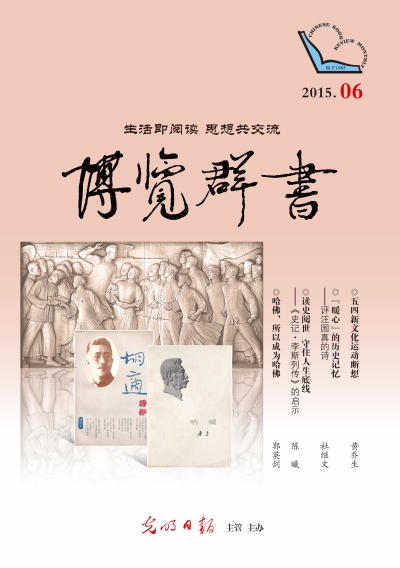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