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流行两个俗语:一是“上说天堂,下说苏杭”,作为江南典型象征的苏州、杭州,已经成为可与天堂媲美的温柔之乡;二是“天下九福,吴越口福”,江南物产的丰美,更是可以使老饕们大饱口福。
晚明江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大抵可以“风物闲美”四字加以概括:说其“风”,是指江南形成“时尚”之风,出现时尚人物,并进而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说其“物”,是指江南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工艺日精,并且出现了“物带人号”的现象,很多物品以时尚人物命名;说其“闲”,是指基于生活富足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江南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庶民百姓,无不带有一份闲情逸致的心境,追求生活的娱乐化,甚至出现了职业的“帮闲”与“女帮闲”;说其“美”,是指江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存在着一种追求艺术化的倾向。
风:“时尚”之风
晚明的江南,形成了一股“时尚”之风。时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响力则是“群起而随之”,形成一股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冲击波。可见,所谓的时尚,大多体现在“衣帽”、“字语”、“器物”等领域。在晚明,江南儇薄子的衣帽样式,无不更改古制,谓之“时样”。那么,什么是当时的“时样”服饰?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说明:一是浅面矮跟鞋,是当时的时尚穿戴之物。二是笔管水袜,应该说也是当时的时兴货色。
所谓俗语,就是一些市语,包括民谣、谚语、口号以及江湖隐语。晚明的江南,市语已经相当风行。曲中行语,大多轻佻,但当时南京的市语,却大多本于曲中行语,试举多例如下:肉麻——意思是说可羞,令人肉麻;摭——读为“者”,意思是说作态;水——意思是说虚奖太过;括——意思是说目挑心招。这些原本出自曲中的时尚流行语,在渐渐延及普通民众的过程中,最后更是“衣冠渐染”,亦开始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
无论是衣帽、字语,还是器物,其时尚的形成,通常倡自一人,于是在晚明的江南又出现了许多时尚人物。在晚明,文化人如果想成为一个时尚人物,则只能依靠他们的著作与行为。如果他们是首倡者,并引发一种群起仿效的效果,最后形成一种“时尚”,那么这些人就堪称时尚人物。在晚明,真正称得上时尚人物者,应该说只有李贽(以“卓吾”先生著称)、陈继儒(以“眉公”著称)、王稚登(以“百谷”闻名)、袁黄(以“了凡”先生闻名)、袾宏(以“莲池大师”著称)五人。除了李贽不属于江南人,其他四人均属江南人。
起于晚明江南的时尚之风,苏州、杭州应该说是当时最为时尚前卫的城市,为此形成了传播一时且又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苏样”、“苏意”、“杭州风”等专有称呼。
所谓“苏州样”,在晚明尚有一个相关的新名词,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当时的苏州人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凡是苏州人以为雅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四方之人所模仿;反之,苏州人以为俗的东西,四方之人也就鄙之不行。当时流行两个名词,这就是“苏样”与“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之为“苏样”;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所谓的苏意,应该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服饰时尚;二是“做人透骨时样”。改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走在时代前列,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
“杭州风”一词,显然也是晚明各地相当流行的新名词。晚明的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地有稀奇之物,某家有古怪之事,某人有丑恶之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亲眼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加以嘲弄。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杭州人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外面漂漂亮亮,里头却是空心甚至腐败,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在“杭州风”这一名词之下,事实上反映了晚明江南城市风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是讹言、谣传传播速度之快,这是民间舆论空间扩大的证据;二是城市风尚的虚伪,甚至作假。
物:“物带人号”与“物妖”
晚明江南物产,可用“丰美”二字概括。说其丰,是指江南物产丰富,品类繁多;说其美,是指江南物产,随四时节候的变化而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景。
在这些江南著名物产中,有些属于天然物产,而有些则属于经过人为加工或养殖之物。就天然物产来说,最为著名的当数萧山湘湖莼菜、松江鲈鱼。在晚明,所谓的西湖莼菜,大多来自萧山,尤以湘湖所产为天下第一,并与杨梅、樱桃,合称“三绝”。鲈鱼也是淡水产品中的至味。过去将莼菜与鲈鱼合在一起,称“莼鲈之思”,已经成为江南的象征。鲈鱼以产于松江的四腮鲈最为出名。明人诗句中有“门柳旧五树,江鲈新四腮”之说,即可为证。就人为加工或养殖的物产来说,最为著名的当数嘉定鸡、金坛鹅、上海顾氏露香园顾绣。嘉定鸡为三黄鸡,出嘉定南翔、罗店,尤以嘴、足、皮毛均为黄色者为上品,重数斤,能治疾。金坛鹅更是擅江南之美,饲养有专门的方法,色白而肥。至于顾绣,更是海内驰名,不但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且山水人物,也无不逼肖活现。顾绣在当时一直价格昂贵,尺幅之素,精妙者即值几两银子。
江南之物产,尚可与四时物候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如华亭人顾清曾经列出了“江南二十八景”,分别为梨花满放、梅萼盛敷、茶笋初肥、桃柳相媚、枇杷摘金、杨梅献紫、牡丹斗色、芍药繁粧、海棠晓睡、蔷薇昼香、芰荷新发、菱芡初尝、莼鲈正美、秫酒始酿、稻花成云、麦风如浪、鲥鱼薦鲜、紫蟹满膏、橙黄橘绿、蒲长苇茂、菊圃千名、杏园一色、松花成饼、桂子为浆、兰蕙列庭、水仙置席、莺啼春树、鹭映秋波。陆平泉在此基础上,再添菜花如缛、稻米如玉二景,正好构成江南30幅美丽的图景。
江南之物,其中最为引人瞩目者是“物带人号”现象的出现。所谓物带人号,是指一器一物,倡自一个时尚人物,并进而借助他的名头而成为一种时尚物品。若举其例,陈眉公堪称典型。从诸多史料记载可知,陈眉公每件事都喜欢创制新花样,人们纷纷效法,犹如宋人之号“东坡巾也”。譬如,眉公所坐之椅称“眉公椅”,所制之衣称“眉公布”,所喜之饼称“眉公饼”。至眉公所交之娼妓称“眉公女客”,已是可笑之至,但更有令人捧腹者,眉公曾制成一种便溺之器,器物底空,以便野坐,又被称为“眉公马桶”。
古玩、古董,是历代常见之词,人们崇尚古玩,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并不足怪。在晚明的江南,同样兴起一股收藏古董之风。嘉靖末年,士大夫在建造园亭、教唱歌舞之隙,兴趣间及古玩。如常州嵇应科、松江朱大韶、嘉兴项锡山等,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此外,南京则有姚汝循、胡汝嘉,亦以“好事”著称。此风间及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进而流播吴越之间,一些浮慕之人,亦纷纷收藏古董,自称“大赏鉴”。在这股收藏古董之风中,尽管董其昌最晚出,但名头最为响亮,藏家甚至以“法眼”称之,家中箧笥之藏,更是为时所艳。
按照一般的常理,玩好之物,理应以古为贵。但晚明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倒是颇令人瞩目,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这股好时玩之风,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的风气。于是,沈周、唐寅之画,文征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
闲:闲情逸致的心境
自明代中期以后,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社会上风行起来。晚明江南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晚明江南人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进而形成江南人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
闲情逸致的生活方式,归根结蒂还是要找到一种逗闷的乐子。这些逗闷的乐子,举其大者,包括谈禅说佛、蒲博之风、狎妓听曲、旅游消闲四个部分。喜禅悦是晚明江南士大夫的风尚。当时的士林名流如焦竑、冯梦祯、陈继儒辈,都好佛喜禅,有些甚至对佛学还有比较独到的研究,有著作传世。晚明江南的缙绅士大夫,同样视赌博为风流之举,并将赌博作为一种娱乐,成为他们闲适生活的一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常州一带,士大夫的赌风大盛。一些士大夫致仕归家以后,开设赌坊,赌徒藉此躲避朝廷的禁令。到了万历末年,更是出现了进士“以不工赌为耻”的奇怪现象。至于赌博的方式,尤其是马吊牌兴起于江南之后,自南而北,很快风行全国各地。狎妓听曲,也是江南士大夫风流雅致生活之一。在晚明,士大夫挟妓饮宴较为盛行。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所谓花榜,又称“花案”,其实就是选妓征歌。以南京为例,所评之榜或案,其说有“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等。江南的文人雅士对戏曲也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如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明人好游,尤以江南人为甚。人在自然界活动,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旅游人文风俗、景观。晚明江南人文风景最著名者,张岱认为有扬州清明、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无不按照四时节序的变迁,形成了一些全国闻名的人文风景。
与民间闲适生活相应,在当时的江南出现了一种职业闲人群体,此即清客、帮闲。其最为典型的例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清客店的出现;二是明代的帮闲,有男女之别,亦即除了男帮闲之外,尚有女帮闲。尽管清客、帮闲遍布全国,但还是以苏州、松江二府最为集中。根据《豆棚闲话》记载,苏州唱曲之人,分为“小唱”与“清客”两类:凡出名挂招牌的,称“小唱”。不出名荡来荡去的,则称“清客”。松江有一则“十清诳”的谚语,已将清客形象刻画得颇为生动,诸如:足蹬荡口鞋,身穿绵绸直裰,却衣身很长,甚至可以盖到脚面上,直裰的袖中带着时兴的汗巾;平常手头所拿,则是圆头折扇;日常使用的饮食器皿,亦颇讲究,用的是回青的碟子、宜兴的茶壶;他们识得一些骨董,学了几句魏良辅所倡的昆曲;见了“小官”,匆忙递上自己的名帖,甚至“老兄”、“小弟”的胡乱称谓。尽管无论从穿着打扮、技艺、社交等生活样式上刻意追求时尚,以示自己之“清”,但“不出夜钱沿门跄”这一句,显然已经道出他们仍然是游手好闲之人,甚至是百姓之大蠹,难逃其“诳”的面相。
美:生活的艺术化
在追求物欲与享受之后,晚明江南的生活风尚又开始趋于艺术化。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无非是藏画、藏书、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
在晚明的江南士大夫家中,通常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以资玩好”。还有一些好古之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册,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尤其是在书画的悬挂方面,更是有了诸多的美学要求。根据文震孟的描述,堂与斋因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堂尊严庄重,较为气派大度,宜挂大幅横批;斋较为小巧精致,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般人家无书,有一些书,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然在晚明的江南,图书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风。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但还是一种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
在江南杭州,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作为装饰。所养之鱼为红鲫鱼,俗称“火鱼”。其品不一,如鹤顶破玉、红颊白喙、牛鬣素尾、阳背阴腹之类,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的奇品,一尾就值千钱。养鱼之盆、盂,或为金,或为玉。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案上,有客人到来,“出相夸示,以为娱”。松江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也开始畜养“朱鱼”用来观赏,品类奇绝,一尾可值银一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总是布置一些与四季相配的瓶花,也即在胆瓶中插时花,藉此引类连情,境趣相合。以插花为例,必须按照居家的时宜及各类花种的性情,以独具的慧心,作巧妙的安排。在生活日趋富裕、闲暇日多以后,其中的幽人开始优游玩弄,仿照古代的名笔,修剪花木,点缀盆池,弄一些盆景,作为家里的摆设。盆景将自然与艺术之美带入屋舍之中。不过一个盆景的培养,常常需要花费十多年。在生活时尚上已是如此精致,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晚明江南优游、闲雅的生活,至甲申、乙酉之际,戛然而止。明清两朝鼎革,打破了江南人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顿时陷入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西湖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感伤题材。往日的河山已经远去,往事不堪回首,怎能不让人悲痛,不让人感伤。江南旧景、旧人、旧事,不过存在于梦中,仅堪“梦寻”、“梦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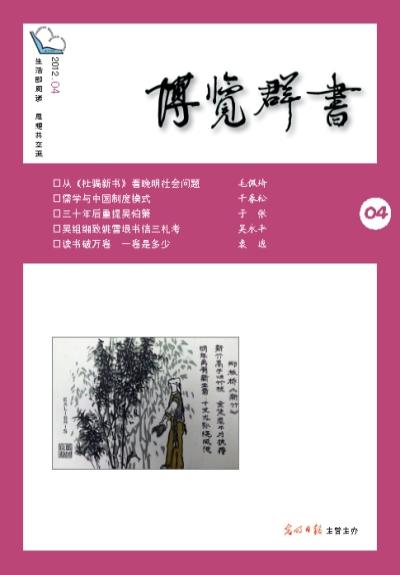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