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冬天,总会想起巴别尔绚烂明媚的文风。想着他最后的申辩:“我是无辜的……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最后的作品……”每一读此,总会埋下头去并忆及《开始》里的那个面颊丰满红润、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奔跑的少年。
70年后的今天,在他的故乡敖德萨,人们设立“伊萨克?巴别尔文学奖”(据俄报载在2010年),并同时为其树立纪念碑。在西方,他和布尔加科夫是最受欢迎的前苏作家。20年代的《骑兵军》终于成为世界文坛的奇兵,成为以少胜多、成功突出黑暗历史重围的典范之作。连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莱辛竟也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对他的敬意(《献给伊萨克?巴别尔的献词》)。
同样,巴别尔也久已扎进汉语的怀抱。从鲁迅的首次提及到人文版《骑兵军》、《敖德萨故事》的行世,这其中既有西方评论的感召,又体现出中国知识人的自我认识。这几年,巴别尔的声音在我国学界从未间断。中华读书报曾多次刊发评论文章;书城杂志做过王天兵与李庆西的专题对话;读书杂志也曾三次刊文述说(蓝英年、王培元、江弱水),其中蓝英年的《请听我申辩》,已经成为汉语读者了解巴别尔的基本文献。并且,众多的作家都阅读过巴别尔,巴别尔大有成为中国作家之作家之势。这里,尤以戴骢、徐振亚、王天兵的努力为甚。王天兵在完善译本的工作之外,还写有《哥萨克的末日》,2009年又出版了《和巴别尔发生爱情》,为人们了解巴别尔打开了大门。至于戴骢,真是应当感谢他。因为,无论是普宁的一泓秋水、缤纷绮丽,还是巴别尔的刀光剑影、铁血柔情,都一样译得出色。这样,除了两个剧本《日暮》和《玛丽》、一些新闻报道、电影脚本《迷路之星》等,巴别尔已全然来到汉语里了。别的,让我们祈祷,还能在克格勃档案库里重现他的手稿。
认识一个人多么难,在巴别尔自己的时代,脸孔对着脸孔都看不清。可他却是清醒的,无论对时代还是创作。“我一生是在和这个人的斗争中度过的”,这是他随手写在自己照片背后的话。他一生在这种激情里度过。在一个鲜血四溅的时代里,他顽强地在作品里整合着自己。而这句话或许也是打开他心灵之门的密码。对一个“便无风雪也摧残”的生命体来说,如若适逢一个血腥的时代,那就是双重磨难,巴别尔度过的正是双重磨难的一生。
一
巴别尔描写的只是人类漫长流血历史上的一段插曲,一段革命巅峰时代的悲歌,同时也是一段人类马背上的历史的终曲。他要把人性放在血腥弥漫的战场上来拷问,犹如维特根斯坦在人喊马叫的战壕里思索生命的伦理。“要革自己的命”,维特根斯坦这句名言对巴别尔同样适用。巴别尔从未想过要到战场上杀人,他说过“我痛恨战争”、“我是个不合格的布琼尼的战士”(《马背日记》)。别尔嘉耶夫有言:“只要你接受了国家、接受了民族性,感到了所有民族的连环套,那么你就接受了战争。”在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作家身上都有一种可怕的民族主义,可巴别尔不同,不仅因为他是外人,是犹太人,更因为他独树一帜的写作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他站在高处。他倾向于这样:选定环境氛围,取消一切议论——这与传统俄语文学里那种冗长的议论的插入多么不同——全任人物信马由缰,绝不包扎伤口。人性是善也好是恶也罢,只不过战场是个可以充分表现的舞台。他要把语言放到战场上来熬炼,其中的秀美与阳刚、咆哮与叹息、情意绵绵的梦境与“铁骑突出刀枪鸣”,真是百折千回而又荡气回肠。这样的写法,还有语言的节奏感、音乐性上,或许只有《平原烈火》那样的作品方可比拟。
正像别尔嘉耶夫所说:“在战争中,仇恨再融化为爱,爱再融化为仇恨……各种极端性纠缠在一起,魔鬼的黑暗和神性的光明交叉在一起……在低处的东西反映着高处的东西,在地面上存在的东西也存在于天空,上帝的天使和撒旦的天使相互斗争。”巴别尔的小说是镜子,他什么也不说,却又像在说:人啊,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样子,如何不要改变呢?而人类已走出多远?我们麻木了,视其为理所当然了。难道历史必须由战争来推动么,鲜血能换来友爱吗?巴别尔一生的勤勉和死亡为其作品做了最好的诠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杀害另一个人,这是沈从文离开军队步入文学的信念之一,为此他要以美好的自然和质朴的人情与之对垒。可在巴别尔这里却是直面鲜血的痛诉与抗争。正是这样一种不眨眼的逼视或能惊醒人类漫长的噩梦,因为人类的整个文化或许都沾染着暴力所带来的血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杀害另一个人,甚至没有权利去随便毁灭一个动物的生命。我们难以忘怀《马背日记》里那些对犹太人悲凉命运的慨叹:“我们是古老的民族,受尽磨难。”还有那些富于人情味的、悲悯的、热爱生活的赤诚独白:“在一间农舍旁边——一头被杀死的牛犊。发紫的奶头贴在地上,只剩一层皮。可怜得无法形容!被杀死的是年轻的母亲……”世纪初的炮火终于使人感到了马背上的不安全,这才卸下了历史无端加在它身上的重负。生活里的他特别爱马、爱动物,可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书生却写下了血淋淋的文本。还是那个别尔嘉耶夫,他说:“如果说在战争中存在着人性化和兽性化的失落,那么,其中也存在着流失在黑暗中的伟大的爱。”《骑兵军》正是这爱的见证。血腥残酷的是文本,文本之外,巴别尔一生都在同自己和人类之恶作斗争。
毫无疑问,巴别尔在文体和内容两个向度上都做出了革命,不仅在俄语里而且在世界上。他那万花筒般的语言色泽,阳光在其间晃晃燃烧又明灭不定,这是俄国文学里从没有过的异端,是敖德萨阳光暖流与莫斯科文学的沉郁寒流在拼杀。关于俄国文学的苦难与阴郁主流,戴骢认为主要是农奴制与集权统治。其实,或许还有严寒。有人问叶赛宁:你的诗为何这样忧郁?他答:“因为俄罗斯的寒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寒冷的国度里再发生如许悲惨事件,人们的心灵可想而知。但巴别尔不同,敖德萨人是天生的乐天派,生性幽默乐观,阳光、大海,充满激情,巴乌斯托夫斯基大体这样说过。他早已把语言的锋刃磨亮,只是在寻找叙事的引力场。这一点,人们不应把他和卡夫卡摆在一起,虽同是犹太作家,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关于卡夫卡的写作,克里玛在《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里有过很好的表述。如果说卡夫卡坐在窗前看看窗外的风景就可以写作,那么巴别尔就必须来到风景里、草原上。巴别尔总说自己缺乏想象力,这在小说内容上或许是真的。他不能凭想象找到自己以为要表达的重要的东西,换言之,他把要表达的东西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为此他要厉声问自己:“是什么在支撑我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水泥?为此他要化名冒险来到战场。但在语言表现上绝不,他做出了非凡的革命。一个人为着文本的完美而呕心沥血,又何尝不是在完成对灵魂的革命呢?“要革自己的命”、“要和自己这个人作斗争”,这到了佩索亚那里得到了更全面的阐释:“革命者是那些没有勇气面对自己从而逃避到对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变革中去的人……如果一个人对邪恶有足够的敏感,他会发现其根源就在自身……让我们写下美丽畅达的一页,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革命。”
当这一切重新回到老托尔斯泰的“从我做起”时,或许我们方能对文学的基本工作真正有所觉察。“一首诗挡不住一辆坦克”,文学的布拉格也绝不会使入侵者畏避。文学与战争从来是相悖的两极,以战争来入文学,这是精神的大冒险,尤其在巴别尔的时代。这是对人类的良知与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严肃拷问。可为了让双手不沾染鲜血,他要将纸笔紧握。要一遍遍地,不停地,如他自己所说,“像犍牛一般劳作,看不见世界”。在这向着人间天堂进发的路途间——艺术正是人间天堂——他感到痛苦:“我生平最大的不幸就是这低劣的工作能力。”那么慢,只因过于激动,在捧出它们时才这样矜持。
二
我接触巴别尔很早,主业之外,苏俄文艺是自己最为倾心的领域之一。90年代阅读马克?斯洛宁的《现代俄国文学史》时就注意到了巴别尔,在“浪漫主义之回光返照”里,作者专辟一章探讨巴别尔。这本书就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样,由流落美国的俄裔学者所撰,虽偏颇,却给出了不同的视角,拓展出了异常的维度。巴别尔作品里最鲜明的光影他几乎都触摸到了。令人惊奇的倒是阿格诺索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它对前苏铁幕后的作家多所涉及,却对巴别尔只字未提。让人不禁觉得,巴别尔在俄语文学里至今还是个外人。毕竟他与同时代其他作家太不一样了,并且,完全不像一位俄国作家,就像犹太画家夏加尔那些明亮、诡异与俄国绘画传统相异的绘画一样。
可是,巴别尔厕身于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人们逐渐会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奇特壮阔的精神文化景观。整整一个苏联时代,如果再加上比邻的白银时代,就像一次宇宙大爆炸一般,催生出高密度的音乐的、美术的、文学的、思想的明星。它不仅远胜过俄罗斯艺术的黄金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其匹的。“俄国竟然有这么多伟大艺术家。”一位美国学者不禁惊叹。什么是人的尊严?这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参照。这是对虚无主义的真正超越,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铁骑下虽微贱,可若能用鲜血铸就篇章却是幸事。巴别尔就是这样。卑污与洁白、枪炮声与歌声、杀害与被杀害,怎么能把所有这些人都放在人类的概念之下呢。在此,人们不应忽略这个群体间犹太人的光芒:巴别尔、肖洛姆、阿莱汉姆、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布罗茨基……犹太人的智慧与俄罗斯的自然、凄厉荒寒的时代浑然一体,闪出异彩——就像瞿秋白在《饿乡纪程》里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描绘,其实在很多俄国作家之上一样——巴别尔无疑是其间分外明亮的一颗。无疑,几位顶尖的犹太作家对俄语文明攀上新的峰巅贡献了智慧,就像王冠上的钻石。可他们却大都命运多舛,就像《马背日记》里所说,原以为苏维埃政权会解救他们,“不料也是呵斥,皮鞭,骂他们犹太佬”。
三
巴别尔的一生是那样动人,在历史的大悲剧面前,他回眸朝世界微微一笑便这样去了。爱伦堡在那篇催人泪下的回忆录里说:“我还要再谈谈巴别尔这个人,我爱巴别尔……”他那样依依不舍。从前总觉得在犹太名人里爱伦堡算比较笨的,因为他的小说都在二流,当然诗歌还有待发掘。其实,他有心灵的智慧,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言:“他有颗金子般的心。”应当说,纵然还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布鲁姆等许多世界顶尖作家、学者对巴别尔的褒奖,爱伦堡的文章还是最好的,它连同佩罗什科娃的《与伊萨克?巴别尔在一起的七年》已经成为巴别尔研究的最基本的文献。
“巴格里茨基连自己才能的一小部分都没发挥就去世了。”巴别尔感叹说。应当说,他还是很幸运的。很多人很有才能,但一生并没做出什么,因为外力或别的,在生命最富创造力的时候他们没能在时间里出场。里尔克用一生的痛苦与挺住来寻找写出杰作的时刻。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言里说,“我本想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科克托在关于雷蒙?拉迪盖的文字里说,“他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刻,死神提前把他带走了。”巴别尔也是这样,他一直在等待自己的时刻,艰苦卓绝,而时间就像一位神,可当高尔基对他说现在可以开始了的时候,他就真的开始了,几乎在阳光闪现的一瞬,就转身提笔了。何等赤诚、何等激动:
……我完全丧失了我这个人肉体上的感觉,四周是一片蓝光,零下30度的刺骨严寒,就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仿佛处于梦呓之中,在首都豪华而巨大的走廊上奔跑,在开阔而遥远的、黑暗的天空中奔跑……要不断的,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的增加大地上一切需要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数量……(巴别尔《开始》)
呼啸而逝的时光,对自己的不满,要把破碎流血的世界用自己同样流血但虔敬的心去缝织。他一生都在这种危险的激情里度过。也许在最后的时刻,他想到的依然是《马背日记》里说过的话:“我想家,想自己的工作,我的生命在飞速流逝。”
(本文编辑 董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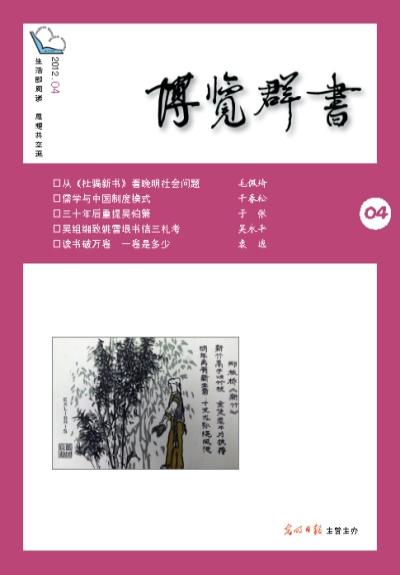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