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家。
上世纪20年代,朱雯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罗洪在苏州师范学院读书,因为他们都是苏州人,又因为都热爱文学,就走到一起了。但他们很少卿卿我我,而是谈文学、谈哲学、谈创作、谈人生……
1932年9月,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朱雯和罗洪在上海举行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才子甚多,有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陶元德等。在婚礼上,巴金与施蛰存第一次见面,两人也成为了好友。
婚后不久,朱、罗二人就迁居到故乡松江,朱雯任教于江苏省立松江高中,罗洪从事写作。彼时,施蛰存、赵家璧与朱雯都闻名于松江,施、朱二位在上海工作,每逢周末假日,他俩常联袂返松度假。施、赵齐聚松江时,也必走访朱雯夫妇,谈学论道,相得益彰。罗洪烹调手艺极高,常做出可口佳肴以待客。朱雯亦常萦怀在上海的巴金,并在松江备好乌篷船,特邀巴金作余山之游。那时,松江去余山只有水路,巴金第一次坐了乌篷船,在蜿蜒曲折的河道航行,一路听着水流轻微的汩汩声响,给人以一种安恬宁静的感觉。他们还同游了醉白池、西林塔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罗洪于1937年写出了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面世,可以说是朱雯、罗洪二位共同心血的结晶。罗洪每写出一个章节,朱雯必加细致的审阅,提出中肯的见解。罗洪亦必诚恳地加以修改,乃至彼此皆认可了才算定稿。妇唱夫和,相敬如宾,可见一斑。
为了出版事,朱雯更是尽心尽力。当时赵家璧正在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任编辑,阅读此稿,称赞不绝,认为这部长篇反映的社会现实虽然不能和茅盾的《子夜》论短衡长,但罗洪作为一位青年女作家,能写出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抬头的小城故事,眼光敏捷,见解独到,是多么不简单啊!
赵家璧的评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那时的一些女作家一般都着眼于身边的一些琐碎细小的事情,或是闺房记乐,或是言情艳闻,能够关注国计民生的实在是好似晨星,寥寥无几。遗憾的是,这部长篇虽然在赵家璧的帮助下出版了,但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能读到此书的还是为数不多的。
抗战期间,朱雯、罗洪一度远赴桂林,朱雯曾编过《五月》文艺刊物。罗洪则帮助处理一些编务工作,他们对投稿者,无论是名家或一般群众,都一视同仁,对爱国青年文章更是倾注热情,不遗余力。有一次收到一篇文稿,朱、罗二位都认为文章写得不错,给发表了,及至寄稿酬时,却发现作者只写了姓名,忘记了写地址,不知如何是好。罗洪认定该稿可能出自学生的手笔,他们竟跑到学校各班查询,结果真的找到了那位粗心的作者。
我认识罗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那时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做事。王元化家住在淮海中路,离“艺研所”很近,步行只要十多分钟就可到达,我路过他寓所时常去拜访他。有一次,王元化问我:“朱雯你认识吗?”我说我在震旦读书时他教过我们的习作课。正好那时包立民在编《文艺报》,要我介绍一些上海作家的近况,我便去拜访朱雯。朱雯先生两鬓虽然染上缕缕银丝,但精神仍然矍铄,他一边让座,一边指着他的夫人向我介绍:“她是罗洪。”于是,我就认识了老作家罗洪女士。
不久,朱雯因脑溢血不幸逝世。我根据零星记忆写了一篇怀念朱雯的短文,在《解放日报》刊出。罗洪读后感慨良多,她写信告诉我说,朱先生生前译著颇丰,她要赠我几本以作纪念,并要我抽暇前往领取。我接她来信,欣慰莫名,兴冲冲地赶到她的府上领书。那次她不但赠给我朱先生翻译的《凯旋门》、《西线无战事》等书,还赠了我她自己的代表作《春王正月》。这使得我对罗洪女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上海师大为了纪念朱雯,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名为《佳作不从俗》。罗洪特地和我联系,把我那篇拙作亦选入集中,使我感愧交集。
罗洪赠我的书中,还有一本朱雯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动乱的一年》。1997年,这本书再版,施蛰存还为它写了序言。那时,诸名家常为新出图书撰写序言,这成了一种时尚,报刊亦常刊登这类序文,以争取更多的读者。我在征得施蛰存先生的同意后,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某家报纸。我一时粗心,把施先生的通讯地址错写成了罗洪的地址,张冠李戴了,以致施先生的稿酬被错寄给了罗洪女士。罗洪好不容易才弄清了来龙去脉,不顾耄耋之年,冒着酷暑,跑到邮局取回稿费,又转寄给施先生。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自己所做的蠢事深感自责。而罗洪却一点也不介意,再三要求我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罗洪生于1909年,于今已是103岁高龄了。我搬到杨浦区后,因路远年高,腿脚不便,很少去拜访她了。但是我还是惦念着她。有时打去电话问候,因她年事已高,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只能托她家人代为转达。我偶尔写些文字,也会复印一份给她。仁者寿,我衷心祝她健康长寿!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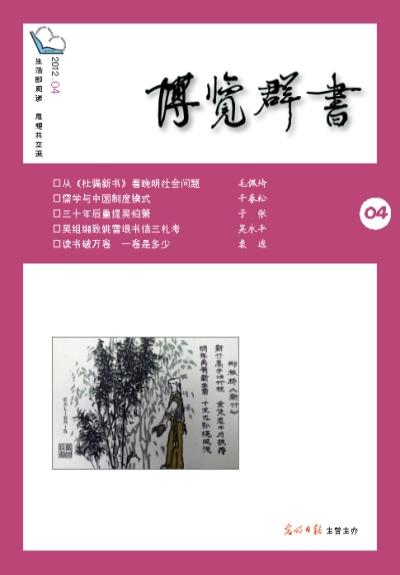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