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武昌起义后,在全国22个省中,竟然有17个宣布独立,然后那些只了解现代政治皮毛的都督,认为美国的建立最初也是因为十三州宣布独立,然后建立联邦,所以中国适可以仿而效之,建立起以美国为摹本的总统制的三权分立的中华民国。然而,这些新政治的操作者,发现他们所要面对的中国,并非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北美,而是一个有着独立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秩序的中国。帝制虽然被推翻,在许多百姓心目中,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袁世凯、曹锟,甚至孙中山,也都对政治理想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的差距缺乏思想上的认识和行动上的准备。因此,民国成立之后,社会崩溃、价值失范,几成一黑暗之中国。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总结,但归结起来有两个,一是对国际秩序理解不够,二是对中国传统认识不深。
虽然杨度等人早就指出,民族国家体系下的西方文明是内外有别的,比如他说:“自吾论之,则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杨度集》P218,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这样的看法,并没被许多法国和美国政治崇拜者所认识到,而是盲目地相信“公理”时代的到来,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只有到巴黎和会上,当德国在山东半岛上的权力被列强转移给日本的时候,那些曾经对“公理”抱有幻想的人,才意识到霸权世界的真正面目。而一直以生吞活剥的方式传播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开始全面反思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就文化层面而言,作为绵延悠久的中国文明,固然有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固然有皇权专制的残暴。但是以礼治国,以情治家,恰也展现出文化之温情。尤其以天地人之综合全体来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可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一条可持续的道路。但是在现代性的挑战面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被视为是中国发展的阻碍,陈独秀甚至说:“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答常乃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P27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并认为现代政治与儒家文化乃势不两立之存在。这样的看法,直可看做是削足适履之愚见。
正是因为对于世界和中国两方面都缺乏认识,所以近百年来,我们始终处于制度的实验之中。蒋介石的失败固然不能简单说成是民国政治体制的失败,但是,漫长的“训政”时期,也足以让人觉得“民主”只成为政治家叫卖的羊头而已。
1949年之后,我们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这个实验最初也是模仿,不仅是经济模式,也有政治的模式。这个阶段在国家层面的成就是中国终于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空前独立的地位。而在政治层面的成就是探索了中国式的基于平均主义的公平体系。但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治上的无序,说明这个制度实验需要做很大的调整。这就是迄今为止仍在进行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当年人们总结中国近代改革的路径的时候,一般都喜欢用三阶段论,即先器物、后制度、再观念。这样的说法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器物层面的改革可以不论。后制度、再观念的顺序说明了一个制度设计的错位,即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意见,即西方的制度是我们必须学的,后果是,实当制度失灵的时候不去检讨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而是怪罪不适应这个制度的人。
我们应该重新提出一个问题,即制度设计是应该以人为本,还是人应该以制度为本。如果说要检讨1840年之后,中国所走过的弯路,以抽象化、理想化的制度为本,而忘记了其中的人,即忘记了每一个有价值、有思想、有生活的中国人,才是那些粗浅的政治家的最大错误。
21世纪,中国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经过了198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来理解中国应该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在经济领域,作为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基地,即成为世界上各种工业设计的代工基地。就制度和文化来看,中国目前的状况也是如此,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经过一百多年的自我否定,现代中国人已经失去与我们伟大的传统之间的联系,我们的耳朵失去了体会圣贤教诲的听力。
建立起与传统的联系,倾听圣贤的教诲,是我们理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角度,也是我们试图让我们的制度建构回归到以人为出发点的重要的一步。其实这也是我研究“制度化儒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10年前,当我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步认识到,研究制度化儒家的解体,是理解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的第一步,而这个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如何建立现代制度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提出了“制度儒学”的概念,并相继出版了《制度儒学》、《重回王道—儒家与国际秩序》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分析儒家与现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关系,甚至分析到儒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的意义。
有一些关注我的研究的同仁已然指出,我的这些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没有从制度建构的原理上去说明儒家应该在当下甚至将来的中国制度建设中的作用,这样导致了许多的讨论依然停留在个案分析和历史的梳理上。所以,制度儒学所要讨论的则首先是儒家的制度建构原则,其次是这样的制度原则如何与现代的制度体系相融合,最后就是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惟其如此,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在这10年或者更长的时段里,从儒家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政治和制度建设的,虽然角度不同,但已经有了很多的尝试。这些尝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超越只从心性层面讨论儒家的单向度突破,而是更多地希望从儒家与中国政治、中国制度建设的关系中来探讨儒家未来的发展。比如郭齐勇对儒家礼法社会的关注;比如蒋庆提出的儒家政治哲学的三重合法性的问题;比如康晓光对于“仁政”和中国国家能力的关系的研究;比如陈明对于公民宗教的设计;比如盛洪对于现代中国的家族制度的思考;还比如秋风、唐文明等对于儒教和宪政问题探讨。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不再迷信于从西方移植现成的制度模式,他们从多元的现代性的视野,看到儒家在中国未来制度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也有一些人从理论层面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扩展性研究,比如赵汀阳对“天下主义”的制度哲学的阐发、黄玉顺对中国正义论的建构,然这些研究都可以视为是中国的制度体系的形成的理论准备。
诚如许多人所言,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最大差别是,传统中国的制度构建主要来自于儒家的价值体系和实践活动,而经过现代性洗礼的当下中国,则不仅儒家传统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且也有近200年的西方文化的传统和近100年的社会主义传统,古老的儒家传统和另外两个新传统,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版图的复杂色彩。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将现阶段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视为继佛教之后,儒家传统对于外来传统的新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我们应该将这个过程看做是中国人发挥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创造新传统的过程,而不是简单采用非此即彼的思路取其一而舍其余。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言,未来的中国文化应当是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吸收了新的价值形态从而形成新的中国思想的时代。就儒家而言,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基要主义的儒家、自由主义的儒家、左派的儒家、社会主义的儒家等形态各异的新的儒家样态,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它们首先是儒家,并最终要归结为儒家。
10年前,有人说我怀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冷眼对待制度化儒家的解体,那么10年后,我抱着添砖加瓦的心情来期待中国制度模式的形成。
(此文为作者2012年修订版序言,本刊略有改动)
(本文编辑 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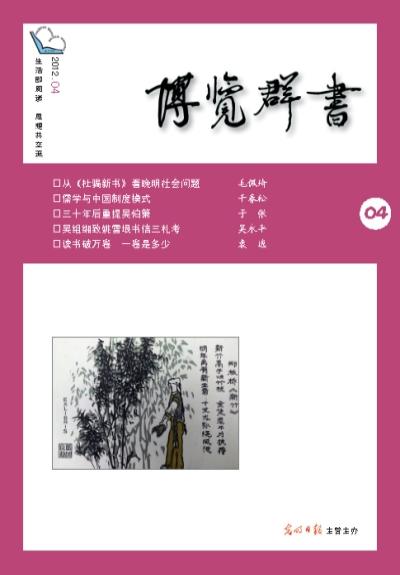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