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谈”,是因关于这个话题,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近来其倡导者李城外君寄来皇皇7大本《向阳湖文化丛书》,我拜读之余,不由不谈谈一孔之见。
一
“向阳湖文化”也可叫做“干校文化”。可“干校”有文化吗?对此有不少争议。“干校”产生于最没有文化、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概括说:“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遽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鲁研专家陈漱渝也说:“向阳无湖,干校无文。”
湖北咸宁这个地方,古称“云梦泽”。“文革”中围湖造田的蠢行使“向阳湖”有名无实,是打上“文革”标记的称谓。上世纪70年代,竟有6000余名中国最顶尖的作家、艺术家、出版人、文化界干部及其家属,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中,有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张天翼、萧乾、张光年、臧克家、严文井、陈白尘、李季、周汝昌、楼适夷、郭小川、陈翰伯、韦君宜、牛汉……这个名单排下去还有很长。他们在这里干着与其年龄和体质极不相称的体力劳动,受着人格的屈辱,留下了血汗甚至生命(如侯金镜、金灿然)。这期间,除了少数人(郭小川、沈从文、臧克家等)坚持写了一些诗篇外,这些作家、文化人被迫集体噤声,只能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思想汇报。“干校无文”,诚哉斯言。
然而这一奇特的历史,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吧——文化之劫的“文化”!
这一“文化”得以成立,还要感谢李城外。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发现并致力于发掘、整理、保存这一“文化金矿”(对此也有不同意见。陈漱渝认为:“当年下放‘五七干校’的文化人本身是一种‘金矿’,而‘五七’干校的生活本身不宜称之为‘文化金矿’”)。他遍访京城当年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约他们写干校生活的回忆文章;他自己也写下系列人物专访,于1997年结集成《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四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2010年武汉出版社又出版了这套厚厚7卷的《向阳湖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向阳湖文化研究》一卷,《向阳湖纪事(上下)》两卷,《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一卷,《向阳湖诗草》一卷和《城外的向阳湖(上下)》两卷)。如果说“向阳湖文化”是当代值得开发与保留的文化遗产,那么这一文化工程的建设已初见规模。
二
这一文化工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是青年学者王彬彬在李辉《旧梦重温时》一文基础上写的《还有什么不能卖》(《岭南文化时报》1996年11月18日)。文章激烈地抨击向阳湖是在“卖文化”,猜想“在他们为引起人们对咸宁的兴趣和好感而对‘咸宁干校’的大力‘开发’中,一定不会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一定会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会尽可能地弄出一点诗情画意来,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甚而愤愤地说,文化名人们当年“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在咸宁受到凌辱,今天,他们则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在这块土地上再受辱一次”。
读了《向阳湖文化丛书》,我觉得王博士的文章是过于武断了。他并没有认真去读向阳湖文化名人们那些饱含血与泪、揭露与控诉的回忆文章。诚如李城外所说,挖掘向阳湖“文化金矿”,旨在铭记历史,弘扬文化,与巴金先生所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许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文革”以后,出现了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文革”的苦难经历孕育了一批文学新人;可本应成为创作源泉的“五七”干校生活,却很少见诸作家笔下。除了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散忆》和《牛棚日记》等,真实反映干校生活的文学作品可谓少之又少。臧克家在1978年发表的诗集《忆向阳》,虽然也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但因作者在干校相对较好的境遇,这种田园风味的诗篇并不能代表干校生活的本质。究其原因,是作者大都年迈体衰,还是“当代人说当代事”的顾虑?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坛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城外对向阳湖文化名人的文字抢救,确实具有深远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正是在他的约请下,老作家、艺术家和老出版人们才拿起笔,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后,陆续驾鹤西去。如果没有李城外的执着坚持,这段历史可能就永远湮没了。
收在《丛书》中的大部分文章,还是敢于“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的,并没有“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我们读到洁泯“半人半鬼,非人非鬼,是人乃鬼”的伤痛感受;读到胡海珠对侯金镜在强劳动下猝然而死,被“一张苇席卷起”,“往卡车上一扔”的惨痛记忆;读到年高的冯雪峰在泥水里放鸭,摔伤了爬起来又摔倒的情景;读到大翻译家陈羽纶被工宣队误诊而瘸了一条腿,以及阎纲被污“五一六”,连遭逼供、毒打和牛汉“野草莓救一命”的故事……读着这些,常给人以阅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感觉。当然,这里也有各种人性的表现:有每天向“五七战士”收取吃食香烟“供奉”的军代表,也有在难友挨斗后悄悄送上一块饼子的严文井;有打小报告诬陷他人的“圣人国学家”,也有为保护别人不惜得罪军宣队领导的郭小川……正如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家在回忆中为“文革”众生相“立此存照”,揭示大难中的国民性,警示后人,无疑使这座“纸上的文革博物馆”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三
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有特殊的兴趣,因为干校也寄托着我终身难忘的记忆。虽然那时我还是少年,但已过早地尝到人生苦涩的滋味。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虽然早已有人撰文,诟病我们这个民族有“健忘”的根性,但不能不承认,近年来,“干校”的往事在沉寂了四十年之后,又开始被人提起,甚至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也不能不承认,出现这一现象的动力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开发历史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
我们那个位于贺兰山下的“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就在四五年前得到这样的开发。地方政府花大钱建起一座“干校博物馆”——不是纸上的,而是大兴土木而建的。当年的“五七战士”们,对此大都持赞成、支持的态度,认为这是抢救历史,为后人留下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的善举,纷纷捐出保存多年的干校旧物。然而一俟那博物馆建成,见到的人,又不免生出几分遗憾——它太像京城里一座宫殿了,和我们当年住的那个简陋土坯房、黄土围子加岗楼的劳改农场有天地之别。博物馆的一期工程,展出了不少“五七战士”用过的劳动工具、生活用品以及书籍、笔记本等实物,也有不少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但时过境迁,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特殊事物的真实复原,尚不能尽如人意,给人以“隔”的感觉。
博物馆开馆那天,当地来参观的老乡人山人海,挤破了头。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少人或许是看到荒凉的西大滩突然出现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来赶热闹的;我更担心那些青少年,看到展厅一进门那组“高大全”式的雕像,会对那段历史产生美好的遐想和虚幻的神往。
与“向阳湖”不同的是,我们这个干校大干部多。但也有一些文化名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教育家林汉达,语言学家周有光、叶籁士、倪海曙等。对他们的“干校”经历,博物馆的建设者们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完全应该的——对于“历史”来说,最有价值、最能流传久远的还是文化,而非权柄。一位北京作家为写《走读周有光》一书,千里迢迢特地到这里收集资料。回京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我进了周老在干校住的屋子!”谁知我一看照片才发现,那标着“周有光旧居”的屋子,不过是我们造纸厂的青年宿舍,和周老当年住的“二站”相差了20公里!
在昔日“五七战士”们的建议下,“博物馆”建设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些不足,正在“二期”、“三期”工程中加以改进。改进方案之一,是以尚存的造纸厂老厂房为扩建基础,整旧如旧,比较真实地再现当年干校风貌。同时,对“干校文化”的深度挖掘、整理工作也在进行。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批评“博物馆”建设者们,实际上通过“干校博物馆”这个事儿,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在向阳湖叫“向阳花”)和他们已成了朋友。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第二故乡”,这个回望过去的精神家园能够建设得更好。经过建设者们的努力,这个“全国第一”的五七干校博物馆,正在成为我国“五七干校文化”研究与展示的一个中心。
我想说的是,王彬彬博士的文章虽然偏激、尖刻还有点粗暴,但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提醒我们:在反映历史以至让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时候,一定要“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一定不要“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不要凭空“弄出一点诗情画意来”。我妄自揣测,王博士写于1996年的这篇文章,也许在客观上起到了提醒、敦促李城外更真实地面对历史、反思历史的作用。虽然我不喜欢前者主观武断的文风,但有时来自反面的刺激也能起到正面的效果,使得日后出版的《向阳湖文化丛书》更加厚重,更加令人信服;也提醒五七干校博物馆的建设者们,将这段历史诠释得更加真实,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四
看了《向阳湖文化丛书》,我觉得确实有一个“干校文化”存在。这不仅因为众多文化名人集中写下了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写下了他们的感悟与思考;也不仅因为“五七战士”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创作的表现痛苦愤懑(对迫害)、讽刺幽默(对时代)、高兴愉悦(对劳动)以及坚定向往(对未来)等各种感情的诗篇,还因为,这里有很可贵的理论建设。《向阳湖文化研究》一书收入12篇关于“五七干校”研究的学术论文,28篇书评及研究动态、史料和争鸣文章等,是我迄今见到的最成规模、最像样的“五七干校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和书评达到很高的水准。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我认为城外君编的这本书,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今后会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博物馆——纸上的干校博物馆。
这套丛书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它丰富多样、兼收并蓄的特色。关于“五七干校”的历史,由于人们的经历、处境各不相同,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批判揭露者有之,深情怀念者亦有之;血泪控诉者有之,五味杂陈者亦有之;套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一千个人对干校有一千种解释。编者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将这许多不同特色、不同观点,甚而是激烈批评自己的文章汇于一处,正好给人们提供了多角度、多方位看待一个事物的可能性,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观念撞击的空间,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民主的精神。研究“五七干校”,汲取历史教训,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因为“文革”和“五七干校”,正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向阳湖的悲剧,正是大批文化人失去了说话权利的悲剧。
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是学者在书斋里把玩的东西,也不应清高到不为现实服务。一谈经济似乎就沾了铜臭,丧失了文化品格,这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过乡、去过干校的人,深知那时当地的老乡有多么穷,现在也并不大富裕,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快点富裕起来。如果真能通过挖掘干校历史,带动一方经济发展,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又有何不可呢?宁夏干校博物馆的人来找周有光,周老运用他的全球化视野,为地方如何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出了不少好主意。这不也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当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前提是不要来虚的、搞花架子,只图“政绩”不看实效;也不要歪曲、粉饰历史,谄媚当下误导后人。如果没有上述两点弊端,真能达到“文化”、经济双赢,又何乐而不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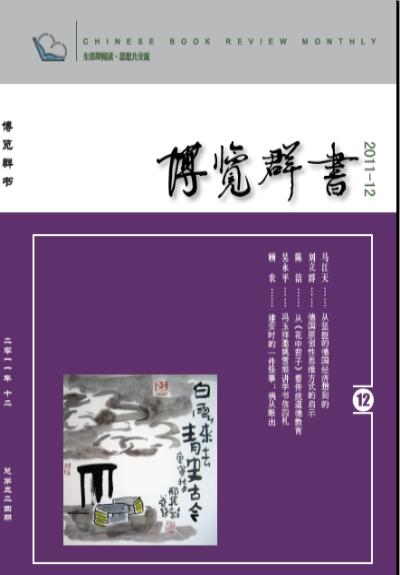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