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的研究,是当今国际史学界研究发展的新趋势,是“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标志。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一书专注于档案文献、口述史料与现代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研究,能从多角度多方位勾稽察核史实记录,用以小见大的方法,从史料矛盾的爬梳中探寻史实真相,提升历史事件、活动和人物的核心价值,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具有相当的创新;能站在学术前沿,适应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时出己意;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突破性进展。
该书的突出特色、主要建树和学术价值主要有:
一、善于运用档案、书信、口述史料对比考证的方法,从历史的细节出发,探索梁启超、陈独秀、徐志摩、台静农、蹇季常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人物文化性格的核心之处,有新的创获。如:由梁启超与蔡锷的交往史料论证出梁对于“共和再造”的杰出贡献,“为全国人人格而战”的精神实乃护国运动的核心(P72-73),“蹇季常是梁启超的灵魂”(P72)等,皆有新意。对梁的思想善变、性格复杂、公众形象与人格特质不一致(P21-28)、陈独秀与台静农的特殊关系(P108-113)、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思想根基的真实旨意(P113-143),皆有为史家忽略的创获。这些探索对于研究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大有裨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二、重在通过档案、书信、口述史料,辨伪求真,不仅纠正一些史实的偏颇、歧义和伪造,而且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纠空疏之学风,复传统的实事求必求其是、持论必求其正的实学学风问题。该书以实例分析和细密考证,揭示实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揭示敏锐的观察力与扎实的考据方法、学术功底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方法论上也很有启示性。如:揭示梁启超年谱台北本基于政治见解的涂抹删改(P40-42)、对二二八事件口述史料记载的曲意涂改(P294-320)、对《实庵自传》不同版本的订正(P110-113),皆能秉持客观求实态度,这对当前空疏学风与范式失衡的学术大有警醒价值。
三、强调“场景再现”(P24)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提倡“文化情怀”(P26),以情感投入来“深入历史的最核心之处”(P27),这种对历史“抱着理解的同情”的研究态度,在当前亟有价值和意义。尤其对梁启超与徐志摩的严师诤友的情谊、梁启超与蹇季常、陈独秀与台静农、梁启超与蔡锷之间的友谊与交情,条分缕悉,鞭辟入里,剖析史料令人信服。
四、资料充实,引证规范,引用资料、观点来源清楚详明,并有新的史料发掘,值得称道。
五、通过对黄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与官方版《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比较与批判,澄清历史真实与昭示学术良知,彰显了该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和黄彰健先生的学术良知,彰显了他们对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使得该书除了学术价值之外,尤具关怀现实的深切意义(P321-322)。特别是揭露把“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的别有用心(P294及315-316),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上是该书的显著特点。然笔者对该书几处有不同看法,敬谨提出与作者商榷:
一、对书中有关文化人物,应放在当时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性格、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的大视野下来分析,从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集群的集体性格来分析和提升。该书已提升到这样的层面了,但缺乏画龙点睛,是个遗憾。
二、对梁启超所说“唐盟碑殆我国与他国为国际上平等条约,传世最古者”(P64)的观点,应加以分析和指正。梁的观点是错误的,“唐盟碑”是国内民族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该书没有分析,是个缺憾。
三、对“告别革命”问题,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问题(P83-86),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抽象论证。该书不加前提条件,笼统肯定改良,否定革命,不妥。
四、口述史,依我个人见解,分为“口述史料”、“口述历史”与“口述史学”三个层面。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不能笼统说口述史料很多靠不住,不如档案史料真实。这个问题易引起争议。作者对鉴别口述史料的真伪与档案书信的可信程度,已做出了范例,这是值得称道的。但给人唯有档案书信才是可信的、口述不可信的结论,失之偏颇。作者在“口述历史”层面已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建议在“口述史学”的研究层面要慎下结论,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持论求其中,实事求其是。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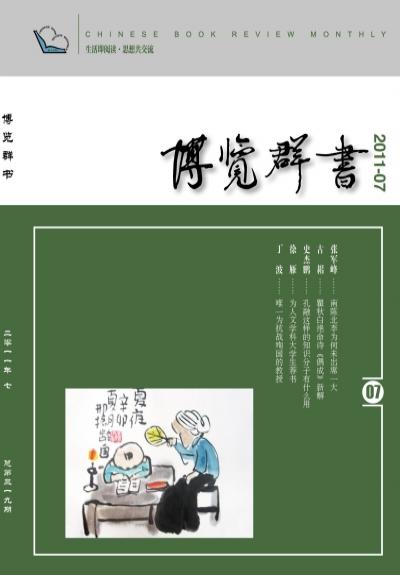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