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成都召开的两次读书年会上,与会者对向阳湖文化都有一番争论,也很激烈,但似乎并未触及实质性的问题。时间仓促,未能展开,充分发表意见,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透彻的事。会后,我不断地思考,深感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一下。
向阳湖文化抑或干校文化
首先,所谓向阳湖文化,主要内容是“文革”中五七干校的那段历史。这就有了一个大前提,即应该搞清“文革”是怎么回事,“文革”的对象又是谁?这段历史,刚刚过去不久,大家是记忆犹新的。“文革”要打倒的对象,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黑五类、反动权威……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统称之“牛鬼蛇神”,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归结起来,实际上只有两种人:一是全国上下在职在位掌握实权的老干部,从国家主席、副总理到各省(区)市以及地县的一、二把手或三、四把手;二是教育界、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和民主党派成员,以及右派、历史反革命(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纯属闹剧,草菅人命),有权的与没有权的校长、院长、书记、主任、教授、研究员、学者、专家,大多是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方方面面的名人、权威人士,等等。前者,全国江山一片红,造反派夺了权,他们被罢官了,下台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含冤自杀、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文革”后都得到平反昭雪,健在的官复原职,发挥余热。而后者的道路却是比较曲折复杂的。“文革”之初,写检查、受批斗、游街示众、扫地出门、关入牛棚,等等;后来则被送去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短不一,直至“文革”结束,才算偃旗息鼓,得到解放。
那么,五七干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报告给林彪的一封信做出指示,五七指示由此而来。在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后,亦即“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之际,开始有了五七干校。最初,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柳河办了一个大农场,取名叫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其中《编者按》有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乎,这一“新的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各地纷纷群起效法,在边远荒芜之地建立起大小不一的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里,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并不问是老、病、弱,统统要去,不去也得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罪的流放”。如河南信阳罗山建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会科学部分——亦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和天津的团泊洼建有文化部所属的五七干校,在江西余江鲤鱼洲建有北京大学的试验农场,在江西余江鲤鱼洲还建有清华大学的试验农场,在上海奉贤有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等等。以上是规模比较大的,也是在全国有影响的。至于规模比较小的,各省市县,甚至一个单位、一个学校都可以在农村建立五七干校,不可能一一罗列了。总之,知识分子必须走五七道路,就是要到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去农村、山区)进行劳动改造。
历史是既往客观存在的事实。“文革”中的五七干校是我国当代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不容忽视,更不能略而不论。总之,五七干校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局部问题。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有一个形形色色的五七干校。对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如果以文化来称谓它,那是五七干校文化,而不能是柳河也好,向阳湖也好,团泊洼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某个地方的文化。
不妨再做个类比,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茶叶品种繁多,其中尖端者也有好几个,如龙井、碧螺春、毛峰、铁观音、普洱茶……却从未听说有龙井文化、碧螺春文化,等等。
而且,究五七干校的实质,这个问题还可以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在刚刚解放了的大中城市里都搞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上至七老八十的专家、学者、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下迄十五六岁的中专学生(即毕业后要当干部者,如师范生),都要人人过关,做思想检查,建立新的人生观、世界观。虽然还比较和风细雨,不用斗争的方法,但过后不少人要放下自己的专业工作和学习,短时间地到农村搞土改,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或到边远地区去访问、考察等等。由此而下,对知识分子,名目虽异,本质相同的运动接二连三,源源不断。三五反运动(主要的是工商干部,也波及到部分知识分子),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胡适的实用主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和反右,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规模或大或小,或长或短,主要都与知识分子有关。肃反和反右,前者针对既有的,而后者却是新划的,全国总计划了多少,说法不一。其后又有反右倾、拔白旗、交心运动,一直到“四清”、“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前面的一系列运动,总的说还是文斗,既不触及人体,也不损及书籍、财物。而“文化大革命”则不然了,文斗、武斗并举,烧书、横扫“四旧”——包括重要的古文物,一齐毁掉。或扫地出门,或一号令下,统统遣送下乡。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去了五七干校。
总而言之,从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的五七干校整个历史阶段,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五七干校虽是登峰造极了,也还是它的一部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必须联系起来,全面地进行研究,这样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给子孙后代一个真实的交待。
再具体一些讲,五七干校也仅仅是“文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不是全部的。“文革”的发生,早在批判京剧《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的杂文时,就已经发出了信号。“文革”之初,先有了“牛棚”,而后有了五七干校,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史”,它的前因后果都必须联系,而不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观之,湖北咸宁向阳湖(不知向阳湖这个名称,古已有之,抑或应运而生的,如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向阳学校、向阳大院、向阳商店、向阳大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仅仅是五七干校中的一个,而五七干校又仅仅是“文革”的一部分,以向阳湖文化为名,能否涵盖这段虽短却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是颇为值得认真商讨的。
值得重视的干校研究
毫无疑问,五七干校应当研究,“牛棚”也应当研究,“文化大革命”更应当研究。研究所需,首要的是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当事人亲历亲为、亲自见闻及种种真实的事物,尤为可贵、难得,必须倍加珍视、收存、分析、研究,总结起来。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陆续地出版了一些由当年被关过“牛棚”、进过五七干校的人所写的回忆亲身遭遇,和深刻反思的书籍。比较著名的有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谭其骧日记》中的《文革日记》、陈学昭《浮沉杂忆》中的《灾难的年月》、刘冰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杨绛《将进酒》中的《丙午丁未年纪事》、《温济泽自述》中的第八章《遭遇“文化大革命”》、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中的第九章《暮年岁月》、韦君宜《思痛录》中的《“文化大革命”拾零》,等等。
有关五七干校的书同样不少,如贺黎、杨健采写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杨绛著《干校六记》、陈白尘著《云梦断忆》、何西来的口述文字《往事如烟》、王西彦口述的《焚心煮骨的日子》、黄宗英口述的《但愿长睡不愿醒》。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诗人在干校中是怎样被迫致死的。巴金的五本《随想录》中有多篇忆及“牛棚”生活,孙犁的散文(如《文字生涯》)小说(《女相士》)也描述了“牛棚”、干校的见闻、感悟。总之,此类的书籍和文章是不胜枚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多的书籍问世,不断地充实这方面的史料。
不过,仅仅有这些资料还远远不够,需要有更多的实物印证这段并不很长的历史,如当年五七干校的旧址,住过的“牛棚”、土坯房,劳动时所使用过的种种工具,生活起居的床、凳子、马扎以及大批判的标语、大字报……凡是有关“牛棚”、干校的一切的一切,都应收集起来,成为不可或缺的史料。这方面,湖北咸宁向阳湖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的有效的、令人称赞的工作。他们是做在全国各地干校的前边的。他们及时地采访了许多进过干校的耄耋老人,抢救下稍纵即逝、失而不可再得的口碑、活的史料。他们编写出版的书籍,应受到重视,给以应有的评价。
列宁曾有过“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论述,妥当与否,另作别论,怎么理解它,也无关紧要。不过,对待同一事物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如同样住过五七干校的人,却写出了不同的文字。有人《忆向阳》,唱的是赞歌,阳光普照大地,到处欢声笑语,莺歌燕舞,好一派心向往之的乐土。而有人描绘的《团泊洼的秋天》却“时刻都会轰轰爆炸”:“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以上这一些,对我们认识五七干校,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也不能不引起深深的思考和警惕。
对一些枝节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态度,有些事意见分歧也在所难免。但对根本的问题,如“文化大革命”及其派生的五七干校等,却容不得含糊、是似而非的。这里,不妨引证一下,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段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还有“‘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前一句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后一句是为知识分子正名。由此可知,“牛棚”也好,干校也好,这些曾经专门对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事物,都应进行深刻的批判,而不能是颂扬它、赞美它。在收集、整理、编写一切有五七干校的资料和书籍,都应依据以上无比正确的论断,才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
(本文编辑 李文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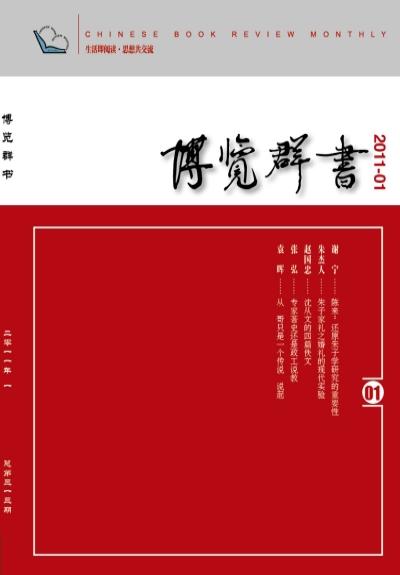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