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我在震旦大学读书时,何满子先生正在震旦教授文艺学。那时他很年轻,仅30岁出头,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与王元化、贾植芳亦很投合,皆崇拜鲁迅与他的著述,都被誉为“鲁迅专家”。他才华横溢,讲起课来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声音洪亮,姿态翩翩,引人入胜。在短暂的相处中他给我留有很好的印象。
在讨论写作时,何先生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具体事例来诱发我们的写作热情。他曾经开玩笑地说他不怕“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小就学得一手好古文,还会写“八股文”。有一次,塾师不禁拍案叫绝地称赞他的作文:“要是放在清朝,凭着这篇文章,考个秀才举人也不在话下。”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他在南京当记者,邂逅沈钧儒老先生,当沈老知道他会写“八股文”时,吃惊地说:“你如此年轻,竟能会写这玩意,不多见,不多见。”
那时震旦的学风宽松,自由气氛也比较浓厚,人们敢于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何先生更是知无不谈,谈无不尽。谈到写作时,他说在读一部书时,最好的是先读了一多半再停下来,思考一下应该如何持续下去,自己所想的与作者是否不谋而合。如果有了距离,就可以相互对比一下差别在哪里,孰高孰低,孰精孰拙。这样不但可一目了然,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还可以训练自己的脑子,开涌自己的思路,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测验出自己的实际水平。把自己看成是一匹马,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他这一番宏论,我感觉颇有新鲜感,一时心血来潮,就跃跃欲试。正好这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青崖教授正在讲授他所翻译的莫泊桑的《项链》,我就照着何满子所讲的,有意先读了一半,然后自己编写下半部。李青崖教授知道我的情况后,不但没有说我不专心听课,还夸奖我读书方法“很有见地哩”!
说实在的,那时我能读上大学也是勉强的。当时父亲因心脏病谢世,母亲亦生病卧床,哥哥处于半失业之境,一大家人生活都很困难。我虽然也申请到了助学金,却不时牵挂着家里的亲人,很难专心一致搞学习。我也曾经有过辍学找工作以助哥哥一臂之力的念头,便把这想法说给何先生听。他听了我的叙述,感同身受,对我有所同情,要我振奋精神,面对现实,战胜困难,还把这情况告诉了贾植芳教授。说来事情也巧,这时有一所职工夜校人手不够,正在向教育部门聘请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作为代课教师。经贾、何二位向教务处提出申请,我成为该校的代课教师,不但解决了膳食费,在生活上还得到了一点补贴。这意外的收获使我喜出望外,因而也能顺利地完成了大学的学业。饮水思源,贾、何二位先生恩德难忘。
52年前大学毕业之时,我们开过一次谈心会,满子先生的临别赠言是“待人以诚,多读鲁迅书”。不想在后来的日子里,何先生却生活坎坷,屡处逆境,不仅划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还被下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所受之苦,一言难尽。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平反了冤案后,他也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时虽将届暮年,但他干劲不减当年。工作之余,他钟爱杂文,一生敬仰鲁迅的风骨文章,学识渊博,观察生活,细致入微,针砭世弊,入木三分,一文既发,振聋发聩,破解民风,痛快淋漓。他的人格魅力赢得广大读者的爱戴,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
作家白榕对何先生极表倾慕之情。白榕本名谭之仁,在震旦和我同窗,后来转学到北京大学,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与我再度同窗,友谊之深,非同一般。有一次,白榕来上海,要我陪他去看望满子先生。一到何家,只见他的书斋群书聚萃,触目生辉,何先生笑脸相迎,殷殷好客,溢于言表。事后,白榕说他心仪满子先生已久,尤喜他的杂文,每遇佳作,必贴于册,如今得见斯人,三生有幸!
何先生以为作一名学人,做学问不能赶时髦,既要有文品,更要有人品,人品不正,只不过在卖狗皮膏药,欺世盗名而已。汪精卫文品虽好,但他叛国投敌,千夫所指,万夫所骂,成为民族罪人。
满子先生以为写历史戏要多读书,勤查资料,切忌信口开河,随心所欲,以致成为笑柄。现在电视中“辫子戏”很多,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之类,一看片名就觉得可笑,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王朝”是指一个朝代的全过程,不是指某一个皇帝而言,正如李氏唐朝不能把唐太宗之“贞观盛世”和唐玄宗之“开元盛世”称作“太宗王朝”或“玄宗王朝”同样的道理。
河满子先生还以为,名家学者开讲座、作报告要有真知灼见、学术价值,而不能哗众取宠。他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像是在说相声、说书,找不到它的学术价值;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不是在开玩笑吗?这些看来似乎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但在他那像显微镜的目光下,无一不显现无疑。但他并不是在豆腐里挑骨头,存心压制新的名流学者,恰恰相反,他对新一代的学人抱着殷殷的厚望呢!
在我与何满子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我说:“你能写点杂文吗?”我一时难以回答,只能脱口而出:“那玩意有点风险。”他不以为然地说:
风险也许就是“怕”的借口吧。要说风险,人之一生无时无刻不处于风险之中,儿童怕夭折,外行怕车祸,乘船怕覆舟,投资怕亏本,睡觉怕失眠,骑马怕路窄,怕之所在,私在作祟,去掉私字,一身轻松,写杂文之乐也就乐在其中了。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满子先生一生遭遇,也许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各种苦难他尽尝矣。然一旦恢复公职,埋头工作,所付辛劳倍于他人,他著书立说,尤钟杂文,深解人间真谛,敢想人所未想,敢言人所未言,被誉为“八大杂文家”之一,并不为过。斯人虽逝,但他那极具战斗性的杂文定能长留于世。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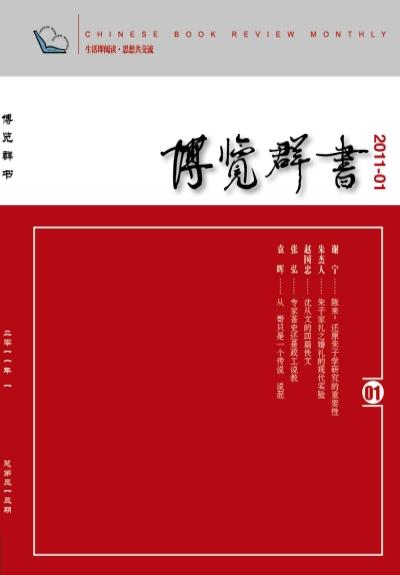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