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作为国共两党在领导的国民革命中被打倒的对象,被认定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北洋外交自然也是“卖国外交”。北洋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巨深。对此,长期研究北洋外交史的专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感触最深切。他在爬梳中外档案时,不断看到与主流诠释不尽相同的历史图像,遂激发了全面探索北洋外交历史地位及意义的愿望。他以追求历史真相的庄严使命感撰写成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一书,出版不久就受到广泛关注,不是偶然的。
“废除不平等条约”怎样遮蔽历史真实
由于外交史研究与国内外的现实政治关联密切,我国的外交史研究常常为了满足现实的政治需要,使外交史研究沦为外交宣传。
外交史研究的政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或称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民族主义又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无论修约还是废约,皆避不开“不平等条约”一词。此词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很难作学术讨论(唐著P3,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唐著敏锐地觉察到,考察“不平等条约”本身的学术史,是厘清近代中国外交史书写中“史实”与“神话”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澄清北洋修约史真相缘何被废约“遮蔽”的关键所在。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百年国耻的集体记忆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集体记忆的核心地位,历经一个长期的塑造过程。清末民初,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曾使用“不平等条约”一词,惟当时并未普遍流传,内涵也不明确。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因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不平等条约”一词渐为朝野各方使用。之后,受苏联输出革命之影响,1920年代国共两党利用“不平等条约”宣传来塑造国人的国耻记忆,引发民众反帝思想,进行革命动员。国共相继执政后,“皆以反帝、反军阀、废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咸集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发展历程。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但是不能突破大格局的局限,北洋修约的成果遂因政治不正确,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可说完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P2)。
废约与修约原本是达到外交目的的不同手段,本质上是一样的。唐著指出,“孙中山与广州政府的外交政策,原本与北京没有太大的不同,也是主张‘修约’、‘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等,主要的争执在于与北京争夺各国的承认。然因不断遭列强冷眼,又因‘关余’问题与外交团有冲突,民族主义的旗帜比较明显。但是,真正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分途,与列强对抗,还是‘联俄容共’以后的事,尤其是1923年底‘白鹅潭事件’后,才决心倒向苏联。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外交上开始标举‘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P306)。
归纳起来,唐书认为“不平等条约”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遮蔽”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平等条约”本身内容和概念的模糊不清;其二是对主持或参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责任人评价不公允,或夸大或贬低。
关于第一方面,以著名的“二十一条”最为典型。唐书指出:“到目前为止,学界及一般民众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及所订条约之名称仍有许多误解。在中国‘二十一条’早已成为反帝废约运动的宣传重点,一般人常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与交涉之后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混淆,常以为‘二十一条’就是条约名称。……八十多年来,‘二十一条’一词众口铄金、积非成是,在‘国耻史’和北洋军阀‘卖国史’上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P157-158)
关于第二方面,以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和1924年《中俄协定》的不同评价最为典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1924年《中俄协定》的评价,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评判,而非学术研判。
首先,关于袁世凯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学术界的评价曾经历过一个“昨是而今非”的变化过程。如唐书所言,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王氏在1933年该书第六卷,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评价是:“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搓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大公报社,1933年,P398-P400)蒋廷黻在该卷书评中,亦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经做到尽头。”(蒋廷黻《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大公报》1933年9月18日第3版)足见到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袁世凯外交尚能公允对待。但是,王芸生同书1980年新版及2005年八卷本,对袁世凯的评价则颠倒过来,认为:“袁世凯之所以为袁世凯,终以窃国大盗终其身也。”(唐著P156-P157)王书对袁世凯评价前后不一,显然与变化了的政治现实有关。
再如,唐书指出,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俄协定》),由于此案数十年来与“联俄容共”、“反帝废约”密切相关,许多当时的政治宣传,诸如苏联自愿放弃在华特权、平等对华、协助中国“反帝废约”等,在革命党相继执政后,写入教科书中,不断复制宣扬,误导许多历史诠释,扭曲、遮蔽了真相(唐著P174)。唐书从档案考察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但就废约而言,苏联在条文表面上虽表示废止旧约,实际上与华会列强一样是‘口惠而实不至’,坚持既得利益,不肯放弃任何条约特权。就反帝而言,苏联介入中国内政的程度,与其所抨击之‘帝国主义列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P269)当时,苏联对中国内争介入之程度,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之外,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也是望尘莫及。唐书指出,苏联对中国进行“多元外交”,除中苏、日苏谈判同时进行外,在中国同时与北京、广州、奉天、新疆、张家口接触,也同时援助广州与冯玉祥,意欲透过冯氏与孙中山,对北京政府产生影响力(P307)。简言之,苏联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对华外交投机性很强,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充满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怎样实现外交史研究的“历史化”与“学术化”
中国外交史研究要实现“历史化”与“学术化”,是八十余年来中国历代学人孜孜追求的目标。1930年,蒋廷黻在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时,即呼吁中国外交史研究要走“历史化”与“学术化”的道路。然而,由于现实政治的压力,自蒋氏之后,中国外交史研究并没有如他所愿,完全走向历史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中国外交史研究以及官方历史教科书,长期被“反帝反军阀”,“反帝废约”等“革命外交”叙述所遮蔽。如唐书所云,“八十多年来国人一直如此相信,历史学者也从未质疑,造成国人对历史理解的扭曲”(P308)。
外交史研究要做到历史化与学术化,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然而,唐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原因是他牢牢把握了外交史研究的“国际性”与“专业性”特点。外交史虽然是历史,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历史研究,因为外交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国际性”。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必须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交涉国的档案资料。若单纯依据一国的档案来谈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有失公允。所以,研究外交史者首先必须掌握多国语言,这是治外交史的一个基本条件。唐启华先生留学英伦,熟练掌握英语与日语。唐书主要依据中外档案作实证研究,除了使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档案》、《外交部档案》、“党史馆”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等档案之外,还充分利用英国《外交档案》(FO Files)、《美国外交文书》(FRUS)以及《日本外交文书》等,在档案利用上充分体现了史料的“国际性”。此外,唐书论述对象,尤其注重北京政府与多国交涉的案例,没有局限于北京政府与某几个大国之间的交涉。唐书探讨“环绕北洋修约之国际多边互动”,同时研究中国与日本、德国、俄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之交涉及互动。
使用多国档案,重视多边交涉,这只是外交史研究“国际性”的一个外在层面。外交史研究还需要研究者在心理上具有“国际性”。换言之,就是要求研究者能够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心理,体认到各国皆各有立场,必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不以中国角度非议列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可谓知易行难。如唐先生所言,“这样的研究取向难度比双边外交研究要高得多,但因此可获全局观,也可与各国外交史研究接轨与对话,将中国外交与世界外交的发展历程结合”(P16)。然而,学术研究贵在坚持有恒心。观唐书标题以“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来定义北洋修约史,吾人即可知其用心之良苦。
此外,唐书在撰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也可谓别具一格,独具匠心,凸显其强烈的学术性与专业性。唐书以“北洋修约史”命名,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论述北洋修约历程的断代专史。以往撰专史者,很容易陷入“通”而不“专”,或“专”而不“通”的两难困境。然而,唐书巧妙地做到了“专”而“通”。具体言之,唐书共分八章,首章论述“清季官方修约的观念与实践”,既重视了近代修约的历史连续性,又厘清了北洋修约的思想源头。次章探讨“民初平等订约与修约的努力”。第三章,探讨“1919年修约方针的确立与推动”,此章上承民初修约背景,下续1920年代北洋修约的展开,起承转合,宛然一体;第四、五、六三章,分别探讨中德、中奥、中日以及中俄的废约与修约交涉历史,以中国对德、日、俄这三个《辛丑条约》缔约的主体国家为论述对象,层次分明,把握了北洋修约的发展脉络。第七八两章,详细论述了北洋后期中国与波斯、希腊、芬兰、波兰、比利时、西班牙、英国、法国、墨西哥、秘鲁、越南等国的“平等订约”或“到期修约”的历程。单独看,各章皆独立成文,论述专而深;贯穿看,各章又融为一体,使人一眼明了北洋修约历程之全貌。
在研究方法上,值得注意的是,唐书格外重视“外交史”与“国际法”的对话,纳入国际法的视野,探索诸如条约修改与废除的法理论证,中国对“情势变迁”原则的运用与发展,以及中国修约的法理症结、修约努力对国际法理的冲击等问题。这种研究尝试,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其意义之大,毋庸讳言。
重建国人对北洋修约史的真实记忆,抹去那些被宏大革命历史叙述所遮蔽的表层记忆,是唐书的一个基本关怀。然而,革命时代留给人们的以“反帝废约”为核心的集体记忆,也是另一种真实的集体记忆,至少它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希冀一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集体心态。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唐书并没有粗暴地否定这种被民族主义激情和革命理想所笼罩的集体记忆,他说:“本研究之目的,不在作翻案文章,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践踏他人珍视的传统。过去革命宣传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已在历史上留下光荣的印记。”另一方面,唐书坚守外交史研究要“历史化”与“学术化”的原则,来重建国人有关北洋修约史的真实记忆。
重建真实的历史记忆
综合来看,唐书虽是一本关于北洋修约史的学术专著,也兼具重建国人有关此段历史真实记忆的社会关怀。过去,以“反帝废约”为主导所建立的民族集体记忆,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记忆。此类记忆有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这是不容否认的。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打破列强对中国的条约束缚,完成国家的独立与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客观上需要增强人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感。自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深入人心,在近代中国人脑海中,没有哪个词能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
因此,构建以“反帝废约”为核心的民族集体记忆,不仅与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也是用来加强民族认同的绝好政治资源。伏尔泰有句名言:“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通过塑造反帝废约的民族记忆,会使新政权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也意味着,新中国政权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
然而,世易时移。新中国成立已逾60余年,今日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与往昔大不相同。新的时代需要构建新的民族集体记忆。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以宽广的胸怀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接纳四方来客。如唐书所论:“过度单调、贫瘠的历史记忆,限制了迈向大国的想象空间。本书希冀能丰富国人对过去的理解,摆脱过时的政治神话的束缚,大步迈入21世纪。”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本文编辑 宋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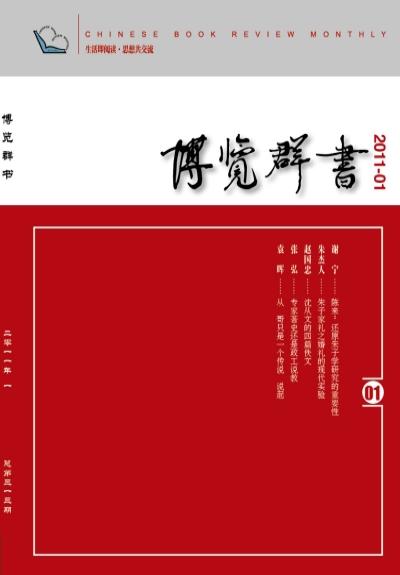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