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晨
古巴的烟草与蔗糖
古巴带给世界两种至“纯”的产物:烟草与蔗糖,前者的“纯”浑然天成,后者的“纯”巧夺天工。
古巴的哈瓦那雪茄享誉世界,西班牙语中的雪茄烟便被取名为“纯粹的香烟”(cigarro puro)或索性直接以“纯”(puro)相称。烟草是地地道道的美洲产物,在欧洲同美洲相遇之时,西班牙人最先便是在古巴岛上看到烟雾的缭绕。从此,烟草便一发不可收,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每一个角落。雪茄烟制作工艺纯粹。最为传统的雪茄只有烟叶这一样原料,只不过烟叶也有外卷叶(capa)与烟心叶(tripa)之分。而剪采下来、经过重重处理之后的干燥烟叶,会在工人手中不断卷曲、螺旋形缠绕,以外卷叶包裹烟心叶,最终成为真正的古巴雪茄——并非如“仿冒者”那般将烟叶切丝、加香加料并最终以盘纸卷制成形。尽管材料单一,但专业品鉴家相信,一个烟盒中不会有两支完全一样的雪茄。
与烟草相比,古巴蔗糖之纯粹便完全是另外的概念。甘蔗本不属于美洲,却在欧洲殖民者的精心谋划之下在古巴蓬勃生长,迫使这种外来作物挑起古巴经济的大梁。甘蔗加工的终极产物的确是纯净的蔗糖,但从棕黑的甘蔗作物到白色的蔗糖颗粒,其中充满复杂的机械化生产程序——压榨、过滤、离心、结晶……,每一步都需要机器和人力,整个过程都依赖化学和物理,但是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剔除甘蔗中所有破坏“纯洁”特性之杂异。然而,真正能够让蔗糖得以从棕色颗粒变得白净的过程,却往往并非发生在生长甘蔗的这片安的列斯群岛,利润最高的步骤常常要在北美大陆完成——古巴提供的仅仅是用以实现“提纯”的原材料。尽管纯糖的制作步骤繁复,但是一粒同另一粒、一包同另一包,带给人的味觉体验却总也别无二致。
在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 Fernández,1881-1969)的笔下,原本毫无交集的烟草先生和蔗糖女士在古巴就这样奇妙相遇了。二者在历史上都一度成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受到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人的一致追捧。尽管它们共同占据着古巴的土地,共同呼吸着加勒比海上的空气,共同撑起这个国家脆弱的经济,但是它们之间,却也永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烟草在古巴的历史悠久绵长,不仅能够用作药物,还能用于民间仪式或官方庆典。古时候的印第安人会将干燥的烟叶点燃,以此来供奉信仰的神,希望能借此物来平息神灵的愤怒。现代人虽然依旧试图通过烟草来抚平烦闷与哀伤,却往往也希望借此物来激发灵感和幻想。烟草对人的身体多有损害,在17、18世纪的欧洲也常被视为道德与社会进步的阻碍,但烟草的制作和买卖却时常在暗中进行,且呈现蓬勃发展之态,仿佛依靠烟草便可逃避现实的纷扰。
蔗糖在历史上则大不一样,它原产自东方。应许之地,牛奶与蜜。曾几何时,在西方人对幸福的想象当中,并无蔗糖的一席之地。但是,十数个世纪过去后,在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中,公主头脑中所能想到的三种甜,除了蜂蜜和牛乳,已经又多了一味蔗糖。糖所能提供的,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除了令人感到快乐的味道,便是人类生命活动当中最为重要的能量;然而,对于欧洲上层权贵来说,蔗糖却长时间代表着权力与威望。当蔗糖在欧洲的传播尚不够普遍,购买、使用甚至浪费蔗糖的方式与数量就足以表明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而当底层人民有条件享用蔗糖,它便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压榨蔗糖工人劳动力的诱因。
烟草与蔗糖,一个本土,一个外来,到底哪一样才最能代表这个加勒比国家? 古巴的基调,到底是传统,还是现代?
美味的古巴辣味炖汤
奥尔蒂斯在哈瓦那大学的一次演讲上,曾将古巴民族的特性比作当地传统菜肴——辣味炖汤(ajiaco)。这是一道配料丰富、历史悠久的特色菜品,美洲丰富的根茎类蔬菜配上切成块状的多种肉类,加入沸水之中共同炖煮,待熬制成浓稠的汤汁,佐以盐、胡椒等调味品,再加入最为重要的配料——古巴特色辣椒(ají,这道辣味炖汤正是因其而得名),便可供大家畅快享用。
食材的寡淡,甚至是散出的异味,往往都需要辣椒来掩盖、来刺激食客的味蕾。煮熟的汤羹不止足够果今日之腹,往往也还能用作明日之“老汤”。作为远古时期印第安人餐桌上唯一的菜肴,辣味炖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续水、加料、熬煮、食用的往复循环中不断延续,同时,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古巴地区的辣味炖汤中加入的是印第安人特色的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等植物食材,但是那时用以熬制“高汤”的肉类恐怕无法被今日的大众口味所接受——硬毛鼠、鳄鱼、蟒蛇、海龟都可以被切割成块、放入锅中。15世纪末到来的西班牙人带来了新鲜的牛肉和猪肉,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美味腌肉;在半岛人之后到达古巴的非洲人,则带来了新的食物——香蕉,还有他们的烹饪技巧;而其后随亚洲人一同进入古巴的,便是欧洲人渴望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香料;再后来,北边的美国人也希望用他们规格统一的家用厨房器械简化菜肴的整个烹饪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过不同厨师之手,辣味炖汤的原材料、口味甚至各个烹饪步骤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始终不变的唯有熬煮浓汤的这口古巴大锅以及调节烹煮火候的这抹加勒比艳阳。
奥尔蒂斯将古巴人的特性比作这道辣味炖汤,因为无论是“古巴民族”还是他们所创造、所信仰的“古巴文化”,都不是一道现成的炖菜,而是在制作这道炖菜之时持续不断的烹饪过程。从生火、打水、上锅的那一刻起,这道菜肴持续不断地被烹饪再烹饪,在古巴这只深不见底的敞口大锅中,总有汤羹不断被舀出,总有食材不断被加入,也总有物质不断在生成。众多异质性的物质在这里咕嘟咕嘟地冒泡翻滚,逐渐融为一体。辣味炖汤的成分不断发生着改变,就像组成所谓“古巴民族”的所有团体、个人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一样,这或许和厨师的喜好有关,又或许取决于季节的变换。辣味炖汤的味道和浓稠程度也常常不尽相同,就像那些构成“古巴文化”的各个元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也并非整齐划一。
如果所谓古巴人民所代表的是同古巴这一地域相关联的人类群体,那么所谓古巴民族的属性、古巴民族的文化特性就是一个一刻都不曾停歇、一直处于运动之中的变量,永远在变幻,无法被定义。
奥尔蒂斯的“文化互化”理论
在20世纪初期的古巴乃至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文本叙述当中,被人们用来探讨民众身份的往往是血缘,是种族。无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们时常都在关注不同血统之人的历史记忆与表述——直至今日,依然如此。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印第安人、非裔美洲人……,不同“种族”之间的遗传和混合共同交织出古巴“民族”的表象,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稳固仿佛建立在不同“种族”之人的和谐共处之上。然而反之,一旦国家出现任何或大或小的问题,首当其冲被追究的也会是生活在同一社会当中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曾几何时,一个能够囊括拉丁美洲血缘现实、符合拉丁美洲人身份想象的“共同种族”——如墨西哥思想家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 Calderón,1882–1959)所言之“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也在不断酝酿。但是显然,对于古巴人以及其他拉丁美洲人来说,还有比“种族”更加适合作为讨论民族身份的选项,那便是“文化”——具体而言,应该是不同“文化”接触的过程和“文化互化”(transculturación,即通常所译之“跨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奥尔蒂斯在其著作《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1940)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互化”这一概念,用以解析所谓的古巴文化、拉丁美洲文化,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文化的特征与生成。实际上,古巴文化以及古巴族裔,二者有一共同特点,那便是无法界定所谓的古巴特性——文化和族裔当中的异质性就是古巴的特性。就像烟草和蔗糖,尽管这二者在方方面面都差异巨大,但是,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们都一直共同掌控着古巴经济的命脉,共同交织出了古巴作为殖民地的过去,也在影响着古巴作为独立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古巴的历史就是错综复杂的文化互化之历史。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各个印第安人部族之间、岛屿同大陆之间已经开始有了人员的走动、文化的互动。15世纪末开始疯狂涌入美洲的西班牙人——准确来说,是来自卡斯蒂利亚、安达卢西亚、加泰罗尼亚等地的半岛人——从撕裂的“旧世界”来到了充满希望与未来的“新大陆”。他们一边向古巴移植着自己熟悉的物种、语言、宗教和制度,一边实现着曾经无法企及的梦想,一边又尝试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舒服。而来自不同地区却统统被欧洲人当作“奴隶”对待的非洲人,也被带到了古巴的土地之上,许多人被送去了甘蔗种植园或是制糖厂。他们也不得不开始经历愈加艰难的文化调适过程。再后来,无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来自太平洋另一岸的“东方”(欧洲人所构建之“东方”实则位于美洲之西边)人,无论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旅人们远离故土、背井离乡,固然经历种种不适与忧伤,但始终未曾放弃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梦想。正是这些不断加入、不断跳出、不断运动中的元素,共同熬煮出那道古巴经典的“辣味炖汤”。
奥尔蒂斯提出“文化互化”的概念,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希望以此取代此前在拉丁美洲文化接触研究领域更多被用到的“文化同化”(aculturación)这一术语。这也是为何我更加倾向“文化互化”而非“跨文化”这一翻译方式的原因。实际上,在相遇的两种文化或是多种文化之中,难免会有所谓先进、强势、处于决定地位的一方;同样,在相互接触的个人、集体甚至国家之间,也往往会有更具权威、优势和力量的一边。但是,就好比当今的美洲文化并非欧洲文化的复制品一样,即便是更具主导权的一方,也无法完全掌控未来文化的走向,就像代表古巴的烟草和蔗糖,前者属于本土,后者来自他乡。相遇的烟草和蔗糖,共同引领古巴的风向,但两者也都不再和从前一样。
奥尔蒂斯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兰裔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在为《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写就的序言当中同样谈道:“文化互化讲求的是一个过程,一个全新、复合且复杂的实体浮出水面的过程;这个全新的实体并非是多种不同特征积聚在一起的成果,也不来自于任何形式的拼接和镶嵌,而是一个新颖、独特并且完全独立的非凡个体。源自拉丁词根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ción)这一词汇便成为了描述这一过程的新术语,它并不包含某一种文化‘倾斜’向另外一种文化的含义,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二者均为主动方,二者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二者共同为文明新实体的创设携手向上”。当然,二者也都要收敛自己的部分锋芒。
纯与杂的回响
甘蔗在美洲的种植是为了满足欧洲人对甜味的享受、对高额利润的追求,而制糖厂的设立则需要大量来自非洲的廉价劳动力。这些疲惫不堪的劳力很快便领悟到烟草的奥秘,他们学着印第安人吸烟,也学着在甘蔗园种植烟草。但是最终,最优质的古巴雪茄烟还是成为了欧洲人的消遣。“纯”与“杂”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
在“新”“旧”世界相遇的初期,即便是双双远离自己长久以来生活的故乡,欧洲人和非洲人在美洲生活的境遇也大不一样;尽管都处于被奴役的境地,被贩卖船只运送至美洲的黑人奴隶也和印第安本土之人有很大差异。在古巴——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一样——种族和地域时常被用来讨论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但是文化这项要素,却应该成为整个古巴民族强有力的黏合剂,成为描绘古巴人的主题。所谓古巴文化,并非一个准确的定义,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加入其中的各个成分、各个要素始终都在变换,始终都在实践“互化”这一过程,或激烈或平缓,或复杂或简单。
古巴的烟草、蔗糖和辣味炖汤——在这纯与杂之间,古巴的文化、拉丁美洲的文化,乃至当今全球体系下人类的文化,哪一个不是在变换着音调、产生着回响?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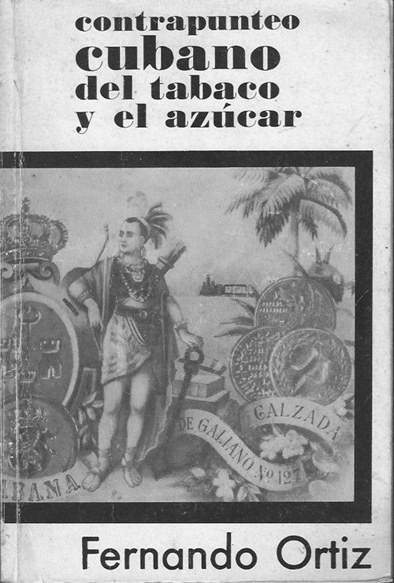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