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由我的博士导师洪子诚先生牵头,组织一批作者想做一套丛书“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书系”。讨论选题时,洪老师提出应当重新讨论40-50年代这个文学转型期。在当时的文学研究界,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在40-50年代之交发生交替的历史情形,形成了一些定型化的看法,普遍认为当代文学取代现代文学是一种政治外力干预的结果。这种主流看法背后包含着对两种文学形态和学科方向的特定理解,即当代文学是一种政治性文学,现代文学则是一种独立的纯文学。洪老师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遮蔽了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值得重新讨论。而我那时对20世纪这个革命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领下这个题目。最终,我决定用处于不同历史位置、具有不同创作风格的五个作家个案,来立体地勾勒出这个巨变时期文学的总谱系。于是有了《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一书的写作。
我一直将这本书视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真正起点。通过这次写作,我才真正体味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领悟到我们可以通过与研究对象的精神交融而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思想视野。书稿选择的五位作家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他们的人生际遇、精神世界和文学体认,都不再仅仅作为知识对象,而是一个个我能与之对话的主体对象,给予我多种文学、思想和精神的滋养。因为有这样的体认和感悟,因此,书中的五位作家并没有随着书稿在2003年的出版而被我遗忘。此后,他们再没有离开过我,而成了我不断阅读、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构成了我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当初选定这五个作家时,主要考虑的是他们创作风格和思想取向的差异性和代表性,但要同时消化五个个性如此鲜明的作家,还真是需要挺大的胃口。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每每向戴锦华老师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的读书心得。谈论对象虽不同,但我投入的状态却没有变化,这使戴老师有一天突然开玩笑地说:你真是研究一个爱一个啊!我这才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花心”。“花心”对于具有史学风格的学术研究而言,或许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的研究者一辈子钟情于一个研究对象,使自己与对象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那是一种研究路径。但前提是对象本身能够提供足够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缺点可能是无法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更好地定位对象和自我。而我同时研究多个对象,又对其中的每一位保持“理解的同情”,是希望能在深入对象和历史格局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
二
沈从文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花费时间最少,但实际上接触时间很长的作家。我从本科时期开始阅读沈从文作品,不过与一般人关注那个写湘西牧歌的沈从文不同,我一开始走进的是40年代那个写作《烛虚》《长河》的“现代主义者沈从文”。大约是1993年,我还在读本科三年级,完成的第一篇论文是用40年代的沈从文与米兰·昆德拉、马丁·海德格尔,讨论文学与存在的意义。阅读昆德拉和海德格尔是那时文学青年的风气,我把这三个人放到一起,并不算奇怪,而是学术风气使然,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之所以关注沈从文现代主义创作的缘由。1994年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讨论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这在当时,算是比较早地关注沈从文这个时段的研究了。1996年,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钱理群老师开设了一门“40年代小说研读”的课程,我在课上提交的讨论文章《沈从文〈看虹录〉研读》,颇得钱老师肯定,次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如果追溯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之路,沈从文在我早期的关注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不过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要回答的问题是:沈从文为何会成为40-50年代这个历史巨变期的“唯一游离分子”?他不能适应新社会新话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沈从文已成为“因政治外力干预而中断写作”的一个典型人物。但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我更想强调的是,沈从文这个时期的表现更是他创作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40年代的创作探索,实际上是一个作家在构建庞大思想体系时遇到的精神危机的体现。因而他在40年代后期谈论“穷”与“通”,在50年代谈论“事功”与“有情”,在60年代谈论“人”与“我”时,也包含了一种超越个我而努力地包容整个世界的努力。只是,这种悲悯阔大的胸怀,不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而实践于他的文物研究中。因此,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更关注的是沈从文形象的变化:他30年代作为“京派”领袖的意气风发,40年代思想探索的某种超人气质,50年代的落寞与彻悟,构成我理解和阐释40-50年代之交沈从文的主要线索。
与沈从文的写作故事不同,萧乾、冯至、丁玲、赵树理这四个作家,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虽非初次相遇,却是第一次把他们作为研究的对象。在关于40-50年代作家的大量阅读中,我之所以选定萧乾作为分析的第一个个案,是考虑到他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经验,特别是他在那个转折年代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日本学者丸山升如此评价这个时期的萧乾:“他面临的确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且,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自29岁到36岁——他几乎都是在欧洲度过的,因而具有些许独特的体验。”这与我一开始就想把40-50年代中国作家的讨论放在全球视野中展开分析有内在的契合之处。讨论萧乾的欧洲经验和思想变迁,特别是他在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遭遇,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革命的世界性背景。1949年,萧乾实际上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英国剑桥大学教书,可以留在香港当记者,可以回到上海或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也可以从事文学创作。在这多种可能性中,萧乾为何选择了看起来自由度最小的一种,即回到北京从事新闻写作?这是我在萧乾这一章中着力处理的问题。由此,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左翼知识界的思想分歧、巨变时代作家的个人身世和自我认同等,得以在萧乾这个个案中凸显出来。
在考虑国统区作家个案时,除了沈从文,另一个选择对象是作家兼学者冯至。冯至在40年代走了一条几乎与沈从文相反的路线:他从一个最具个人风格的作家,转变为顺利地融入“集体的时代”的主流作家。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其中包含的个人与时代、个我与集体、欧洲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学与革命等问题,呈现出的是一种难以仅仅从外观上理解的历史经验。因此,冯至这个章节,我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与人格塑造写起:从20年代步入社会的失败,到30年代德国思想的滋养,再到40年代在战乱的昆明获得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使他既不违背自己的思想诉求又能顺利融入大时代。
在冯至的思想里,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核心问题是:如何以个人的方式超越个人主义,如何通过自我修养而通达集体时代?在我的理解中,帮助冯至从个人通达时代的桥梁,是里尔克、歌德与杜甫。这其中包含着个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跨越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这种立足自我又超越自我的思想路径,对于始终在文学与政治的简单二元对立框架中理解当代中国革命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矫正。回想起来,冯至一章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最大收获之一。他不仅使我从狭隘的当代文学视野中跳脱出来,站在世界文学与政治哲学的高度观察大时代的变动,而且也为我理解个我的生存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思想者的意义是不受限于时代的,冯至的中年体悟、生命哲学正包含了这样的内涵。
三
在考虑与40-50年代新中国同时崛起的解放区作家时,本书选择的是丁玲与赵树理。实际上,这两个作家才真正是我的专业本行即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但一般的讨论,往往强调他们作为“作家”而非“知识分子”的特点,偏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较少从思想史视野考察他们精神特质的形成、文学创作的初衷、基本的思想诉求和所接纳的文化资源。本书以作家为主体考察20世纪中期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过程,事实上是一种基于思想史视野的考察方式。从这两位作家提炼出的相应文学问题序列,则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当代文学如何确立自身的规范内涵。从表面看,这两个作家是如此的不同,丁玲之“洋”和赵树理之“土”是明显的,但把这两个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却正好能从横的世界脉络和纵的中国脉络,呈现出20世纪中国文学最宽广的历史维度。
丁玲之“洋”,与她自登上文坛起就始终以“摩登”的姿态站在时代潮头有密切关系。她的思想资源、社会阅历、自我认同、文学素养等,无一不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先锋性现代思想潮流相关。这也使她与中国革命呈现出一种高度自觉而又紧张纠缠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从丁玲这一个案,显示出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与文学实践的激进现代性内涵。这也需要处理丁玲如何成为作家、如何向左转、如何到达延安、如何经历自我改造完成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如何经历40-50年代转折期并主导当代文坛的建制……可以说,丁玲自身就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史,也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一种肉身化形态。在经历40-50年代转折之前,她已经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创作个性的成熟作家,经受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考验,而将自我提升到另一更高境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作家主体如何伴随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我曾在文章中将之称为“主体的辩证法”。
从丁玲这里,正如从冯至那里的获益一样,我领会到的是一种新的生命哲学,一种“在历史中生长”的能力。人的主体修养和精神世界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可以通过现实实践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与境界。有人问晚年丁玲如何看待当时的处境,她答曰:依然故我。经历了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容衰毁誉之后,而能坦然承认依然故我,这是一种生命力强悍的表现。不过,丁玲的特点实际上并非仅有“故我”,毋宁说是在对“新吾”的不断探索中,始终不丧失其作为作家和思想者的主体意识。有故我即有新吾,这两者并非不可兼容,关键是新吾能在包容故我的同时又超越故我。丁玲从20年代上海的时髦女作家,到30年代延安的明星作家,到40年代赢得世界声誉的社会主义作家,到50年代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与受批判对象,再到80年代的复出。这些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实践的“活化石”般的呈现,也是她在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中艰苦地自我战斗的缩影。
四
本书写到的五个作家中,初版本出版之后,我与丁玲“重新相遇”的故事最值得一说。初版本中关于丁玲的两章,实际上没有摆脱学界对她的刻板印象。一是将中国革命与丁玲个人的生命及文学实践对立起来,另一是没有理解丁玲精神主体的可塑性与生长性。对于丁玲这样的始终与中国革命共生共长的作家而言,革命并不是她身外的对象,她所有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实践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的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革命的辉煌期还是低潮期,她一直坚持从革命的总体大局和发展前景来谈论个我与集体的关系。这种气度和心胸并不是每一个20世纪作家都能有的,而对于我这样的在80-90年代氛围中长大的一代人,则实际上是陌生的。
我与丁玲研究会的第一次接触,是2004年去湖南临澧县参加丁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转折的时代》初版前后,我把丁玲部分重写成论文发表。大约因为此,丁玲研究会会长王中忱老师注意到我,并把我当成新秀邀请去参会。不过那次我完全没有融入会场的氛围。悬挂在临澧县大会堂的丁玲遗像,在我当时的感觉中,不过是逝去的20世纪历史的一个象征。印象深刻的,倒是在王中忱老师率领下,一群人去看丁玲在临澧县蒋家的故居。故居已全然不见踪影,只留下两块埋在土里的石碑。门前有个水塘,据说就是丁玲小说中写到的田家冲(当地名黑胡子冲)。南方乡村正午的阳光照在橘树林中,我们穿过丁玲很小便离开的故乡的山地,像一群散漫的游客。
我第二次参加丁玲研究会的活动是2014年。这次是去湖南常德参加丁玲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恰逢李向东、王增如老师的《丁玲传》刚刚出版,他们带了十多本到会场,我幸运地分得一本。书里呈现的那个活生生的丁玲抓住了我,我整整一上午坐在宾馆房间的窗前,一口气读完了《丁玲传》。这本传记回答了我关于丁玲的许多疑惑和问题,也更新了我对丁玲的认识。此后的时间里,王中忱老师时常召集我、何吉贤、程凯等年轻学者,与王增如、李向东、涂绍均、解志熙等老师一起吃饭聊天。那时,我才有机会听他们聊起活着的丁玲。他们管晚年丁玲叫“老太太”,说起80年代与她接触、一起办《中国》杂志的往事,他们津津乐道,对丁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亲近。一个已经逝去的人,能使曾在她身边生活过的人如此长久地怀念她,仅就这种人格魅力也使我对丁玲兴趣盎然。我慢慢感到,20世纪革命历史开始在丁玲身上活过来,以我们这代人能够理解和触摸的方式,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可以说,2003年书稿的初版只是我与丁玲相遇的起点,我对她更深刻的理解和体认多是在初稿出版之后发生的。在这次修订中,丁玲两章我做了几乎全盘的重写。重写是觉得自己此前对她的理解过于肤浅,即便一时还不能完全将新的理解理论化,我也需要在书中勾画出新的思考线索。我越来越意识到,丁玲实际上是一个在精神高度上超越了我们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用一般的文学观、历史观和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刻板印象来谈论她,实际上是小看了她。
五
与丁玲的“洋”相比,赵树理的“土”代表的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另外一个发展脉络的极致。他的创作道路与作品,常常与“乡土中国”“农民文化”“民间文学”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从中国乡村大地内部生长出来的现代形态。他是中国的,而且“太中国”了。但日本学者竹内好却在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称他是“新颖的”。竹内好认为赵树理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意味着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内涵甚至比丁玲这样的摩登作家更有独创性。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一种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奇谈怪论,特别是在以追求西方现代性为主要规范的80年代“新时期”。那时,赵树理被视为“保守”“落后”“封闭”的50-70年代文学的象征。他甚至没有资格跨入现代作家的行列。我对赵树理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赵树理的作品难以唤起我的情感投入和共鸣,但他的文字、叙事、结构的精致却让我不得不另眼相待。他像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品种,让我这种文学青年无从下手。我重新认识赵树理的机缘,是90年代后期,当我有机会在一些跨国跨区域场合谈论中国文学,并且自觉地在全球性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时,赵树理的独特意味开始显现出来。他的陌生感并不是“没有文化”,而是一种无法用西方现代性所能解释和把握的中国文化。
赵树理为我打开的是两种视野。其一是超越知识分子的主观视野。赵树理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不是都市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设想的读者是广大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他的作品是预备让识字的人看,并让识字的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在这里,文学或文字这个媒介,是中国几千年生活传统所形成的“活文化”在当代转化的产物。可以说,赵树理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机制中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从这个层面,赵树理是激进的,又是传统的。“激进”的一面在于,超越知识分子阶层的视野而使文学最大限度地普及化大众化,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贯追求。当代文学作为人民文艺,对于以作家文学为主体的现代文学的超越也正表现在这里。“传统”的一面则在于,从一种长时段视野来看,中国历史唐宋转型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以市民阶层为对象的(拟)话本小说与戏曲(杂剧、散曲)的出现,越出了文人群体的言志或载道传统。事实上赵树理基于小说和戏曲的文学实践,也使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颇多批评。如果可以,或许他更愿意把自己接续到唐宋转型这个更长的“现代”源头上去。
这也涉及赵树理为我打开的另一种视野,即超越20世纪的现代性视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实践总体地受限于西方式现代,赵树理可以视为这种主流现代观的一种“反现代”形态。他对乡土中国的切身体认和深入理解,提供了这种超越性文学实践的可能性。仅仅站在20世纪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这一点的。只有对现代性本身产生反思、批判的自觉意识,也就是穷尽了20世纪西方现代性之后,赵树理文学的特殊意义才能显现出来。
修订版中赵树理的章节没有做很大调整,但我的研究思路和立场越来越明确。以前讨论赵树理,总想着要为他的现代性持一种辩护姿态,但现在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这种现代性内涵用一种理论化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与我对丁玲的研究经历相似,21世纪初期的几年里,我也开始有机会接触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老师们,并到山西沁水县、晋城市等去参观和开会。有许多书本之外的有趣发现。比如在晋城剧院观看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才更了解到赵树理的家乡与宋代杨家将故事的关联,比如和当地的老人闲聊,才发现他们说话的腔调,大概正是《小二黑结婚》里的口语……不过说实在话,在跟当地视为有文化的学者、文化干部对话时,我还是觉得有些吃力。我由此反过来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在都市和学院中生活的中产阶级女性所能看到的视野的限度。不过,正是在对作为庞大基体的乡土中国的接触中,在彼此接触的对象化反思中,我开始更自觉地思考何谓“中国”何谓“现代”。这也是赵树理给予我的总体启示吧。
六
书稿的初版本2003年12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关注。我也因为这本书而被许多同行视为研究40-50年代转折问题及五位作家的“专家”。这次书稿的修订重版,保留了初版本的基本框架和大部分内容,但在文字的打磨、章节标题的设计,特别是基本研究思路上,有很大变化。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考虑。就读者的一面而言,我感到人们看待和理解这五位作家的方式,与我最初写作的21世纪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某些尚未得到明确讨论的大变化。那时,这五位作家还是正在展开的现当代文学学科探索的一部分,阅读者和研究者也多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讨论他们;而现在,这些作家已然成为经典,被视为文学史的一部分了。就前一种阅读要求而言,人们更多地关注专业化的文学研究这个面向,而就后一种阅读体验而言,更希望将其视为现代中国普遍性的文学资源,从中获取超越时代的人文与思想价值。
我作为研究者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初版更多地从专业的文学史研究角度,尝试立体地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段中作家的现实遭遇和精神体验,那么修订本则力图在文学史描述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回应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基本问题。这个变化过程,事实上也是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在基本态度和研究方式上发生的调整。这是一个“走出20世纪”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将20世纪文学资源化的过程。如果意识不到这个变化,恐怕就很难理解21世纪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些新的特质。在修订过程中,我关于五位作家的讨论重心,从文学史转移到思想与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创造出能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分享的普遍经验。出于这样的考虑,修订版的书稿定名为《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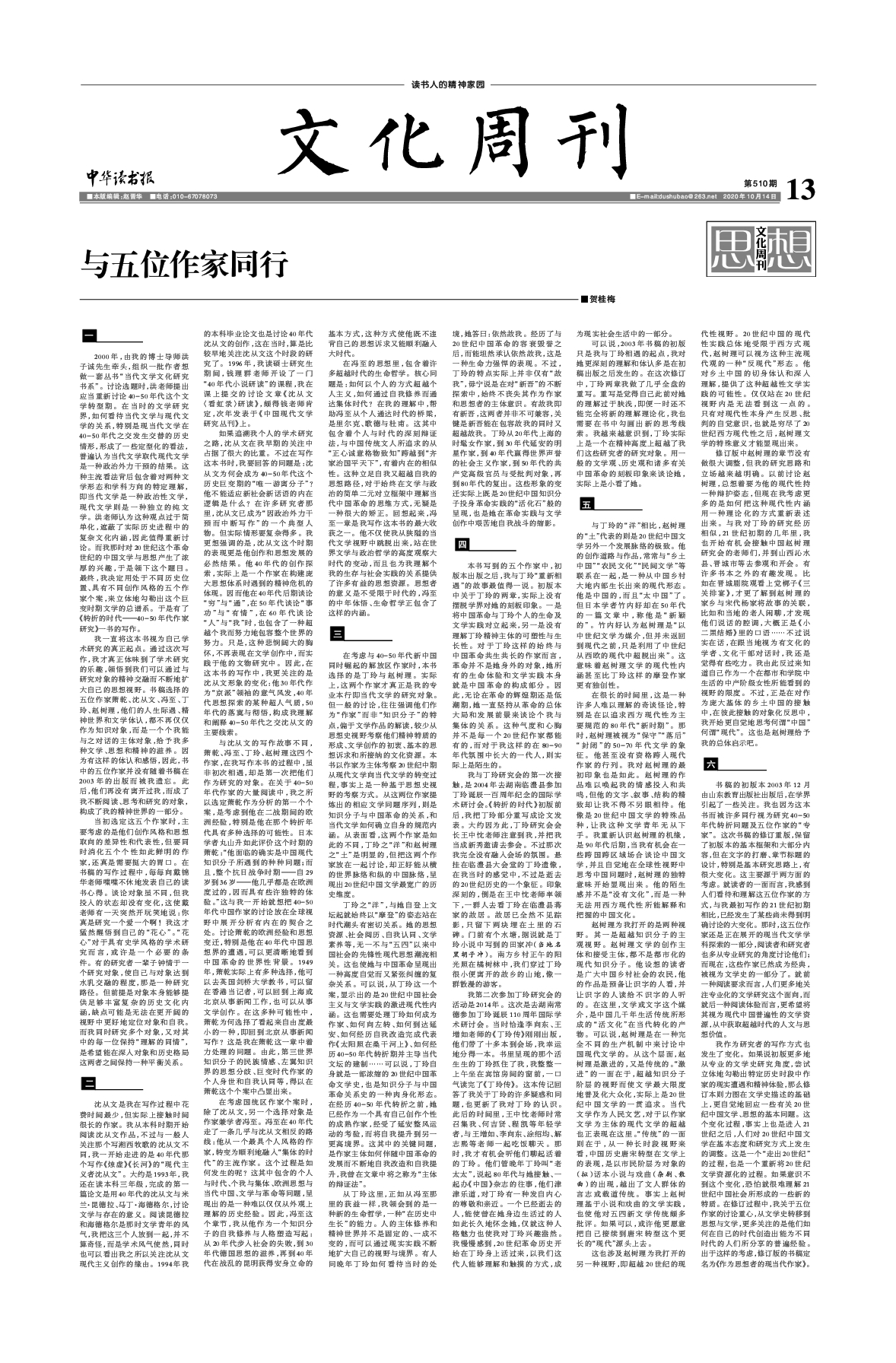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