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不止一次提到《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现在觉得好像还有些话可讲,可以放在我的随笔集《云集》的起首。常听人提起“古典范儿”,但若只是穿汉服招摇过市之类,则岂止是皮毛,简直有点可笑了。我想假如真有古典范儿这码事,大概也是《庄子》这番话所说的意思。我们尽管生活在当下,吃汉堡包,坐地铁,用iPhone,发微信,但与遥远的古代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孤独,惆怅,悲痛,快乐,正与古人某一时刻相去不远,彼此自有心灵相通之处。
我在《惜别》中引过《礼记·檀弓》的一节:“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这里特别触动我的是,子贡听到孔子唱歌,觉出“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但孔子仍然不免抱怨“赐,尔来何迟也”。无论预感即将失去老师,急于与之见上一面的子贡,还是知道“予殆将死也”,希望与学生一起多待一会儿的孔子,他们的心情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处于同样境况时,与他们的想法并无二致。
《檀弓》的故事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一并来读,或许更有意味:“孔子葬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子赣即子贡。想起孔子死前不久他“遂趋而入”,可知心里实在放不下对老师的这份深厚情感,比别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缓解。打个比方,家里来了客人,告别时主人或送到家门口,或送到电梯口,或送到更远的地方,子贡之于孔子,就是那个送得最远,一直依依不舍的人。
孔子师徒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年代,为什么我们回过头去,还能看到这些遥远的人呢,因为他们其实是与我们相同的人,对人生和世界具有类似的感受和认识,所以才能产生共鸣。也许只是相视一笑或一泣,甚至相对无言,然而却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纵观人类文明的进程,技术、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非常大,也非常快,不过“人心不古”之外,还有“古风犹存”。也就是说,一代又一代人过去了,其间确有一种不朽的东西,它永远存在,只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了而已。我所理解的古典范儿,就是承认我们可能重新体验古人的想法、情绪,以至不得不一再复述他们实际上早已讲过的话。
我曾以“历久而弥新”和“放之四海而皆准”来描述经典作品,因为它们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今想想用来形容古今相通以及中外相通的此类情感或精神更为恰当。譬如我们看高更的画,读《安娜·卡列尼娜》,往往也会受到感动。无论如何,大家同属于整个人类,文明是同一个东西。这也是我花费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的原由:希望尽量结识古今中外的智者,了解他们感受如何,想法如何。虽然也许藉此发现,在很多方面无法再以所谓“原创者”自居,只是对远方传来的我们的心声有所呼应罢了。我偶尔写点小文章,也不过是将这种呼应记录一二。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有云,“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此之谓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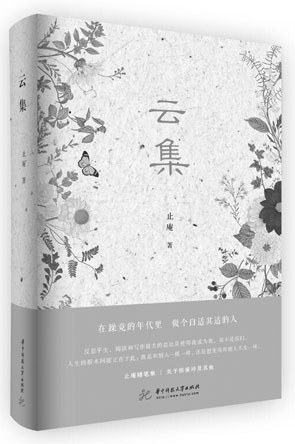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