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背面傅粉”,是传统诗论中取自绘画技巧之手法或概念,成为分析诗歌表现手法及其艺术效果的一个专门术语,意指从反面的立场或相对的着眼点间接下笔描写,从而透过反衬的效果,使正面的主题获得进一步的烘托与强化,其义往往与“从对面说来”可以相通。在唐代诗坛上,将此一技法表现得驾轻就熟的诗人,首推王维;而严格言之,王维诗中所表现的“背面傅粉”与其说是一种来自艺术考虑而采取的创作技法,不如说是一种来自人格形态的自然牵动的结果。从《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寄崇梵僧》《山中寄诸弟妹》《送元二使安西》《相思》《送杨长史赴果州》等多篇展示“背面傅粉”之手法的典型作品中,可以分析出王维在情感表现上的特殊风格。
先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为聚焦,其曰: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题下原注:时年十七)
作为王维加注年龄的十首少作之一,本篇显系反映少年诗人孤身于长安奋斗之余思亲念家的题材。在一般的情况下,如王维般“闺门之内,友爱之极”的诗人若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直接而正面地写出自己强烈的思乡情怀之后,接着通常会继续进一步重笔浓彩地抒发己身的客居之悲与思亲之烈,以充分展现异地怀乡之主旨;尤其在“倍”字所寓含的情感已达饱涨的临界点之际,只要让情感的分量再多增加一分一毫,便会冲垮理性的藩篱而倾泄无余,以致陷溺在羁思旅愁的翻腾之中而歌哭淋漓,产生诸如“归思欲沾巾”(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宋之问《新年作》)、“恨别鸟惊心……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与“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曹丕《杂诗二首》之一)之类的强烈字眼和动荡情绪。此乃因诗人者,深感于哀乐也,故形诸笔墨时总是表现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
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的文学常态。
然而,王维的独特处就在“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句乍乍触及那情绪满涨的制高点之际,却随即宕开笔墨,远调笔端从远方兄弟之处境着眼,以间接方式设身处地想象至亲至爱的手足于登高时“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缺憾,而间接传达出羁旅他方的自己在家族聚会中缺席的落寞。入谷仙介(1933—2003)认为,“后半的设想之词,在即兴创作的现场可能会获得喝采,然而意思仅仅止于字词表面,稍感浅露。所以胡仔评它不如杜甫之句,并不为过”。但后半两句是否真为“意思仅仅止于字词表面,稍感浅露”,因而“不如杜甫之句”,恐怕大可商榷。
事实上,正是后半两句才越出前半两句所触及的一般情感体验,而真正显露或建立了王维独特的个人性格模式,亦即在“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情感饱涨至临界点的时刻,王维并没有像一般诗人一样,进入情感风暴的中心而陷入激情状态,并顺任情绪的浪潮而倾泻无遗,极力渲染思乡的苦楚与辛酸;反而在激情溃堤的临界点之前就抽身而出,并调开笔端,透过“从对面说来,己之情自已,此避实击虚”的叙写方式,转向远方亲人的角度来着墨,以至由第一人称的大吐苦水变为对他者的同情与了解。但在取效《诗经·陟岵》“不写我怀父母及兄之情,而反写父母及兄思我之情,而我之离思之深,自在言外”的做法时又更进一步,即使是描写故乡亲人对自己的思念,也未曾使用情绪化的形容,所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描述的是客观的现象,而非情感的翻腾;着重在“知”所代表的“了解”,透过设身处地来省察情感的行为状态,而不是在“感”的层次上扩大自己的情绪反应或情感浓度,其结果反而是“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正是通过“从对面说来”的间接笔法,在“两面俱到”的宏观视野下,充分曲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幽隐情衷。如此一来,其笔调便在表面的简易平淡中蕴蓄了大量情感,那念念在彼的深情、两地牵系的血缘纽带,都表现得十分深婉有味,却一点也没有泛滥,正可谓“深于情而不滞于情”者,可以说是“背面傅粉”的极致。
试看“遥知”二字,一方面是以“遥”的距离感将即将在临界点上灭顶的自己抽离出来,从眼前“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李白《远别离》)的深渊中宕开,而免于丰沛的情思被激荡到喷薄不可自抑,以致一头被情绪按倒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以“知”字表现出一种来自理性的力量,将先前置身于情感感受中的处境转移到观照与省察的状态,因此不再是热情洋溢的陷溺沉沦,而是清明冷静的跳脱旁观。而且这般由“思”而“知”的微妙置换,更一贯直下地透抵末句,那“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句虽然以“遍插”与“一人”呈现出“多/一”之间极端数差所特有的张力,突显出自己一人之缺席所造成的无法填补的空缺,然而其写法却丝毫不说兄弟如何期盼、如何落寞,只是进行一个客观事实的呈现,那“少一人”之词更是不带情绪的数学计算,乃是对前一句“知”字的补充与推衍。
显然,整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以“思亲”为主轴,而意脉贯连;但就内在思致的层次而言却可以断然二截,前半属于“任我则情”之“以我观物”,后半则转为“反观无我”之“以物观物”;前两句是以感性范畴的“情”为焦点,就“自我”这感受的抒情主体来落笔,至“倍思亲”而达到情思的最高临界点;后两句则是转而以理性范畴的“知”为基础,就远方之“他者”——情感客体来进行客观事实的呈现,笔尖袪除了情感的躁动灼热而带有理性的冷静与深沉。这种冷静与深沉的特质并不是来自对情感的逃避或拒绝,也不仅是出于对情感的控制与压抑;确切来说,所谓“静水流深”(stillwterrunsdeep)之原理乃庶几近之。意思是说,王维的情感不但是丰沛的,也是深刻的,“深刻”使得情感不会只是一味地任意向外抒发,而会翻转过来向内蓄积含敛,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便反而似乎带有平静的外观。这是因为情之“热”者,常常一往不顾地任情澎湃泛滥,求其俱焚共燃的白热与炽光;而情之“深”者,则往往欲说还休地含放于口内心中,默默挖掘更宽广的胸量以蓄纳更丰盈的情感。情之热者,形式上是向外喷薄,而情之深者,形式上却是向内含藏;向外喷薄者,人品往往率真任性,而向内含藏者,性格往往成熟深沉。此即是钟惺所谓:“情艳诗,到极深细、极委曲处,非幽静人原不能理会。此右丞所以妙于情诗也”以及“右丞禅寂人,往往妙于情语”真正意义之所在。
(本文摘自《唐诗的多维世界》,欧丽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定价:59.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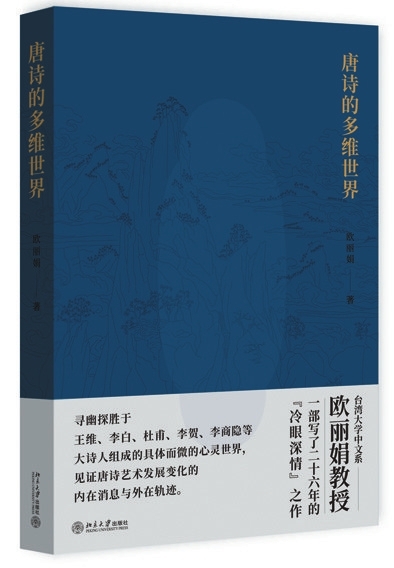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