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某次接受访谈时,记者问我:你的创作追求是什么?我说:无非有二:一是终生做大地道德的呈现者、阐释者,为乡土立传,为生民塑魂。近期的目标,是想进行向福克纳、诺里斯、怀特致敬的动作,立足京西之南——我的“约克纳帕塔法”,完成“京西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写作。目前已完成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脉》,正在写《京西逸民》,并以此为开端,持续架构我的“世系”,以达到让世界读懂了京西,就是读懂了乡土中国的书写意图。二是继续我的“西典新读”工程,写我的书话散文,并做到智性、感性和理性浑然交合,尺牍之间,有大气象,做大读者、大文章家。
这是一种写作规划,显得十分豪迈,类似野心。其实,豪迈也是一种自我施压,因为要兑现宣言,就得埋头苦干,是对轻逸生活的剥夺。《京西逸民》最初的几章顺手,但写着写着就迟滞了,因为长篇小说写作,是远遥的长途,爆发力是无用的,需要才力、体力和耐力的长久支撑。此时的我,有些“三力”不逮,强撑了几天之后,终于停了下来,无论如何不愿意继续写。
苦恼之下,我想到了果戈里。1848年1月10日,因《死魂灵》而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给友人瓦·安·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说:“对不起,亲爱的!每天我都准备写——但都被不可思议的不愿意写制止住了。”
记得当时读到的时候,我觉得颇不可思议,一个被视为文字天才的大作家,居然“不愿意写”!为此,我还在“不愿意”三个字上加了粗重的下划线,以此存疑。
好像是后来有一天,我遇到了止庵,我说:只要打开读书类的报刊,几乎准有你止庵先生的文章,你的创造力何等地强劲啊!
止庵摇摇头,面色阴郁地说:你这样说,我一点也不会得意,因为文章背后所经受的煎熬,时时让我想到放弃——跟你说实话,我居室里的床,离电脑仅有一米多的距离,但是,要想从床上爬起来坐到电脑跟前去,开始一天的写作,要跟自己的惰性较很长时间的劲儿——
今天我也遇到了此种困境,便不禁明白了,作家笔下的文字,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像泉水般喷涌,而是心血缓慢聚结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对灵感的耐心等待,对生活的痛苦思考,对思想的痛苦提炼,也包括对准确字词的艰难捕捉。写作者究竟不是机器,能够不停歇地连续运转,“京西三部曲”的雄心固然豪迈,但也不能不接受必然的“等待”。
但正在此时,就来了疫情。防疫隔离,就把人封闭在室内,而被迫的封闭是无奈、是无聊,是煎熬,度日如年。而写作者的底色,有自救功能,遂生一念:与其煎熬于大自然的瘟疫,不如受用于自主的精神苦役,那反而是悲壮的征程。便把未竟的文稿重新找出,决定在上次的断处,强迫自己续写。
奇怪地,一如冰冷的石头只要握进手掌,也会被慢慢地捂热,枯涩的笔触只要在纸上戳戳点点,文思也会慢慢地如约而至,竟渐渐地写下去了。写着写着,脑洞就开了,一如神助,疾行三月余,居然完满收官,成卷帙了。明末清初云南诗僧苍雪有云:人老笔椽下,云生砚瓦边。真是禅语如人语,只要固执地在“砚瓦”边坚守,终会有笔墨示人。
也真是有宿命的存在,我那部被王干先生戏称为“京西的包法利夫人”的长篇小说《玉碎》,成于2003年春夏之际,那时候正闹着“非典”。阅莎士比亚的传记,他的几个最激越的剧目,也都是在疫情中写,因为他经历了数次瘟疫,恐惧和惊慌几乎伴随了他一生,所以他有拂之不去的悲愤,就成就了他伟大的悲剧。
看来,“作家与疫”,颇可以写一部专门的文艺论,或许,困厄、困顿、困境对精神和灵魂的作用,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二
《京西逸民》是我的“京西三部曲”的第三部。基于对前两部创作得失的把握,便有清醒的借鉴,写起来特别精心,试图写得更独特、更准确,有超越的样貌。
小说以农村城市化建设为脉络,描绘了在土地腾退和拆迁过程中的矛盾纠葛、现实困境和最终破解。我在写作时,不回避矛盾,不虚饰亮色,而是正视问题,直面失误,做理性关照,以极大的善意告诉人们,城市与人是相互作用,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过程。我从这个意义上向城市的内部用力挖掘,试图把《京西逸民》写成一阕呈现“人与城”关系的现代寓言。
为了使小说感性丰沛,有动人质地,我特别注意对京西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对京西人物性格的深刻镂镌,试图让人们从中看到,这片土地乡风纯朴、人文深厚,土地上的人,具有自我审视、自我否定、自我矫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品格特征,是一块厚积薄发、充满希望的土地。
我还想要说的是,这部小说,在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上,我有深刻的用意。向罗曼·罗兰致敬,写出复调,有双重、甚至多重主题。农村城市化进城,必然是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作用的过程,人的生活方式和感情状态,便有自然而然的彼此交集和相互影响。这就让我眼前一亮,便把京西人的情爱作为案例,浓墨重彩地拿来描摹、剔滤。我欣喜地发现,乡村爱情(传统爱情)和都市爱情(现代爱情)之间,存在着一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说的“双重矫正”的关系——乡村爱情矫正着都市爱情的内容,都市爱情矫正着乡村爱情的形式——稳固、忠贞矫正着善变和背叛,优柔、平等矫正着粗糙和专断。这样的概括,或许有些不准确,但总的感觉是:两种情感样式的相互反拨、相互补充,让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新的城市样态下,有了内在的完善、内在的和谐。
于是,农村城市化是一种文明的进化,这里的人们,有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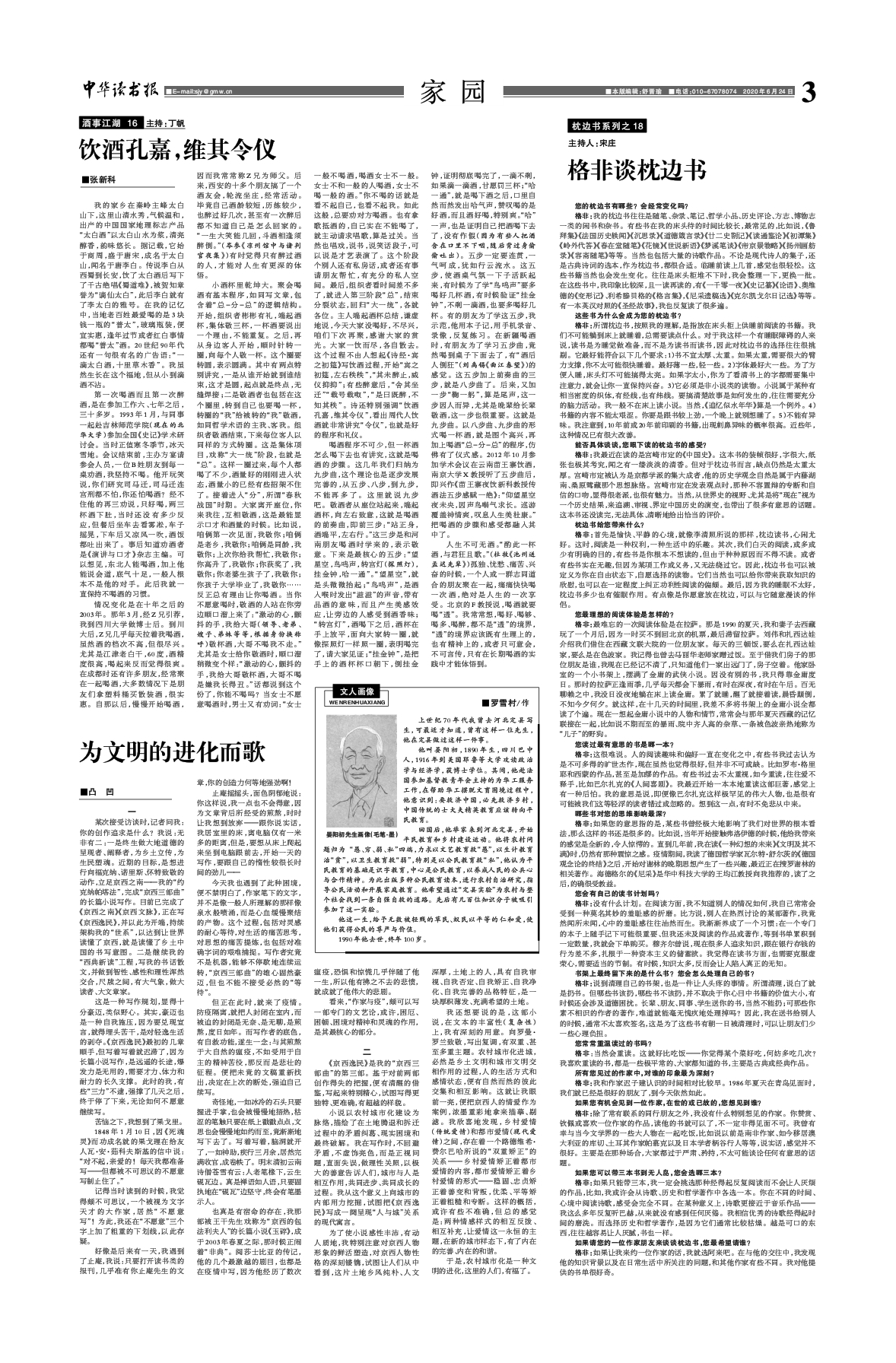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