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南昌大学刘经富教授惠赠了他刚出版的两种书籍:《陈宝箴诗文笺注·年谱简编》(商务印书馆)、《陈宝箴家族史料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令人欣喜异常。笔者闲暇仔细拜读,收获良多,对刘老师在义宁陈氏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更为钦服。这两部著作集其数十年沉浸之功,拓展和深化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必定成为后世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重要著作。
陈寅恪说过,东汉以后学术文化的重心不在政治中心首都,而是分散于名都大邑,地方大族盛门成为学术文化的寄托之地,“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钱穆亦云:“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此意尽人皆知。”从家族的视角介入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研究确实是有效的方法,笔者爬梳过义宁陈氏与湘乡曾国藩家族、善化瞿鸿禨家族、宁乡程千帆家族之间的联结,而借助刘著披露的材料和所作的笺注又能探究义宁陈氏与龙阳易家之间的关系。
陈宝箴与易佩绅、易顺鼎
陈宝箴与易佩绅初识于咸丰十年(1860),陈三立为其父撰写的行状有记“赴庚申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其巨人长德及四方隽异之士,而于易公佩绅、罗公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有三君子之目”。他们互相鼓舞、共同期许,如易氏曾言,“君年今三十,我长君五年。君多五年期,着鞭在我先。我悔半生误,回首多尤愆。眼看日月逝,迅如矢离弦。百岁能几时,忍为流俗牵。我心怵以忧,同志期共坚。勿立千仞高,一坠乃深渊。勿言平地卑,拾级登峰巅。君行我云从,负担无息肩”(易佩绅《正月十八寿陈右铭三十》)。他们在京时或与友朋会饮,勾连酬酢,或共商学问、直刺现实,结成知己,如他们讨论过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陈氏认为朱熹教人为学至精至详,并无支离之病,但宗朱学之人以攻击陆、王为事,矫枉过正,其末流之失即在支离;阳明学不以空寂为宗,但该派学者批判朱学末流过于偏重,未能深究本末,徒以附会宗旨为事,此为其缺陷。他指出躬行实践往往各有所得,如周敦颐主静,程颐主敬,仅在用功上微有不同而已,即便同为孔门弟子,子夏、曾子也是或笃信圣人或反求诸己,虽曰同堂而各有所成,故徒于朱、陆纷纷聚讼,非为学之正途。其实,朱熹的穷理,王阳明的致良知“皆为诚正修齐之实功”,辩者不能因噎废食,而学者因各有其主,各有偏重,于是自设藩篱以自卫,不免或支离或空寂。他主张不同的学习者应该依照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学说,“聪明才智之士,患不在不明,而患躐等蹈空,无积累之实,宜多读朱子书;沉潜刻苦之资。患不在不勤,而患支离束缚,无归宿之途,宜兼读阳明书。正取其相异而相成也”,而会通意识极其重要,“天下之理,一本万殊,不观其意,无以会其通。”讨论显示了陈氏对理学和心学葆有的融通观念。
是年九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陈宝箴在酒楼上遥见圆明园大火,“燕市痛哭,几不欲生”,乃“辍文学、讨时事”。时清军与太平军在南方各省激战犹酣,他们相约南还从戎,易氏先行,陈氏有歌行相送:“君不见山川变换风云改,朝为桑田暮沧海。又不见城郭繁华佳气多,昔日弦管今干戈。人生万事动如此,离合悲欢等闲耳。举酒且饮饮莫哀,慷慨高歌送吾子。吾子昔年来帝京,放歌燕赵千人惊。环墙拂尘走光怪,摶沙忽聚如平生。春秋风雨日相见,鼙鼓东南正酣战。多君壮气尚喧豗,驱叱鲸鲵走雷电。感时欲上万言书,长安市上提壶卢。阴山白草霜落枯,三冬闷拨寒炉灰。键户玩易换青鬓,疏狂痛诋高阳徒。吾谋不用事不已,一寸冬心寒未死。腰间錍箭簌簌响,吾子此行非无情。桓桓将军重揖客,跌荡军门森棨戟。赤手撑持半壁天,不惜千金招骏骨。嗟哉丈夫七尺躯,八荒六合为蓬庐。苍生未清贼未灭,安能郁郁偃息沉江湖。吾子行矣且勿悲,从来壮士轻别离、请为变徵歌,跌荡生奇姿,子从此别行勿迟。昨夜军书星火驰,男儿作健今其时。”(《易笏山出都将为从军之行作长歌以送之》)此诗堪称气机磅礴、豪迈无匹。易诗则记述了朋友间的投契与友谊,“天下知己有此哉,数字契合于尘埃。叔牙未识管子面,公然许为天下才。遂订金兰成莫逆,岂非神鬼为之媒。罗子俗恂恂,中有大略外不闻。陈子何飒爽,追风骏足脱羁鞅。京华一载余,观摩日无虚。看我奋臂为壮士,看我低头为腐儒。圣贤豪杰茫无着,两君助之情跃跃”。离别让人彷徨,“陈子犹能强作达,悲感每托为清狂。罗子悬恻最难遣,未免朝夕神暗伤。”虽然我辈聚散无常,“万里一堂相切磋,四海一室相包罗”(《西江两君留别罗惺四陈右铭》)。途中,易佩绅思念挚友,又有《道中寄怀陈右铭》。
该年冬,陈宝箴离京回乡省母,途中有致易佩绅函,首先评点了湘籍文士,认为陶澍启其端,陶文宗尚欧、曾,而其他以文学风流煽耀于潇湘、洞庭之际的不遇之士多学庄子,如王闿运得庄子的机锋以为文字语言,易佩绅窥庄子的宗趣以谈道学,某些人视王氏为狂士,易氏为愿人,在于不知其学之所出。他指出儒学虽经周敦颐、程颐、张载和朱熹推扬,但未能深探力索于六经之旨以求心得,自汉以来能够以颜回、曾子和孟子为宗,以通肸蚃于孔子的其实没有。从中见出陈氏为学注重回溯本原,取其本旨的认知。
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陈宝箴转抵湖南与易佩绅会合,易氏时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招募楚兵数千人,建立“果健营”,罗亨奎为副手,驻防在来凤、龙山一带,翼王石达开部正进攻此地。关于陈宝箴之所为,陈三立所撰行状有描述:“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府君间走澧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公修府故儒吏,延见府君风雪中,府君单絮衣,乃取狐裘复府君,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公为流涕,趣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府君持去,守益坚,寇不得逞,引去,于是果健营之名闻东南。”同时,陈宝箴开始展现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特长,易佩绅在招兵买马与所取财资的过程中与地方官员有了矛盾,陷入僵局,陈氏积极为其筹谋和调停,如他在致湖南布政使恽世临函中分析了当下形势,指出易氏领兵不过三营,战线又长,“株守一隅,则远者势难兼顾,星散置防,则所在皆形单薄”,一旦某关隘有失,其他关隘即形同虚设,而太平军屯集,以后劳力废财将要数倍于此,因此凭本军分布,渐次增募勇粮才是上策。易氏以往可能过于激切或意气用事,亦是出于为国为民的热忱,而非济私,他希望恽氏不计前嫌,念其苦衷,收回“碍难照给”的决定,予以支持,这在情、理、法上均无窒碍。我们知道,陈宝箴后来又调停过曾国藩、席宝田与沈葆桢间的争执和矛盾,均成功解决。石达开退出湘境后,易佩绅军奉调入陕,陈宝箴则辞而归省,后入席宝田军立下大功,为之后从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治七年至同治十三年,陈宝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久居长沙,差不多同期易佩绅或为官湖南或携家闲居长沙,他们来往尤多,《郭嵩焘日记》记录较详,如同治十年(1871)七月即有数次,“初一日己丑。朱香荪邀陪龙皡臣、易笏山、陈右铭、李作舟。”“十二日。便道一过易笏山、陈右铭、张东墅、彭海春。海春病甚笃,为之怃然。”“十八日。左景乔夫人六十寿辰,一往祝贺。便回拜各处,在陈幼铭、易笏山、龙皡臣、叶介堂处久谈。”同月,湘军中出了一件大事,统兵主管处理苗变的席宝田大病,令麾下各大将分统其军,导致援黔湘军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传言有人要取而代之。时易佩绅正在军中督办营务,掌管援黔湘军军需善后的陈宝箴立告易氏不可妄行更代。王文韶即派陈宝箴前往沅州,以视疾为名了解实情,陈氏留营旬月理清战状本末,有效地解决了难题。
光绪六年(1880)七月二十四日,陈宝箴过访郭嵩焘,忆及早年佐易佩绅幕事,“追述初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于时意气方盛。其言多可听者。”(《郭嵩焘日记》第四册)1892年易妻逝世,陈氏有挽联“始处贫贱而备尝忧患,终处富贵而未尝安乐,云何不益以寿;夫为大藩而赞之勇退,子为名士而教之义方,即此可知其贤能。”1898年,早已乞病归里的易佩绅卜居江西九江,而陈氏正主持湖南新政,经历着精彩、跌荡的晚年生涯。
易顺鼎自幼就熟识陈宝箴,他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由刑部郎中改捐试用道,分发河南,随后参与黄河治理,该年八月黄河郑州段决口,灾情严重,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调在粤随张之洞总理巡缉事务的陈宝箴协同办理河工,十二月末陈氏抵河南,为主持督修的礼部尚书李鸿藻筹谋治河方略。期间,易、陈有诗唱和。次年八月,治河失败,陈氏亦因目疾请假回籍调理,易氏有诗赠别。
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陈宝箴经王文韶力荐,补授湖北按察使,十二月初上任。次年二月,陈三立挈家至武昌侍父,他与易顺鼎、程颂万等时时宴集于湖北按察使衙署乃园,易氏有记,“陈右铭丈方任鄂臬,伯严随侍署中,樽酒不空,座客常满。臬署有乃园,余则寓居曾祠凌霄阁,皆有亭馆、花木。江山游览之盛,仿佛钱思公在洛阳日,永叔、圣俞、师鲁辈,时时载酒为龙门之游也。”光绪十八年(1892),易顺鼎迎母入庐山消夏,以庐山三峡泉水赠张之洞与陈宝箴,陈氏有诗:“廿年不践匡庐径,读画因君系梦思。饷我新泉分瀑布,淪将春茗助敲诗。清流合让支筇客,辟地须寻面壁师。安得草堂容设榻,一瓯谁足日高时。”(《谢易实甫赠庐山泉》)易顺鼎有和:“斟酌古今来活国,涪翁妙意可三思。浇将无咎过秦论,赚得东坡试院诗。块垒何多次山子,波澜莫二道林师。请公一口西江吸,同订僧床野饭时。”(《次韵陈按察丈谢赠庐山泉》)陈宝箴随后又赠诗二首,易顺鼎均有复诗,形成了一段迭相唱和的佳话,这些诗歌或表述对庐山山水的向往,或表达从俗事中抽离的愿望。他们还共同参与了一些文化事件,如黄庭坚《清隐院顺济龙王庙记》碑于康熙五十一年在老家修河出土后成了本地文人传诵不绝的盛事,后义宁州知州张鸣珂精拓了碑文,易顺鼎携至长沙呈陈宝箴鉴览,陈氏即去函嘱代拓二三十本见赠,于是张氏又监工拓了一次。作为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易顺鼎入幕张府后成了特受倚重的重要人物,陈宝箴不时通过他与张氏交流,有多通函电存留,陈氏亦重易氏之学识,相与讨论国政大事,如两人在甲午战争后论辩过中西商务发展上的问题。
陈三立、陈师曾与易顺鼎
陈三立与易顺鼎年少即相识,民国元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乃是陈氏六十寿诞,易氏赋诗贺寿,谈到“海内平生亲,陈兄我所独。君年二十时,我年十五六”。父辈同居长沙,又是道义之交,“两家居长沙,堂上称伯叔”“患难同九死,道义重骨肉”,二人一同长大,一同学习,“君家闲园中,不啻我书塾。稍稍爲诗歌,时时共灯独”(《壬子九月二十二日爲散原六十初度赋贺一首》)。因易佩绅长期为官贵州,易顺鼎常游走于黔湘两地,光绪元年(1875)二月他赴黔省父途中在武陵舟次巧遇前往长沙的陈三立,“推篷一握手,绿鬓喜如故。剪烛恣高谈,蛟龙亦惊寤。”有时易顺鼎也逗留长沙,与友人雅宴相与酌酒唱和,又或从外地寄诗以通声息。之后因其父调任山西、四川、江苏等地,易顺鼎本人也分发河南,与陈氏晤面减少,而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他入京参加会试,与陈三立、文廷式等常作诗钟之会,易氏有记,“丙戌会试入都,四方之士云集,如陈伯严、文芸阁、刘镐仲、杨叔乔、顾印伯、曾重伯、袁叔舆辈,友朋文酒,盛极一时。每于斜街花底,挑烛擘笺,以歌郎梅云辈爲上官昭仪,选定甲乙。……伯严是时,于此体尚不甚工,‘来本鹤膝’所作一联云:‘如我更多来日感,劝君莫作本朝文。’在伯严特游戏为之,以发同人之欢喊者,然至今日亦俨成诗谶矣。”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易顺鼎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前往武昌,同年二月陈三立已至,二人同任两湖书院分校。他们不时宴集于乃园,如程颂万有诗《湖北臬署乃园宴集赠陈主事三立,同座者范中林、易中实、黄修园》。当时,张之洞广招英才,一时名士云屯,据刘成禺言萃聚鄂中的贤士大夫分为几等:
南皮广延名流,礼遇有差,往来鄂渚不入幕者,当时目为第一名流,如王闿运、文廷式之属,经心、江汉山长谭献、张裕钊、吴兆泰之属,宴会首座,时谚呼为分缺先。幕府诸贤,如汪凤藻、王秉恩、钱恂、许珏、梁敦彦、郑孝胥、程颂万之属,两湖、经心监督分校,余肇康、姚晋圻、杨守敬、杨锐、屠寄、杨裕芬、邓绎、华蘅芳、纪钜维之属,宴会皆列三四座以下,当时皆目为第二名流,时谚呼为坐补实缺,总督僚属分司也。而梁鼎芬、蒯光典、陈三立、易顺鼎位在第一二名流之间,名曰宾僚,时谚呼为分缺间。他如陈庆年、陈衍、张世准之属,不过领官书局月费,时谚呼为未入流。京官如周树模、周锡恩之属,礼遇有加,时谚呼为京流子。此南皮在鄂人才之九品宗正也。至若王先谦断绝往来,孙诒让礼聘不答,时谚呼为上流人物。
在张之洞主持之下,他们常有活动,据易顺鼎记,“南皮师为海内龙门,怜才爱士,过于毕沅。幕府人才极盛,而四方人才辐辏。余与伯严追逐其间,文酒流连殆无虚日。其与诗钟之会者,幕府则杨叔乔、屠竟山、毕若溪、杨范甫、宋芸子、汪穰卿、范仲林、秋门兄弟辈。过客则文芸阁、曾仲伯、缪小山、王子裳诸君。而闽派如郑肖彭、沈爱苍亦同会集,洵一时之盛也。”
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陈三立、梁鼎芬应易顺鼎之邀共游庐山消暑,宿琴志楼,该楼位于三峡桥旁,乃1890年易氏请假回籍养亲时所建。现庐山开先寺旁石壁犹存石刻一条,录:“光绪十八年闰六月朔陈三立、易顺鼎、易顺豫、梁节庵同游。”有趣的是,他们一同聆听了西方传教士夫人弹琴,据易氏所记,“今年,陈君伯严闻之,欣然规往。余恃熟客,请为导师。至则青衣应门,仿佛识余。重闻弦声,不异昨日。与陈君流连感叹,不知哀乐之何从而生。”而陈师曾受易顺鼎嘱托绘制了《匡山草堂图》,陈三立有诗“聊倩儿曹提画笔”提及。
他们在武昌的宴集尤其频密,大集即有:同年九月初九日,众人同游公桑园,归饮按察使署;十二月六日,同至两湖书院看雪月,十二月二十日,同应张之洞之邀宴集于凌霄阁,次年三月初三,同修禊于武昌曾文正祠,作诗钟之会,张之洞遣人送酒食。同治十九年(1893)四月,陈三立偕易顺鼎、罗运崃等再游庐山,过东林寺、渊明故里,居琴志楼,尽二十日,各得诗数十篇,汇刊为一卷名《庐山诗录》。后来易顺鼎持此诗集到处征集题吟。同年七月,易母去世,陈三立有挽联,“从千人军万里道,偕麾节驰驱,半生巾帼奇踪,俊厨更了笞儿愿;记前朝松五爪樟,映板舆行处,他日匡庐重到,涧瀑长闻哭母声”。
甲午战争爆发,易顺鼎数次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言献策,力主抗战,闻和议已成,又单身赴京游说力阻,并斥责李鸿章、吴大澂误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他从厦门入台,与刘永福夜晤,倾心相谈,论及国事和唐景崧不免痛哭流涕,之后以二人为首共同起誓抗日。易氏随后回渡求援,张之洞等大员不愿承担破坏和议的罪名,不说同意或不同意,不说接济或不接济。同时期,陈宝箴从保定去电劝其返湘,免生枝节,陈三立亦担忧挚友安全,六月六日电函劝其返鄂商议行止,几日后又电有要事相商,望迅即至鄂。七月,易顺鼎筹得义款万余两,再至台南,但事已不可挽回,八月,陈三立有电“已有密旨令南洋接济”,三日后又电提及可筹得饷银五万,令易氏大喜。但很快,他收到陈氏多封电报,或谈及易佩绅担心儿子安危已至武昌,劝其速归,或谈及此前所言接济之事乃是京城误传。九月,全台尽失,易顺鼎起程赴沪,路上与陈三立不断互通信息。查阅《散原精舍诗文集》,从六月初六至九月初七,陈三立有致易顺鼎电稿十二则。
陈三立回湘辅佐其父主持新政时,易顺鼎常至长沙,如据皮名振《皮鹿门年谱》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易佩绅、易顺鼎父子“为诗坛之集”,与会者有八指头陀、蔡乃煌、李秀峰、陈三立、陈师曾等。维新失败后,陈宝箴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陈宝箴去世,陈三立心灰意冷,转居南京,而易顺鼎得授广西右江道等职,后再入张之洞幕随侍武昌或京城,仅在数次路经南京或陈氏至武昌筹划铁路事时才得相见,彼此赠诗却未停止,易氏还因境况颇窘函请陈氏资助。清廷覆亡后,易顺鼎和陈三立避居上海,来往频繁,他们或一同列席某人招饮,或同与传统节日之会,或彼此互访,唱和亦多,如《王闿运日记》记民国元年农历十二月与陈三立、易顺鼎、樊增祥在沪宴集的情形,“十八日与樊、易、陈同登岸,访亨社,裴回往来,行数里未得,后乃得之。小食粥酪,同至酌雅楼,请子玖、子培、子修、小石,小石不至,便约重伯、李梅痴九人同集。皆言宜留此度岁,遂定起行李。硕甫往来奔驰,竟未遑食。”“十九日 寿苏、子培来,同丞相车至静安寺,子修、易、陈、李、樊同集。仙童急欲联句,竟无人附和。”次年,易顺鼎剪发入京,因经济压力而入职民国政府,又常出入于戏楼舞台,而陈三立隐居沪上以遗老自立,洁身自好。当时评剧捧角之风盛行,易氏尝作《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称赞名角小翠喜、小香水、金玉兰等,樊增祥、陈三立等责其“凌乱放恣”“拉杂鄙俚”,因距离和观念差异,陈、易交往益稀,但据《缪荃孙日记》,易顺鼎但凡回沪,多与陈三立、沈曾植、瞿鸿禨等雅集。1920年,易顺鼎逝世,陈三立撰有《祭易实甫文》,忆及始于总角之年的情谊,易氏波澜起伏的生涯和不太得志的缺憾人生,婉曲深挚。
陈三立、易顺鼎交称莫逆,诗歌风格却大相径庭,如汪辟疆所言易氏“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至以诗为戏,要不肯为宋体”,他早年学六朝,与王闿运近似,后改宗中晚唐,清峻可喜、深秀精妙,却因贪多而缺乏裁剪;陈氏前期诗清新隽雅,中期风格为之一变,论诗恶俗恶熟,以江西诗派为宗,“兼有杜陵、宛陵、坡、谷之长,闵乱之怀,写以深语,情景理致,同冶一炉,生新奥折,归诸稳顺,初读但惊奥涩,细味乃觉深醇。”
总之,梳理义宁陈氏与龙阳易家代表人物的往还交接让我们了解了两个家族间的情谊,更重要的是从中映照出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脉络,以及个体在历史大潮中的人生选择、命运沉浮和心灵坚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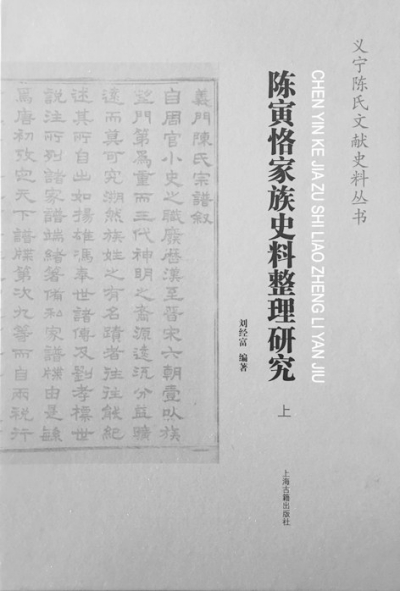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