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台湾蒋勋先生,内地人除了知道他是“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祖籍福建福州,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之外,还知道他“母亲是满族正白旗人,外曾祖父是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辛亥革命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被抢空了的家宅依然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都够一百多户人家居住”。1988年他回到一岁时离开的西安,“知府衙门早已不知去向”,“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他说“不用了。何必要把现在住着100多户人家赶出去呢?”而这据说也是他自认为曾经不愿让他们兄弟姐妹“知道自己是满清后裔,是被革命的对象”的、他所见过的人中“比别人更会讲故事”的母亲,在他五六岁时讲给他,他又通过《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等》大陆媒体,讲给国内的读者的。这些“凄美”而极富沧桑感的故事,乍听(看)起来确是十分动人的,保不住有的人信以为真的同时还会生发出许多的感慨,然而当其一旦面对史实检验的时候,却令人遗憾地暴露出不少的破绽。
先说西安府的最后一任知府。其外曾祖父,不知是母亲没给他说,还是母亲说了他没记住,蒋勋先生似乎从来没对人明确地讲过,而有清一代西安府的知府,共有崔允升、白龙升、王希顺、孟继昌、陈维新、王汝楫、祁彦、胡朝宾、杨国正、张绍龄、叶承祧、刘芳标、邵嘉引、阿尔亲、董绍孔、彭腾翓、卞永宁、李杰、祖业宏、萧士蕃、江濯、庄祖贻、韩奕、高珙、徐容、桑成鼎、金启勋、赵世朗、潘柬鼎、蔡琏、王绍文、乌灵阿、朱闲圣、白嵘、蓝钦奎、张奎祥、成德、王嘉会、富躬、国栋、克尔图、王兴尧、王时薰、林文德、翁熠、周廷俊、田锡莘、舒其绅、武若愚、吴沂、吴学濂、朱勋、陈文骏、盛惇崇、樊士锋、方载豫、邓廷桢、鄂山、沈相彬、韦德成、云麟、李希曾、郭维暹、贵麟、白维清、徐栋、濮城、成瑞、段大章、蒋琦淳、何炳勋、沈寿嵩、吕傍孙、龚衡龄、杨光澍、李慎、宫尔铎、林士班、郑子兆、李楹、李希哲、文启、童兆蓉、周铭旗、胡湘林、胡延、傅世炜、张筠、光昭、尹昌龄、瑞清、胡薇元等92位,其最后一位胡薇元,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三《职官四·西安知府》记载:“顺天府大兴县人,原籍浙江山阴。宣统三年七月由陕西兴安府知府调任,是年九月一日因政变解任”;由满人出任知府的,计有胡朝宾、刘芳标、阿尔亲、乌灵阿、富躬、克尔图、鄂山、云麟、贵麟、成瑞、文启、光照、瑞清13位,而最后一位瑞清,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三《职官四·西安知府》记载:“满洲正黄旗人。荫生。宣统二年八月由陕西同州府知府调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升延榆绥道去任。”蒋先生外曾祖设若如其本人或其母所说,是“满族正白旗人”,则确定没有做过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设若如其本人或其母所说,是西安府最后一任知府,则其必是汉人而不是满人,或者是“满洲正黄旗人”而不是“满族正白旗人”。所谓既是“满族正白旗人”,又是“西安府最后一任知府”,缺乏必要的史实支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客观地讲,辛亥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之初,的确发生过不少趁火打劫的案件,但是数日之后,具体说,即10月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之后,这种情况即基本得到控制。其具体起义领导人,亦即曾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和陕西首任督都的张凤翙(翔初)先生1944年(辛亥33年)纪念之际曾回忆:“初一日那天,相当混乱,有些趁火打劫的宵小抢劫银号情事,旋被完全镇压。”《陕西通史》民国卷也写到:“西安起义的第二天,张凤翙就发布《安民布告》,宣布起义军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接着,又颁布了《劝商户照常营业布告《求贤定乱安民告示》,严禁抢劫奸淫,并派出由起义军官兵组成的稽查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查,对一些趁火打劫的不法之徒严行镇压。为保证各商号照常营业,由郭希仁负责赶制“保护旗”1000面,遍插各商号门首,以示安全。同时限令各初等、高等小学一律在5日内开学,这就使西安起义后一度混乱的社会秩序较快地得到扭转。军政府正式成立后,继续发布了一系列整顿社会秩序、严肃军纪、安定人心、保护商业和进行有关社会改革的政策法令,如《通饬剪发告示》《劝谕清军官兵向义归心告示》《严禁抢掠告示》《劝谕各码头兄弟勠力同心光复各属州县告示》《严禁假冒催粮官弁告示》《谕民踊跃缴纳粮草白话告示》《勿轻信谣言妄语告示》《切实保护过往商贩文》《严禁士兵非法持票换钱文》《保护商业告示》《严禁挑拨回汉关系告示》《劝民捐助粮饷公告》《通告旗人各谋生计告示》《劝谕农工商各安其业告示》《严禁军人虐商布告》等,此外,张凤翙还核定了秦陇复汉军《军律八条》,出示晓谕军民一体遵照,《军律》规定,私行招兵者斩;兵不归营在外招摇者斩;冒穿军衣假充兵丁招摇撞骗者斩;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者斩,兵丁擅入人家扰害居民者斩;私藏军火者监禁,步兵骑马者拿究;深夜游行街道嘈杂喧哗者拿究。故如此背景之下,像蒋勋本人或他母亲所说的其外曾祖“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的恐怖情景,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明显似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在焉。
第三,关于其曾外祖“家宅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都够一百多户人家居住”的说法,也让人倍觉荒唐。如此多的家宅的置办,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办到的。语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要说其外曾祖极有可能就没当过西安知府,就是他真的当过西安知府,依前举《续修陕西通志稿》所载胡薇元和瑞清两位知府任职的时间迁任频率,他的知府任期自亦不可能太久,怎么可能置下如此巨大的家业?又何况更关键的,二府街就是一条长约380米的短仄街巷,清末这段,根据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中浣舆图馆测绘图改绘的《清西安府图》显示,此街南面虽无明显的公共建筑而似悉为民居,北面则东、西两头的二元坑(光绪十九年《陕西省城图》称“二府坑”)和二府园之间,已为协标教场和协标都司署所占据,而经侯欣一《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考证,到宣统二年(1910),其中段又成了西安地方审判厅的驻址。民国期间,1932年5月西安市政工程处绘制之《西安市区域全图》显示,其街南仍没什么变化,其北面东头的二元坑已为中山中学所占据,二府园依然存在(只是未标),中段则是长安地方法院和与之毗邻的公安四分局的所在;据1939年5月西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绘制的《西京城关平面图》显示,其北面较《西安市区域全图》没什么变化,只是中山中学已改名第二中学,而南面的东头则出现了一个□□(因图中文字看不清,只好以□□代之。作者注)会馆。此外据朱文杰先生《记忆老西安》的勾沉,民国年间这条街上还有一座供奉理发行业祖师罗真的罗真庙,1914年由西安地方检察厅改组的长安地方检察厅、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下的空军第三路司令部、1942年成立的西安海关、1943年在郿县开采铅矿眉山公司的驻地和胡宗南系统的《自由晚报》的社址,也都在这条街上。因而不管是清末还是民国,蒋先生外曾祖即使真的在这里住过,并且确实家业较大,恐也占半条街不到,绝不可能雄踞“二府街的整条街道”。而解放之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不仅街的北面驻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西安市政府财贸院等大的单位,南面也还有市级机关房管局、莲湖区二府街小学和西安市剧装厂等若干单位,早年的各种建筑应已不复旧观,蒋先生外曾祖家宅纵然尚有遗存,到1988年他重游悬弧之地的时候,又如何仍能居住多至一百多户呢?“二府街的整条街道”是个什么概念?“能住一百多户”又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彼时真的“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蒋先生果然能有诗圣杜甫之高尚情怀,潇洒到对此无动于衷,竟至连一丝收回若干作为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吗?故事真是太美了,美得竟让人油然而想起“杜撰”二字。
不是吗?这位蒋先生的整个家世故事之中,除了西安的二府街是真实存在的外,其外曾祖“满族正白旗”的出身疑似杜撰,其外曾祖“西安最后一位知府”的身份疑似杜撰,其外曾祖拥有二府街“整条街”的家宅和他面对只要申请就可以发还的巨量房产了不动心的故事皆疑似杜撰。事情的起根发苗,端在其外曾祖的民族与身份,但是其外曾祖的真实名号与行状,他却闪烁其词,连一点确切的信息也提供不了,这一切难道都不值得怀疑么?之前帮看文杰先生写二府街的稿子的时候,我曾经就有关的内容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近日又见雷凡乡友微信中对这位蒋先生夸说自己身世的文章疑窦迭生,遂心动手痒,援笔匆匆写出如上这些话,愿意了解事情真相的朋友,想必宜乎能够给出自己的判断,而不会以我的闲情别寄,责怪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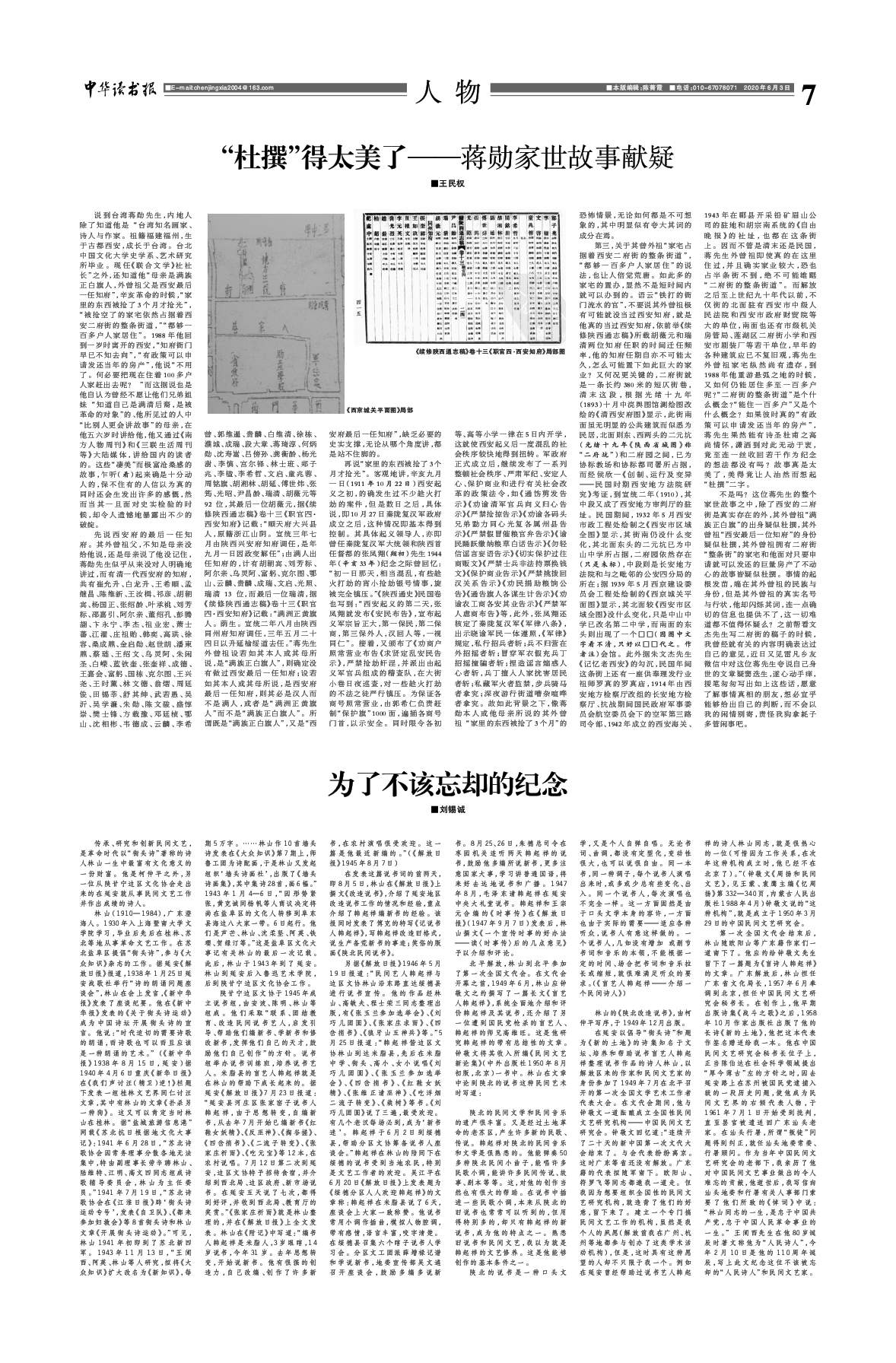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