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世纪,鼠疫(黑死病)不断侵袭英国。据说1348—1349年的鼠疫造成1/3到1/4人口死亡。1666年之后,鼠疫基本在英国绝迹。之后,英国又接连遭受天花、流感、霍乱的打击,每次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引发恐慌,这促使英国政府在19世纪开始着手进行公共卫生建设。温斯洛(C.E.A.Winslow)教授认为,公共卫生是“阻止疾病、延长生命、促进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一门科学与艺术。这需要利用有组织的社区资源维护环境卫生、控制社区传染、教育公民讲究个人卫生、组织医学和护理服务进行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并动员社会力量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达到保证健康的生活标准”。乔治·罗森(GeorgeRosen)教授在其名著《公共卫生史》中写道:“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护、促进其公民的健康和福祉。”英国最早建成世界上最健全的公共卫生系统,但国家权力介入公共卫生,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抗议,这种局面持续至今。
一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初期,人口激增以及城市化发展,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这是因为,在城市兴建的新的定居点狭小、原始,没有合格的卫生条件,因此疾病蔓延,人均死亡率惊人地上升。大量证据证明,英国的城镇由于缺少干净的饮用水,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正在成为“死亡的陷阱”。霍乱在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4年和1861年在英国的连续爆发,促使一些有识之士自发调查过度拥挤的城市如何成为传染病的温床。
詹姆士·凯-沙特尔沃思(JamesKay-Shuttleworth,1804—1877)医生是先行者,1832年他发表了经典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in Manchester)报告。他的报告使人们了解到公共卫生不需要神秘的艺术,相反,其关键在于确保城镇街道干净、饮用水清洁以及排水系统完善,确保废水被排出城市。在两年后的1834年,英国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由律师出身的艾德温·查德威克(EdwinChadwick,1800—1890)领导。“济贫法委员会”认为,“采取和维持必要的预防疾病的措施所需支出将低于现在不断产生的治疗疾病的费用”,并促动议会在1834年通过新的《济贫法》(PoorLaw,这部《济贫法》通过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通过的旧《济贫法》被替代)。新《济贫法》不仅规定济贫院(workhouse,又称“贫民习艺所”)为收容英国日益增加的穷人的法定机构,而且建立了《济贫法》规定的“医务室”。因为以查德威克为首的社会改革者认为,贫穷导致穷人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会生病,因此这是“贫穷的疾病”,这种“疾病”越来越威胁着整个国家的福祉。在新的《济贫法》的规定下,医疗服务体系很快建立,以满足越来越紧迫的需求。例如,在济贫院里建立了专治发烧和一系列传染病的隔离医务室。“事实上,这是在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向全社会推广之前的贫民的NHS”。但根据新《济贫法》建立的医务室,条件苛刻,提供的治疗条件有限,人们对其唯恐避之不及,就如同对济贫院的态度一样。
查德威克在“济贫委员会”的任职使其意识到,英国民众面临的卫生问题比当时人们意识到的问题更严重——特别是在伦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查。1837年和1838年,他在数名医生的协助下,对伦敦环境展开调查。查德威克是边沁的忠实信徒,他认为对于民众健康来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如果人们生活在肮脏的环境里,预防很难取得效果。查德威克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环境和社会因素上,而不是疾病本身上。他认为贫困是由于人们生病后无法工作造成的,因此国家有职责维持健康的生活环境。查德威克集中力量调查污水、粪坑、排水池以及过度拥挤的住房对健康的危害。其调查结果《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Reporton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于1842年完成。在报告里,查德威克强调以伦敦为代表的城市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认为肮脏的环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他在报告中提出的解决办法包括,政府应负责供应清洁的饮用水、处理污水以及消除污染源。
查德威克的报告以及1848年霍乱的流行促使议会进行关于公共卫生立法的辩论,1848年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ThePub-licHealthAct)。根据这个法案,英国设立了“卫生总署”(GeneralBoardofHealth)和“地方卫生局”(LocalBoardofHealth)。法案规定,饮用水的供应和污水的排放都由卫生总署统一管理——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由不同机构负责,从而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稠密的城镇的卫生条件。虽然这部法案发挥的作用不大,但对英国公共卫生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特别是据此设立了存在至今的“卫生医官”(MedicalOffi⁃cersofHealth)职位(根据1846年的《公害去除法》[NuisanceRemovalActs],利物浦是第一个任命“卫生医官”的地方)。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通过后,约翰·西蒙(John Simon,1816—1904)被任命为伦敦的第一位“卫生医官”。到19世纪70年代,“卫生医官”成为常设的职位,即每个地区必须有一名“卫生医官”。“卫生医官”有权力调查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的事务,如垃圾箱的标识、食物造假、屠宰场卫生、有毒气体的排放等等。并且,“卫生医官”的权力不断增加,既包括调查权也包括执行权。
1854年的霍乱流行带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另一个突破。公共卫生的主要倡导者、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在1832年和1848年曾经历过霍乱爆发,并确信这是一种水传播的疾病。这一次,他通过调查伦敦市中心的病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找出了一口受污染的井。井的手柄被移除后不久,霍乱消退。斯诺还分析了由不同自来水公司提供饮用水的地区的霍乱发病率,证明购买从泰晤士河下游取水的自来水公司地区的发病率,比购买从泰晤士河上游取水的自来水公司地区的发病率高14倍。继这项研究之后,他建议人们饮用开水。这时已经取代查德威克成为卫生总署首席医疗官的约翰·西蒙将这项工作付诸实践。他成功地将公共资金转用于传染病的调查——包括白喉、伤寒和天花。在西蒙的推动下,1872、1875年,议会再次通过《公共卫生法案》,法案得以进一步完善。特别是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全面涵盖了关于住房、饮用水、污水和传染病防治的规定。在查德威克以及西蒙的推动下,英国发展出一套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体系。
英国公共卫生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到维多利亚中期,伦敦建设了完善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其他城市紧跟伦敦的步伐,英国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1868年,约翰·西蒙爵士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作用的扩大:“(国家)介入父母与孩子之间,不仅限制工厂雇用儿童,而且要求孩子接受免疫;(国家)介入雇主与雇员之间,坚持为了后者的利益,所有工厂都必须满足一定的卫生条件;(国家)介入卖者和买者之间,限制有毒物质的售卖,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不合格水的供应、禁售假药、掺假的食品和饮料、不适宜的肉;这些行为都是对公众的侵犯。地方当局被授予权力介入清洁水的供应、住房状况的规范以及建立隔离医院。国家负责对疾病的治疗,不仅无条件地免费治疗贫困导致的疾病,而且国家在紧急时刻会为感染传染疾之人提供有组织的医学帮助,不仅为穷人,并是免费为每个公民接种。”
二
随着公共卫生的发展,国家日益涉足人民的健康,传统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放任的观点均受到挑战。19世纪40年代,议会通过一系列立法,授权卫生总署对水污染等问题采取措施,这就挑战了私营自来水公司的权力,遭到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人的抵抗。无独有偶,1853年议会通过的《免疫法》(The VaccinationAct)规定天花免疫是义务性的,一些人认为这侵犯个人自由,侵犯了家庭的庇护权。这些人或基于经验的、宗教的或自由的原因强烈反对强制接种,他们把矛头对准查德威克,1854年查德威克在卫生总署5年任期结束后,只能退休。之后,1867年的《传染病法》(The Contagious DiseasesAct)继续了同样的故事。根据《传染病法》,议会赋予重要城镇和港口的高级官员可以扣留任何被怀疑是妓女的妇女并强迫她们接受医学检查,如果发现染病,强迫她们进行必要的治疗。这个法案被认为严重威胁了个人自由,特别涉及对女性的侵犯,引起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女性主义者共同的抗议。
从19世纪至一战之前,中央政府干预的增长与英国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解决。自由主义和地方民主主义者强烈抨击政府的家长制和集权主义倾向,这种反对的声浪放慢了公共卫生发展的速度,并把查德威克踢出卫生总署——查德威克曾被约翰·罗素称为英国的普鲁士部长。在强制性天花疫苗接种等问题上,这种健康的强制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表现得相当突出。如19世纪后半叶英国出现的“反疫苗联盟”(Anti-vaccinationLeague)和“废除传染病法案全国性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RepealoftheContagiousDiseasesActs),就是对抗政府强制接种和对被怀疑是妓女之人进行检查的产物。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政府不得不废除婴儿接种和妓女检查的强制性法律。
一方面,有学者支持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扩大权力,如18世纪的德国医生约翰·彼得·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1745—1821)就用“医疗警察”这个概念解释国家角色的日益扩充,用公共卫生和以医疗管控为重点的措施对健康进行干预。弗兰克的“医疗警察”概念混合了家长制国家观念与重商主义的原则,认为健康的人口是国力的来源,而国家的有效管理是保证人口健康的关键。他列举出政府管理致病行为的办法,并提出改善环境卫生的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国家的管理。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批评国家权力伴随着公共卫生的发展不断扩大,侵犯了公民自由,这些举措后来被福柯表述为“医学专制”。
福柯在分析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特点时定义了一种新的威权形式——“凝视”。福柯认为从启蒙时代起,科学知识开始统治西方文化,但这种社会的“理性”是通过建构“规训的”知识和语言达到的。西方的文化权力通过一种新的“监视机制”进行广泛的行为约束,把个人及其主观经验转变成服从的躯体,如医学、心理学、犯罪学及当代在压抑对话中对性的讨论。福柯认为科学医学的兴起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医学化——把疾病变成一种“异常”,把医学的职业权力扩大到监管健康及疾病。因此“躯体”成为大范围的控制和规训的焦点,在这过程中医学起了关键作用。诊所的诞生、教学医院的诞生,使得医学“凝视”制度化。这又扩张到人口的生物政治领域,便利了国家对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的调节。
笔者认为,公共卫生需要以国家之力推广,大而言之,公共卫生需要全球合作。以英国为例,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健康问题不能只靠地方力量解决,这促使中央政府做出回应。公共卫生的发展的确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但工业化并不是国家对人口健康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在工业化之前,欧洲各国已经对人口健康采取行动,如建立检疫、隔离制度。因此,福柯定义的医学“凝视”只是一家之言。公共卫生发展的确需要“大政府”,因为公共卫生一方面需要利用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理解疾病的本质和原因,并为预防和控制疾病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公共卫生也需要运用国家权力,依赖于各种非科学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卫生具有政治的维度。公共卫生改革与“大政府”的理念同步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但并不一定带来“医学专制”。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软弱无能的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他还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的部分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这在许多国家埋下祸根,如导致艾滋病在全球泛滥。
三
今天,人们把对健康的追求等同于对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追求。新型冠状病毒等传染性疫病不是对某个国家人们的生命造成威胁,而是对全球所有人的生命造成威胁。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举措各具特色。2020年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爵士(SirPatrickVallance)在与首相一起面对媒体发布政府简报时,提出“群体免疫”(HerdImmunity)计划,此举引发全球舆论哗然。其后不久,英国政府在确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的压力下出台了史无前例的举措。2020年3月19日,英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新冠状疫法案》(Coronavi⁃rusBill),政府认为这个法案对此次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至关重要。正如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MattHancock)所说:“赋予政府需要的权力保护人民的生命非常重要”。3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关闭咖啡馆、酒吧、餐馆(可以外卖)、健身馆、学校(学校仅对父母是医护人员、警察等重要工作岗位的子女开放)以及40个地铁站。政府宣布:警察有权力禁止任何类型的聚会;警察或公共卫生官员或移民局官员有权拘留被怀疑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并将其隔离(历史惊人地相似!),如果被怀疑者拒绝监测,将被处以1000英镑的罚款;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边境的安全,可以动用边防部队;法庭听证会可以通过电话或视频远程进行;保护租户们不被房东驱逐。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议会要求这些举措每六个月评估一次。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Sunak)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工作保留计划》(New 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Scheme),企业不分大小,包括慈善性质的和非盈利性质的企业,都适用此计划。政府要求企业在疫情期间不解雇员工,对于无法工作或暂时没有工作可做的员工,政府将支付其80%的工资,每月最高2500英镑,这稍高于目前英国的中等收入水平。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介入并支付雇工工资”。
笔者认为,这次疫情是二战之后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它也必将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影响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在经济领域反对“大政府”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政府”。并且,各国政府在此次大疫之后定会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建设或改革,国际合作也必将进一步加强,因为公共卫生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既考验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也会加强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如果说此次疫情留给我们任何教训的话,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很快会传遍全球,在面对全球疫情之时,各国需要一致、快速行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扫门前雪。疫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只有全球合作,如信息共享、医疗资源(包括医生)相互支援,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各国政要不仅应该关心本国疫情,更应该关心整个人类的未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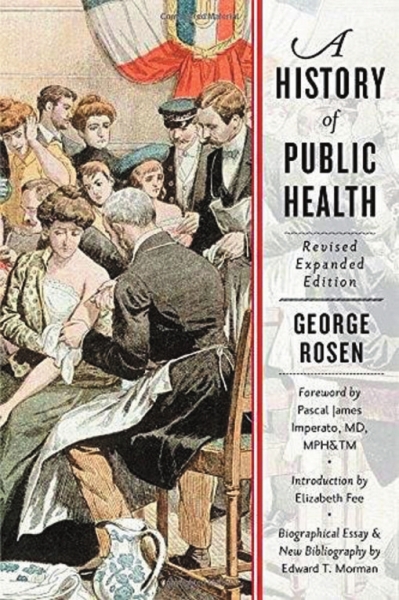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