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郊区墓园的黑白照片,接着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是塞巴尔德的小说《移民》开头。从第一句话开始,小说的叙述声音就被赋予了新闻报道般的庄重感。人只要生活在时间里,就必然熟悉这种声音:客体的曾经在场,主体的脆弱记忆,以及当它们一起消逝后,两者因彼此混淆而给人以连根拔起般的迷失感……
塞巴尔德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1944-2001),生活地域则辗转于瑞士、英国、德国之间,某种程度上讲,属于二战幸存者的后代,他笔下的故事大多也聚焦于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在历史的阴影中,人如何持续受到伤害,并且走向死亡的?
塞巴尔德将他的作品定义为“纪实小说”,并且将黑白照片引入小说,作为对文字的补充。其成名作《移民》提供了这一写作的典型范例。与其说是四篇短篇小说,不如说是塞巴尔德针对“移民”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四段追寻之旅。小说中,塞巴尔德选取了四位移民者作为“我”的追寻对象:“我”过去的邻居、“我”曾经的小学老师、只有一面之缘的“我”舅公、“我”认识的一位画家——“我”与这些他者只有过去的一点微弱联系,并非出于私人的情感动机,“我”才去探访这些他者的人生经历。而且在“我”探访过去的时候,这些人已成为死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与他者之间的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十分遥远。
因此,要如何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断,唤醒这些“死者”的记忆与感受,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迟到的联系?这位追寻者为我们做出了示范,我们看见,他怀着惊人的耐心和洞察力,记录着客观事物中纠缠蔓生的大量细节、幸存者的转述、甚至回到死者“曾在”的现场,并且凭借以想象去建构——让他者的生涯成为我自己回忆。
在这个过程中,“照片”承担了重要的纪实功能,在语言虚构的世界之外,形成了真实世界的参照。塞巴尔德看到了照片在记录历史时所具备的明显优势,然而,在照片选择上,塞巴尔德和新闻摄影的选择(“决定性瞬间”:自身具备强大的戏剧性张力)却迥然不同:班级集体照,家庭合影,私人肖像照,以及风景明信片,报纸的照片……这些寻常的照片,无声地记录着一部私人的心灵史。可以想象,随着个人的死亡,这些记忆也会被销毁,被遗忘。塞巴尔德让这些被遗忘的照片跳出尘封的死亡档案馆,被置于文学的放大镜下,被重新解读和审视。在《保罗·贝雷耶特》中,作者描述了当“我”看到已经死去的小学老师的照片的感受:
……在观看其中那些相片时,我确实觉得,现在也仍然觉得,好像这些死者又回来了,或者说好像我们正准备向她们走去。
另一处,“我”的小学老师保罗在照片背面写道:
人总是在直线距离大约两千公里外——可是从何处算起?——而且随着每次脉搏跳动,一天天地、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变得更不可理解、更没有个性、更抽象。
这话必须作为证言,附着在一张死者的照片上,通过死者之口——而不是通过小说家的虚构——对人们说出。作为“死亡”载体的照片赋予了小说一种罕见的情感强度,我们得以在这种媒介中看到了死者的归来:他的形象、声音以及声音中记录的精神痛苦,同时抵达了叙述者和读者所在的时空。
通过照片,塞巴尔德唤醒了我们对于过去某个瞬间的临在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然而,不同于“非虚构新闻写作”的是,从整体考量,这些作品在“真实-虚构”天平上依然明确地向虚构一方倾斜,也就是说,“真实”并不是这些纪实小说的唯一标准,它们只是提供了材料和证据。通过“纪实小说”,塞巴尔德重新演绎了真实,也重新发明了虚构,并实现了虚构对现实的明确指认,将这些迷雾般混沌难言的个体生命经验上升至时空哲学和历史反思。
这一写作观念无疑具有深刻的原创性,但也体现出二十世纪文学遭遇的普遍的现代危机:在我们目力可见的时间中,在延续至今的空间中,发生过(也还在持续发生着)大量的历史罪行,面对这些过量的灾难,文学审美失去了道德立场,文学的力量则面临着失效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的句子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如果说任何一种虚构都是轻慢的,那么,就必须引入“纪实”的严肃感,来与这份过于沉重的历史遗产相对称。现代的小说,不仅是“说什么”的艺术,更是“怎样说”的艺术。所谓“移民”不只是在空间的意义上被驱逐出故乡,也是被驱逐出人们此前信任的一整套生存经验:家庭、关系、教育、习惯、甚至语言——即使这些人从历史的暴力事件中幸存,它们依旧全面地被剥夺、被伤害——这渐渐地导致了人的精神疾病及异化,并最终走向自我放弃与自我戕害。这隐藏的伤害难以识别,更难以表达。因此,《移民》中的几位被探寻者不约而同的对于过往采取了沉默的策略,却因对于往事的压抑而再次受到伤害。邻居塞尔温大夫提起了“乡愁”以及生活被错置几十年后的荒凉处境,不久后便举枪自尽。舅公安布罗斯虽然在他的一生之中,学会了几种不同语言,作为尽职尽责的管家,奔波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点。最终仍旧为记忆所累,自我放弃式地选择了电击疗法,渐渐黯淡、萎缩,最终死去。马克思·费尔贝尔的画家母亲留下的日记,女性的声音间接出场,留下了生命崩毁的线索。
塞巴尔德借助他者的转述,照片,日记,景观——所有生命经验的碎片共同拼接成一份关于“移民”生活真相的历史证据。人类的所有幸存者(以及幸存者的后代)必将携带着这一疑问在失衡的噩梦中前行:一方面是历史之重,一方面是(必将随时间消失的)记忆之轻。在塞巴尔德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奥斯特利茨》中,主人公奥斯特利茨便持续地面对着时与空的双重失衡困境:
我想到,我们能够保存于记忆中的事是多么微乎其微,有多少东西随时都会与每个被戕害的生命一道渐被忘却;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在自行排泄罢了,那些黏附在无数地点和对象上的往事,那些本身没有能力引起人们回忆的往事,从来未曾被人听说、记下或者传给后世。历史,比如说吧,就像影子般叠放在木板床上的那些草褥,因为里面的谷壳经过多年,已经脱落,这些草褥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短,又皱又小,仿佛这就是那些人——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想着——那些在黑暗中曾经在这里躺过的人的遗体。
至于奥斯特利茨,他又是如何诉说的?
“我看见……;我梦见……;我感觉……;我记得……”奥斯特利茨穿行于时间迷雾中,在虚无的精神旅途中发现的一点蛛丝马迹,并在庞大的历史废墟上捡拾着一些碎片。同时,与之对称的是“我无法说清楚……;我不明白……;我弄不清……;我感到困惑……”当奥斯特利茨尝试以一种私人语言对创伤进行表达时——也依旧知道这种表达依旧是言不及义的。在他能够说和无法说之间,存在与虚无彼此缠绕,寻找与失落相互问讯,它们不断攀升,指向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死者在弥留之际会在几秒内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么,《奥斯特利茨》那就一部漫长的临终回顾——过去时间中忽然闪现的记忆之光,永远地拓印在了小说里。
在此,塞巴尔德显示出和他的德国前辈瓦尔特·本雅明相似的历史观。1939年,本雅明《历史哲学史纲》中,曾有过这么一段著名的话:
保罗·克利有一幅画,名为《新天使》。表现了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前方。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着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堵断壁残垣则拔地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
本雅明在留下这段文字之后的1940年,成为了数目庞大的失踪者之一。而塞巴尔德笔下的奥斯特里茨正是这失踪者的后代。小说中,他如是说:
希望时光不要流失,没有消逝,希望我能够像后跑,跑到它后面,希望在那里我能发现一切都依然如故,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所有的瞬间都同时并存着,在历史所讲述的事情当中……
当普鲁斯特通过写作《追忆逝去的时光》,来试图把握“时间”这个抽象、复杂、游移不定的庞然大物——通过追忆过去的细枝末节,在小说中建立起一座关于“时间”的大教堂,完成对过去的眷恋时,生活于二十世纪末的塞巴尔德却在空间的遗骸上,破除了时间之魅,他主动把自己放逐到时间之外(一个彻底的“移民”)——去死者的时间里找寻历史的答案。他不仅在想象中看见了那些死者,还通过诗歌般的语言浓度,虚构出了大量可信的细节,召回了死者的时间。正是这些瞬间,让我们意识到:当世界的秩序吞噬和粉碎个人的生命时,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形成另一种秩序——以细小无声、难以捕捉为标志——照亮着历史黑暗的迷雾,这就是塞巴尔德的小说里令人心碎的力量。而所有的幸存者的人生,正是由于这些重新拾回的时间碎片,而被扶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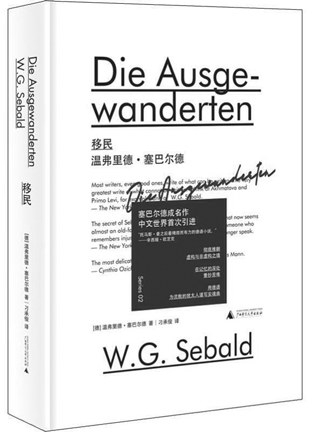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